1.雙極
唐諾和陳列為年輕作家雙雪濤槓上了。在2012年「台北文學獎」年金類評審會議上。不到吵起來,但他們確實為了手上這篇為了台北而寫的小說產生意見分歧,唐諾讚美雙雪濤「文字有線條」,筆下台北則是「陌生人的視角進到台北」;而陳列說,「文字很多地方是浮泛的,不夠精確」、「他的台北是想像的,並無真正台北生活……任何地方都可以」。兩人意見相同的地方只有一點,唐諾同意陳列,並說,「我感冒是村上春樹那段。」在那年的評審會議上,當時還稱作〈融城〉的創作計畫過了初審,並頒發20萬台幣。小說後來在中國出版了,內容大概和原初計畫差很多吧,書名叫《天吾手記》,豈止「只有一段村上春樹」,它本身帶著某種村上春樹印記,從命名、小說形式、語言,足夠讓唐諾從感冒變成重感冒。
雙雪濤在一次訪問中提到,他在投稿《天吾手記》前也不過在台北待過十多天,是因為得到「BenQ電影小說獎」來台領獎。他老兄說收到台北文學獎主辦單位通知後,琢磨了一晚,本來在銀行工作的他,第二天一起床,一口氣提上來就跑去辭職了。這也是很村上春樹的(《身為職業小說家》:「不知怎麼毫無脈絡可循,沒有任何根據,忽然起了這樣的念頭『對了,說不定我也可以寫小說』」。)東京有了小說家村上春樹。台北曾催生小說家雙雪濤。
台灣還沒出版地緣關係多親切的《天吾手記》,倒先出版短篇小說集《飛行家》。這時我總會想起2012年年金會議上評審的意見。一篇小說同時「有線條」又「不夠精確」,可以「陌生人視角進來」但又是「想像的」,前者指向雙雪濤的「文字」,後者指向「地方」。這曾讓台灣文壇兩大家爭論的兩個點,正是雙雪濤於《飛行家》中展示的特色。
遠較〈融城〉時期的文字更進步,不如說更個人,《飛行家》以強大火力展示一種「雙雪濤體」,具體面貌是段落中的調度,人物在裡頭同時行動與對話,說話不加引號,而敘述者的描述和觀點也交雜其間。它空白少,占地面積廣。句號比逗號多,對話比形容多。句子更短,更瑣碎。也就更利,更糾結。訊息量高,延伸遠。句句發散,卻又段段集中。看起來粗糙,其實裡頭打磨得多細。雙雪濤體就是清水模,以為是灌漿水泥,一次一大塊,從模板間距到每一體積注漿施受量都有嚴格計算。人看見稜角,其實是一種淬鍊。以為樸拙,卻是洗練。
尤其是裡頭的對話。借用同是東北來的莫言說的:「許多年輕作家不愛寫對話,這也是西方作家的特點,他們不擅長中國的白描。因為白描是要通過對話和動作把人物的性格表現出來……我試圖用自己的聲音說話,而不再跟著別人的腔調瞎哼哼。」姑且不論莫言對白描是不是誤會了什麼,但你會為《飛行家》裡豐富的聲音嚇一跳。對話構成《飛行家》中不少篇章的主體,在那樣的拋接中,故事被推進了,人物被展示了。但他的對話這麼擠這麼洶湧,完全是相異於台灣的小說家街景,我們是那樣井然有度,要不是不會寫對話,不然就是「書面化」的寫──說得很夾纏,寫得倒挺「乾淨」,一句一段,至少還在形式上讓人看起來像對話。但雙雪濤哪管這個,他的對話是違章建築,櫛比鱗次,塞得滿滿的。很接地氣,活蹦蹦滿地亂跳。那句子一拋一接,聲音一來一往,在丟刀子,不相讓的,很可以。沒在怕。姑引一段:
女孩說:餃子生的我都能吃一蓋簾兒,就想吃這口了。饒玲玲說,我去煮吧。你們聊。劉泳說:冰箱左邊那個門,第二層。廚房的燈在那。女孩說,你倆兩口子?饒玲玲扭頭說:兩口子他告我燈在哪?女孩一笑,是我傻逼了,但是你們文學圈誰知道誰跟誰怎麼回事兒呢?
你瞧,這對話多麻利。人物的腔口。各自的行動。還有關係(兩口子他告我燈在哪?)。還有那種帶著刺的笑。好萊塢編劇教父羅伯特.麥基《對白的解剖》考證「對白」的詞源,dialogue。「Dia-」在希臘字中是「透過」,legein意思是「講話」,dialogue毋寧是複合的英文,意思是「透過─講話」,對話當然是一項行為,但對話不是最終目的,它是為了導引出什麼,於是老麥基提出「對白等於行動」的主張。講話其實是動作的一環。
雙雪濤小說中,對話當然是對話,但其實也不是對話了,不只是對話了。一方面對話表現人物個性,但卻是更有機能性的東西,那是動作本身。是情節。甚至,是千斤頂,讓人物嘴巴不住開闔,四達八叉,看似南轅北轍不搭嘎,其實撐開一個空間,讓人浮想聯翩,是荒謬,是異想,是諷刺,是意在言外,是唐諾對話陳列,以為是雙極,沒接上,都在堅持,其實是各自滑開了,那個新生的間隙裡,有東西誕生了。
還是引用莫言:「我覺得這是一個要命的問題,一個作家怎樣使自己的作品有其鮮明的個性,在當今作家成群結隊湧現的時代顯得尤為重要。」《飛行家》裡每個角色都有響亮的聲音,雙雪濤發出自己的聲音。蒙面歌手遮著臉,你依然知道他是誰。
2.雙重
雙雪濤很會說故事。與其說他的小說會說故事,不如說他抓住了故事的核心。
故事的精要是什麼?是「懸疑」。於是短篇〈北方化為烏有〉裡,有位編輯帶來兩份稿子,他手下兩個投稿者不約而同寫了同一個謀殺案,像是狗的正面與側面。小說好玩在,當投稿者相遇,這會兒你一定想知道,到底是實話加上實話會得出真相,還是謊言加上真相會有解答?或者〈刺殺小說家〉中敘述者應徵殺手,只因為委託人發現有個小說家寫什麼,他家大老闆就會發生什麼,只好把小說家殺了,這又是哪招?最後殺得成嗎?是不是讓人很想往下看?
故事的精要是什麼?也許就是「衝突」。《飛行家》裡老有人死,有屍體,有刺殺,有猝然臨之的暴力,那讓小說一下子全像電影《白日焰火》、《東北偏北》,工廠黑煙城市白雪,對比太鮮明,性格太冷淡,衝突太劇烈,沒死幾個人說不過去,雪就這樣成了紅色……(關於陳列與唐諾爭論的「地方」。《飛行家》提供一個生產方案,但不是台北,而是東北。一個「地方」要怎麼誕生?雙雪濤筆下透過人物出生和語言體現。)
故事的精要是什麼,也許還包括「形式」做為驚喜盒的機括。雙雪濤長於透過形式製造「恍然大悟」或「不得不然」的閱讀驚喜,過去現在對照、雙敘述不同主角互相靠近又遠離……這些都是讓「故事」之所以打動我們的技術性元素。但小說家不需要把故事跑完,《飛行家》吸引人的倒是這個故事之外的「什麼」──他的表演、他的沒說完、他的刻意跑走,讓故事維持一種微微的困惑感(據稱出版這本書的大塊文化老闆稱之為「迷離」)。那是一種刻意的未完成,介於「被你意料到」和「刻意跑掉」之間,在寫實和超現實之間,在有意和無意之間,在具體和抽象之間,當然飛行很難,但漂浮卻只有他一個人做到。
那麼,故事的結局是什麼?這裡可以岔出來聊一下唐諾的感冒。雙雪濤的文學偶像是村上春樹,於是討論雙雪濤很容易從文學變科學,你看評論到最後總會像在看「量子纏結」,纏結的量子相隔多遠卻出現各種相似、悖論……。「雙雪濤如何,村上春樹如何」是一個起手勢,《飛行家》有幾篇確實會讓你會覺得有村上春樹幽靈在裡面飄蕩,修辭有那麼點村上腔:「玻璃杯裡的啤酒,形式裡的形狀」,村上春樹的慣見元素同樣可以在裡頭發現,「通道」、「異境」,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討論,但不會有什麼結論的。但這個沒有結論,也許可成為結局。一方面是關於雙雪濤小說的結局,一方面是雙雪濤小說家的結局。
《飛行家》簡體版的文案是「為故事而生的人,最純粹的小說家」,但我想,為什麼不是顛倒過來呢?「故事生而為人,最純粹的小說家」,小說家多會寫,《飛行家》裡頭淨是些沒有出路的人,是些小的不能再小的單位,從到北京混、專說胡話給編劇刺激腦力的小寫手、工廠裡的小工、潦倒的工程師……他們幹不了什麼大事,再有也終究是敗了。生命有一些什麼圍困著他們。那些衝突那個困境,基本上沒有地方可以去了。這個世道,沒有道理是硬道理,最不該期待是你怎麼還有期待。那怎麼辦呢?〈寬吻〉講了一個救海豚的故事。海豚因為長期被關著而傾向自殺,負責海生館表演的女孩執意做演出,表演內容是自己在大池子裡假裝落海好讓海豚去救。「因為牠喜歡我。因為這個節目,牠會活著,然後一次次把我救起。既使牠知道這是假的,牠也會擔心,擔心另一隻海豚搞砸,所以牠會相信節目是真的,然後等待每天救我,我知道有點殘忍,但我想不出別的辦法。」當然在這故事裡,你可以說每個人都一廂情願,誰都在騙自己。海豚在騙自己,但騙自己卻讓牠活下去;說「因為這個節目,牠會活著」的女孩也在騙自己,畢竟你有問過海豚嗎?你又知道海豚這樣想的喔。但女孩對海豚說謊,其實也是對自己說謊。而敘述者自己婚姻正觸礁,跟著希望海豚能堅持下去,他是不是也用這故事在支撐他生活?
我想說的是,這不就是「故事」的本質嗎?「故事」也許就是林宥嘉的一首歌,「人生已經如此艱難,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雙雪濤所有的小說都有一個「現實無處可去」的共同點,這才是真正的故事起點,現實是這樣啊,是海豚就是會死掉。是謀殺、是小人物想出逃、是〈終點〉中的司機和少女的一段對話:「師傅,我去終點。」、「關我什麼事」、「是,我就說一下」(這倒和另一篇小說〈翹翹版〉中那個挖出屍體卻挖不出真相的敘述者的結語很像:「墓碑上該刻什麼,一時想不出,名字也許沒有,話總該寫上幾句」),終究,沒有地方可以去了,沒有出口了,怎麼辦呢?就只有故事了。所以故事必須存在才行。它做為一個喘息,一種寬慰的眼光,一個可能性。在那個「所有上升的一切必將整合」的天啟瞬間,必須要存在一個波赫士〈不為人知的奇蹟〉或卡佛〈一件很小很美的事〉,不然就真的沒辦法了,什麼都沒有了。
關於小說家的終局,那也是很村上春樹的。回頭看小說家的起點(無論是村上或是雙雪濤,起床決定不幹了),或是《飛行家》各篇中不停出現的小說家身影:「每天八點起床,下樓吃早餐,回來寫一上午,中午吃飽一點,午睡,睡醒後處理郵件、電話和微信,然後接著寫上一點……」乃至《飛行家》之外雙雪濤透露出來的生活與小說觀,那裡面總把寫作當成必要的勞動,以及從勞動中感受到本質性的快樂,我們熟知的職業小說家村上春樹每天起床就是這樣幹的,我相信村上先生還會這樣繼續幹下去。那是他做為小說家的終局。那也可能是雙雪濤的,但就是確立了這樣的終局,才構成雙雪濤的起點(「對了,說不定我也可以寫小說」),他虔誠洗手,反覆揮劍,反覆想像那更完美的一擊。
延伸閱讀
1.【書評】吳曉樂:以愛情為引,勾出了歷史的縱深──讀張悅然《繭》
2.【書評】楊佳嫻:異托邦對話錄──讀黃崇凱《文藝春秋》
3.【書評】李桐豪:當年的小說應驗今日時局,東方之珠寶變為石──讀鍾曉陽《遺恨》
4.【書評】江鵝:作者你是被什麼東西逼過,要這樣逼我們?──讀《第11本小說,第18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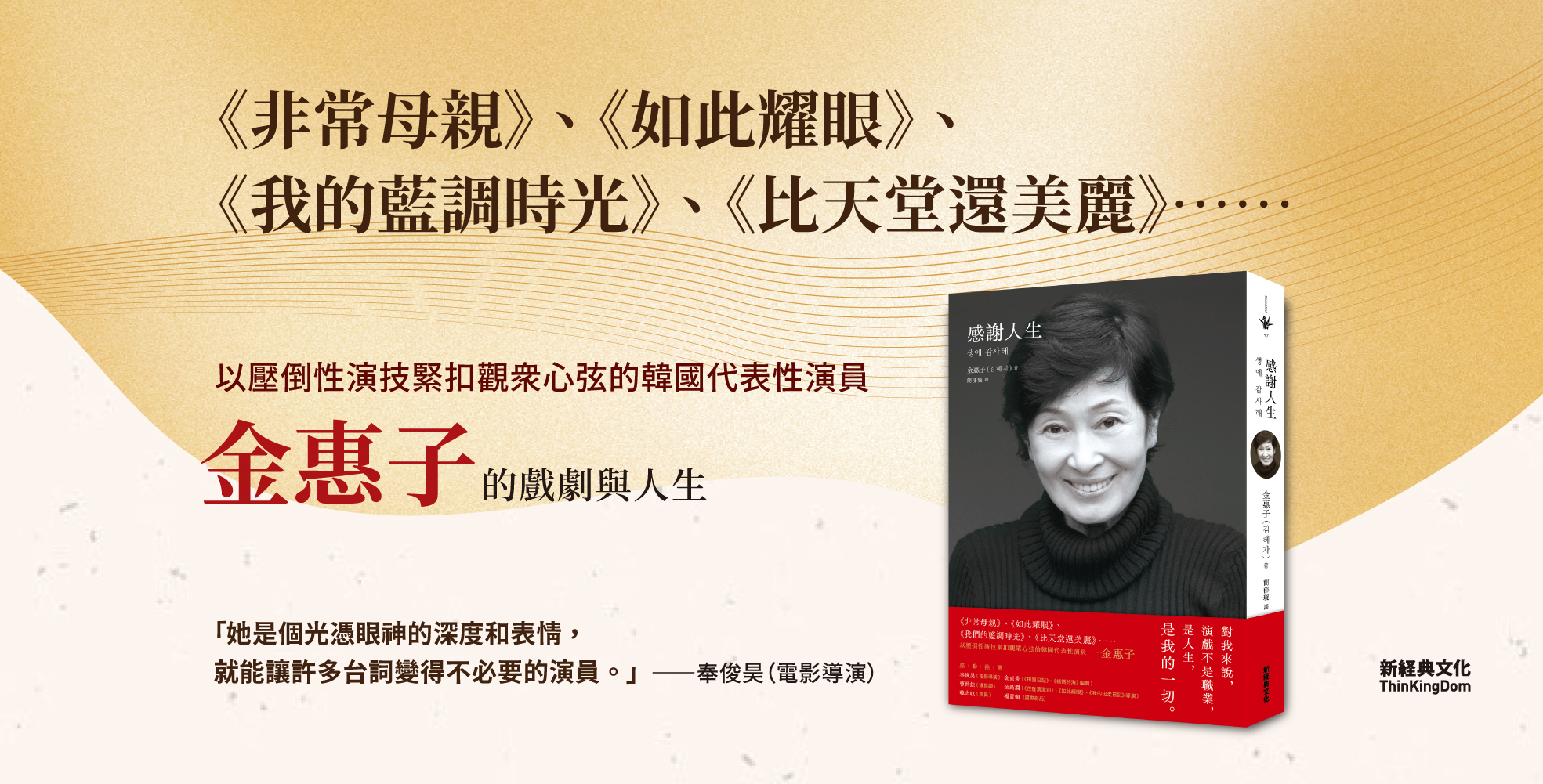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