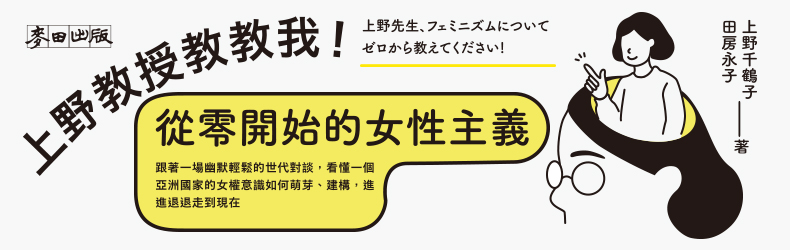
《上野教授教教我!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為日本「女性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1948-)與知名「散文漫畫家」田房永子(1978-)合作的新作──生於上下世代、做出完全不同人生選擇的兩人,透過輕鬆對談,梳理出日本社會如何在現代化過程中從零開始發展女性主義,以及那進退的變化如何直接或間接影響男男女女每個人的人生選擇、情感關係、生活樣態。
同處亞洲文化圈的我們,在書中能讀到了許多台灣社會的影子。麥田出版邀請了兩位與本書作者同世代、且長期關注女性主義的作家李昂與楊佳嫻,聊聊她們讀完本書的觀察。
對 談 人
作者簡介
李昂曾以《殺夫》獲聯合報中篇小說首獎;2002年獲頒第十一屆賴和文學獎;2004年獲法國文化部頒贈最高等級「藝術文學騎士勳章」;2013年獲吳三連獎文學類小說獎;2016年獲中興大學頒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中興大學「異想世界:李昂文藏館」於2019年正式開幕。
作者簡介

李昂:我和女性主義關係中,上野是非常重要的朋友,甚至影響到我小說的寫作。我在日本出版過五本小說,跟吉本芭娜娜、小川洋子、上野千鶴子這三位女作家對談過,其中上野給我最多理論面的衝擊。
上野是個絕頂聰明、機智的女人,念京都大學,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拿到社會學博士學位,學養基礎和英文都好,這些基礎使她可以在社會脈絡下用寬闊的視野看女性問題。而我多年來看到日本女性地位的低落,跟整個社會對女性的挑釁和敵視,在這本書兩位作者的對談中都得到了證實。
楊佳嫻:我讀的第一本上野作品是《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當時已經絕版了,要去二手書店找。但各位如果讀過她前幾年的《厭女》,也一定會對她直率尖銳的口吻印象深刻。讀這本《上野教授教教我!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就會知道她是反應非常快的人,田房則相對溫和。不同世代的兩人交換對女性社會處境的看法,尤其她們是落實到具體生活中來看,特別精采。
楊佳嫻:我是1978年生的高雄人,後來發現成長的歷程確實和台北同學有點差異。當年選擇文科完全沒有阻力,一方面可能我母親很早就發現女兒只會這件事(笑)。另一個原因,南部的觀念裡女孩念中文系很不錯,因為妳畢業不就是去當中學老師嗎(李昂老師笑)。中學老師當年在南部是一個體面的職業,也是個容易談婚姻的職業,連帶的各種價值和刻板形象都非常正面。一個女性當中學老師不會顯得太突出,又有一份說得過去的職業。這有點像紀大偉說的,八零年代《席德進書簡》出版的時候,大家對他的同志身分有點介意,但又會立刻說,可是他是藝術家,所以好像可以接受。有時候刻板印象反而帶來意外的空間。
我們家只有兩個女兒,父母重男輕女這事我經歷得少,但是進了學校對女孩子還是有各式各樣的要求,很大部分來自於「女學生必須純潔」的各種想像。比如我出去約會說謊被我媽抓到,「不念書,妳以後是要變落翅仔嗎?」她會立刻聯想到這個詞。對父母來說,這是養一個女兒所能落到的最糟狀態。少女時期父母會非常小心地保護妳的純潔性,害怕這純潔性一旦被汙染,妳的社會位置會往下掉。
李昂:婚姻百百種,但一般來說不分男女,考慮到婚姻時都會以原生家庭作為依據,不想再掉入同樣的窠臼。而許多家庭裡犧牲的都是母親,但為什麼這些受苦的母親還是會成為書中所謂的「毒母」呢?毒母有各個面向,有一種是她受到父權壓迫,連帶女兒也受父權壓迫,女兒不懂母親為何不替我爭取,為何母親和父權站在同一陣線。包括要求女兒上短大那種所謂的新娘學校,為當個賢妻良母做準備,別受太多教育以免嫁不掉。也是書裡兩個世代的女人念念不忘的議題。
今年已經74歲的上野,為何生長在那個年代還可以在京都大學參加學運,去芝加哥大學讀博士?理由很簡單,她父親是個醫生。她父親雖是個老派的醫生,但這在經濟上給了女兒獨立自主的機會,反而她母親比較傳統,要她嫁人。所以上野和父親的關係好過與母親。上野說自己就是從「厭女」出發,才成為一個女性主義者。厭女對一個女性來說,就是她感到自己的不足,討厭做一個女人,因為我這也做不到、那也做不到。田房則在上野的引導下細看自己與母親的關係,因為這絕對深深影響女兒將來要不要走入家庭。這些在書中有很多細緻的論述,到我這把年紀讀都還很有收穫。
楊佳嫻:「事實婚姻」和「法律婚姻」的二分法可能稍微簡單了點,在歐洲有些國家試圖創造出中間地帶的法律身分,比如「伴侶制度」。若大家記憶猶新,台灣推民法修改時,同性結婚、伴侶法、多元成家三套法案本來是同時推出的,但後面兩者受到的反對程度非常高。對多元成家的誤解──經過跟椅子或摩天輪結婚的討論過後──位於中間的伴侶法得到的討論相對少了。三者目前唯一部分實現的只有同志婚姻,但釋字748號也沒有說同志的結婚是「婚姻」,這個詞最後還是保留給異性戀的。
當然台灣目前高學歷女性較不想結婚確實和女性主義洗禮有關。如同李昂老師提到上野的情況,如果經濟獨立,確實較有餘裕考慮自己適不適合走入婚姻,走入一個由法律框限的親密關係裡。框限同時是一種保障,有兩面性,一旦有餘裕考慮,很多女性會選擇不走入。
有一位比我稍年長的大學理工系女老師告訴我,她是他們系上第二位女性學者。當年剛進來時,同事會關心她有無男友、結婚了沒,沒有人關心她研究什麼。隨時間過去,她結了婚,開始被問生子,第一胎生完問第二胎,最後生到了第三胎,大家終於閉嘴。這時終於有人問她研究什麼了(現場笑)。我不是說討論兩性就落後,因為直到今天男女仍然同工不同酬,網路上對女性的敵意到處可見,每則新聞底下仍充滿各種品頭論足。所以不是今天討論多元性別,女性的問題就不重要,但我們面臨一個問題是,該怎麼和相關人士以及下一代討論,上野和田房這本書具備引導的功能。

李昂:我走訪日本三十年,清楚感覺日本的社會結構非常嚴謹,從神權、到男權、到父權一脈下來非常完整。但台灣不同。台灣是個島嶼,也更是個移民社會,我們繼承了清朝中國大陸來的,不管儒家或者是父權的文化,後來經歷日本統治,國民政府來台等等,不斷被外來者進入,新的殖民者推翻前面的殖民者,因而持有一種開放性,所以台灣社會沒有日本社會那麼嚴謹堅固的結構。所以田房提出的A面B面難以破除、不能交叉的現象,台灣的確沒那麼嚴重。
當中也有文化面向。日本至今仍有下班的應酬文化,男性職員說我要回家幫忙老婆或帶小孩一定會被嘲笑。而現在台灣的年輕男性若說我要去喝酒,不回家幫忙,文化上可能不容許,可能會被指責不是盡責的父親。整個社會的氛圍和運作,台日的確不太一樣。
再則,日本是十分反移民的社會,外國人在日本拿到公民資格的機會極少,也較少接收移工。在台灣即便托育制度仍不足,台灣母親能得到的幫助還是比孤軍奮鬥的日本母親好很多,因為相對容易雇請到幫手。再則,我們社會氛圍不會嚴格要求母親一定要為孩子做飯。日本是連孩子中午帶的飯糰都被品頭論足的社會,社區其他主婦會評價妳這個媽媽夠不夠格,主婦只好挖空心思做便當。而台灣外食文化盛行,如同鄉下那種幾代同堂的家庭也都還存在,也不少祖父母能幫忙育兒,這些都減輕了主婦一些負擔。
台灣的女性主義絕對是走在亞洲最前面,田房提到的很多事情,即使是在我那個年代,我們在台灣都已經試圖打破了。但這不表示我們比較進步,而是我們的社會給予婦女的資源和力量不同。日本的女人百分之三千就是真的比較辛苦。
楊佳嫻:我們在日本小說裡常會讀到母親的痛苦,比如老牌的推理作家夏樹靜子十年前的小說《霧冰》,就是寫一位母親沉重的負疚感。很多小說裡也都會寫到社區母親之間的恐怖關係──公園溜滑梯旁邊的母親群體,現在來了一個新母親,她夠不夠格融入我們,發生各式各樣的排擠,衍生出殺人案……當這類小說題材多到一個程度,大體上就可以知道日本母親的壓力多大。
A面B面的想法也讓我想到那部經典著作《第二輪班》,很多女人在公共場域、個人工作已經上一輪班了,可是回到家,面對家務她必須再輪第二輪班。試圖向丈夫協商,有些時候也協商不了。這也呼應田房說的,父親的「石像化」──母女之間已經爭吵到快要殺人了,但父親會從後面飄過去,沒有要排解或緩頰的意思。石像化,實際上說的也是男性一直留在A面,所以當B面發生事情的時候,他會不知所措或覺得與我無關。
我認同李昂老師說的,現在台灣特別是都會區,這種情況相對緩和。早年有個流行詞彙叫「新好男人」,因為變得普遍,現在已經不太用了。所以透過性別教育一代代這樣下來,台灣在這方面確實還是比較有希望。
李昂:我有七本書售出海外版權,在國際上打書時很容易被問到這個問題。但在海外這個標籤會有不同面向。九○年代初期《殺夫》在日本出版時,我問上野這題材為什麼在日本可以被接受,而且我去打書或演講,都不太感覺到敵意和惡意。我立刻從她那得到答案──因為我是外國人,我不在那個體系內。所以,在日本我作為一個外國人,自稱女性主義者是可以的。可是當上野這樣自稱,她就被攻擊得很慘,被貼很多惡意標籤。上野總可以很精采漂亮地反擊,可能就是從那種水深火熱的社會訓練得來。
在歐美,二十幾年前尤其像在澳洲那種地方,當妳自稱女性主義者,會被認為是很胖、嫁不掉、沒有男人要的形象,或者就是女同志。但因為後來出現了一種所謂的草根女性主義(grass root)──被認為是跟當地的國家、政治、社會息息相關的女性主義,所以他們也認為我的作品是草根相關的,就不歸入歐美那一派。基於這種種不同的理由,都使得我受到的壓力比較小。
但台灣女性地位的爭取確實許多是在我們那個世代完成的,最開始是呂秀蓮,但她也不能使用「女性主義」,因為那年代馬上會被扣帽子,甚至是紅色帽子。於是她改了一個說法叫「新女性主義」,從那展開了台灣的女性運動。我很服膺上野講的,宣傳理念要傳播得出去才有用,所以我在報紙寫專欄,也很早就上談話性節目,難免會受到壓力,但跟上野相比沒有那麼慘。
楊佳嫻:我主要的活動範圍在學院和文學圈,這兩個領域妳自稱女性主義者不會造成傷害,或立刻出現偏見,有也不會明確地說出來,在台灣大家至少還有一點政治正確的敏感度。
當然我也在想,日本社會是不是也在改變中。像之前的伊藤詩織,雖然最後的判決不盡如人意,過程當中她也受到大量打壓和攻擊,可是有她那樣一個勇敢的女性出來抗爭,堅持到底,還是在日本社會投下一顆震撼彈。不追究是成本最低的做法,但也是比較爭取不到正義的做法,對方可能再危及其他女性,甚至沒意識到這行為有問題。必須要透過像伊藤這樣的受害者,願意付出比較高的社會和個人成本站出來,才能讓日本社會鬆動。
還要補充,女同志不一定是女性主義者,過去確實有這種誤解。不管是異性戀或同性戀,這都還是關乎我們對於自己的性腳本或性別腳本可不可以用一種比較多嘗試、有彈性的方式看待和實踐,才有可能促成上野最後講的,女性主義不是鐵板一塊,女性主義是多樣的。
上野千鶴子作品

延伸閱讀








 霧冰
霧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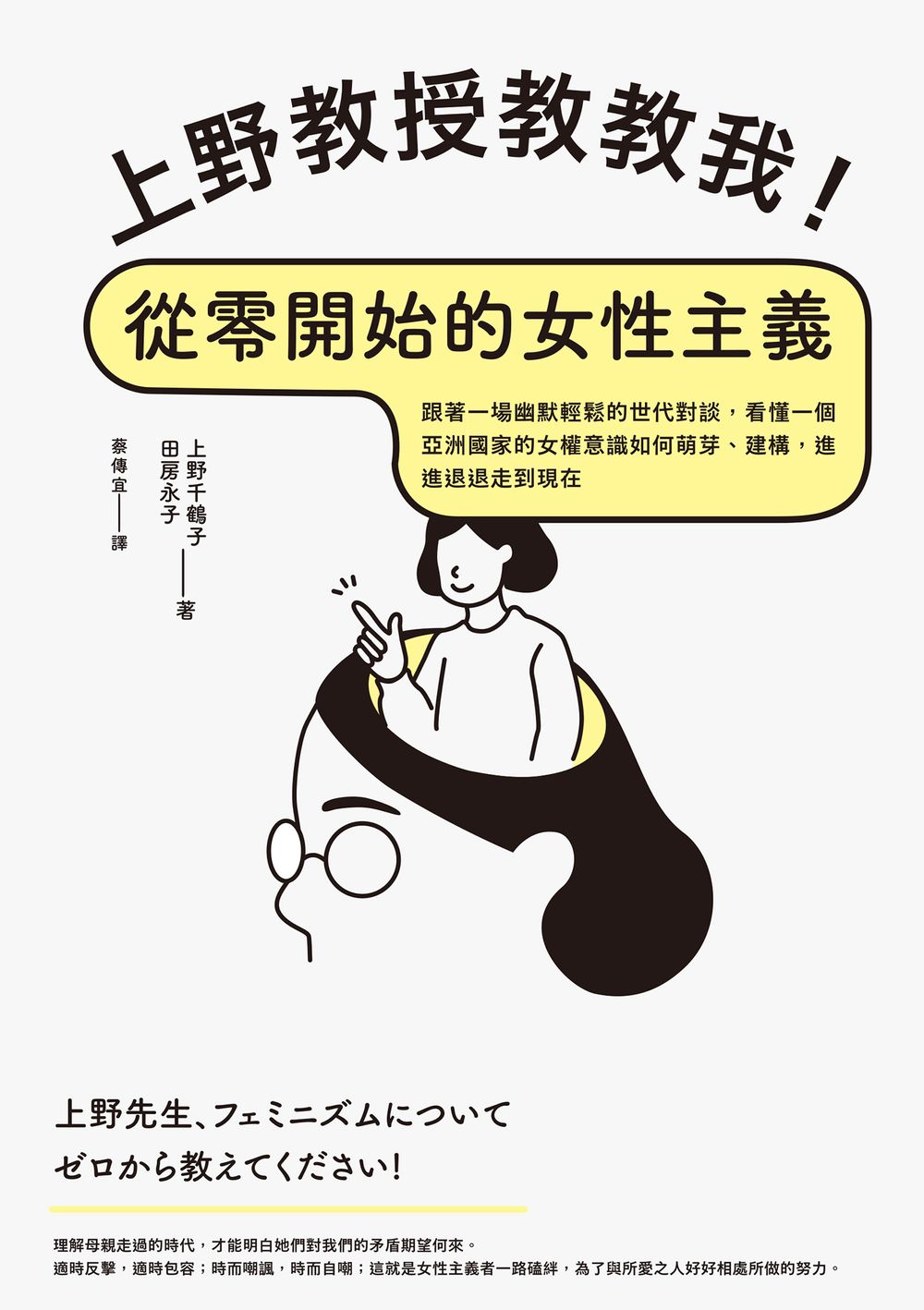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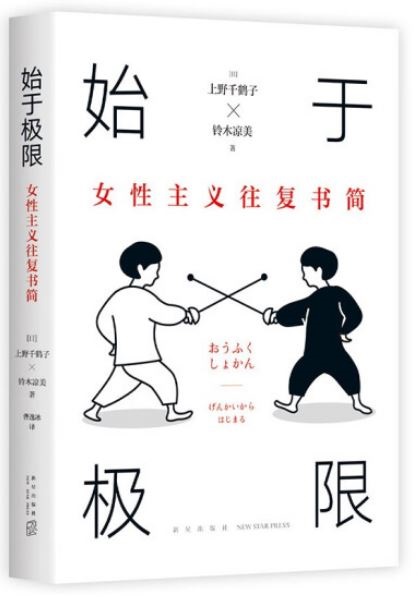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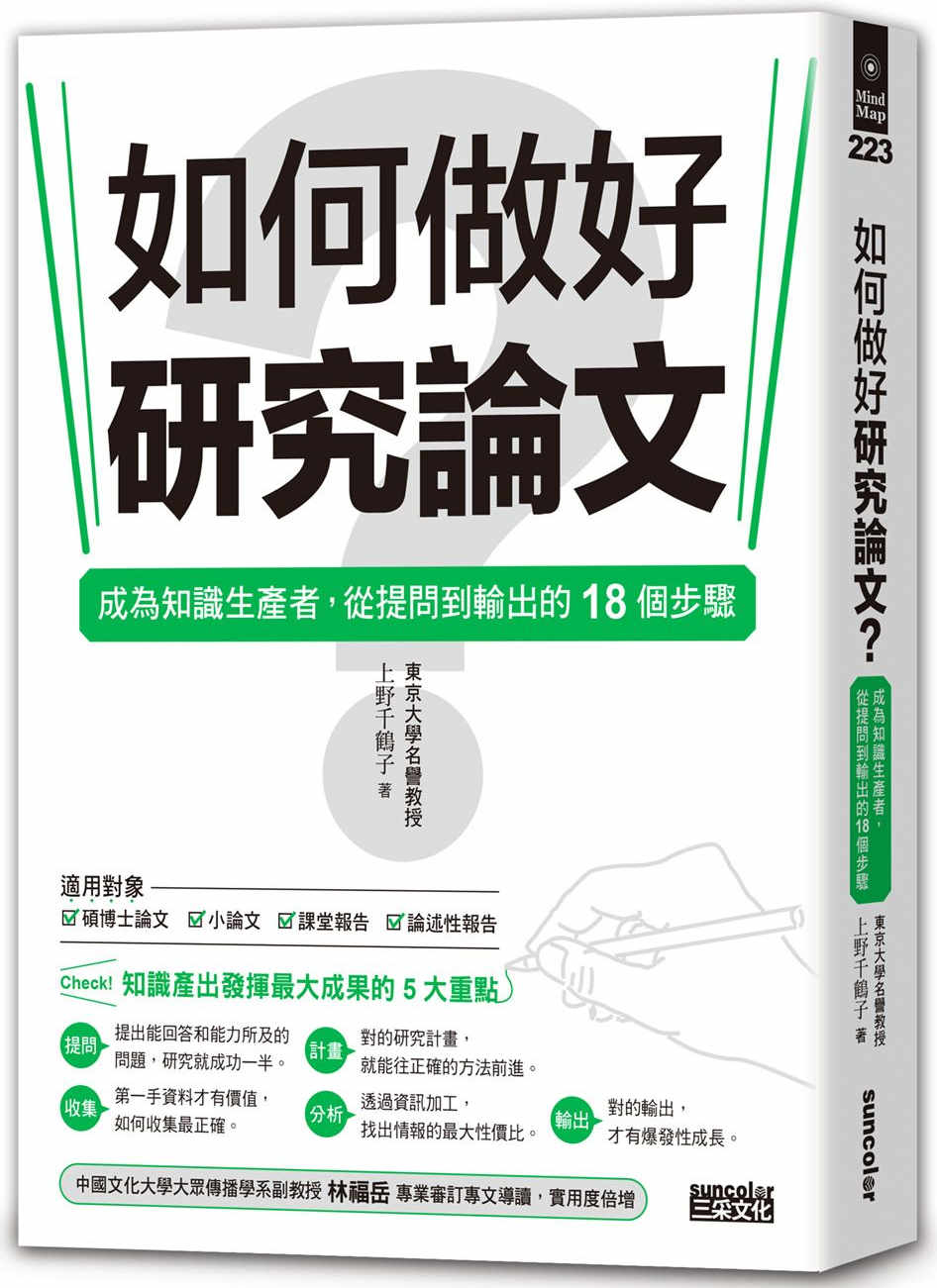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