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譯者當然也會恨自己譯的書,但多數是敢恨不敢言。(圖/pixta圖庫)
譯者當然也會恨自己譯的書,但多數是敢恨不敢言。(圖/pixta圖庫)
恐怖大師史蒂芬.金討厭自己寫的《劫夢驚魂》(Dreamcatcher),這還算小 case,他更討厭早年以筆名發表的一本中篇小說,恨到不僅停印單行本,甚至從合集裡摘除,決心讓它從地表消失,更寫專文說明「絕版是好事」。
為人作嫁的譯者,當然也會恨自己譯的書,但多數是敢恨不敢言。
好久好久以前,有一本翻譯小說細數職場新人的血淚史,紅得發紫。在譯後記裡,譯者坦言自己並不認同故事主人公,還數落這角色的個性有哪些缺點,結果引爆愛書人圍剿。原來,作者恨自己的作品可以,譯者竟連洩怨的空間都沒有。
編輯發書,譯者接不接,決定權在譯者。既然中意的書才接,為什麼還有怨言?案源不多的階段,譯者多數是有書就接,像我入行之初,第一本和第二本間隔好幾個月,接第三本之前也空窗很久,當時想法是,反正是副業,再沒書可接的話,回歸新聞圈也行。
幸好我興趣廣泛,第一本是以美術為主題的現代驚悚小說《我綁架了維梅爾》,接著是商業書《夢想家、生意人與狗雜種》,然後是另類童話《魔法陣》,第四本是十九世紀推理小說《雙姝謎情》,都不算難。到了第六本,又是商業書,原書強調「簡單」卻名不符實,內容專業而龐雜,舉例繁多,一點也不簡單,我邊譯邊叫自己記取這次教訓,以後不要再踩到這種地雷。然而,接簡單一點的書,就能沉浸書香天地、躺著翻譯嗎?譯者對書的愛恨情仇可沒這麼簡單。
 我綁架了維梅爾
我綁架了維梅爾
 夢想家、生意人與狗雜種
夢想家、生意人與狗雜種
 雙姝謎情
雙姝謎情

跨世代恩仇錄《該隱與亞伯》是我大學時代就想拜讀的小說,如今已和《戰爭與和平》、《大亨小傳》、《天地一沙鷗》並列全球百大暢銷書,春天編輯來信邀譯時,我還愣了一下,「中譯本早就出了吧?」而且,該隱、亞伯是《聖經》裡的古人,以他倆為名的作品層出不窮,這本該不會碰巧跟曠世鉅作撞名了吧?作者亞契(Jeffrey Archer)文筆流暢洗鍊,重情節起伏和人物糾結,節奏感直逼追劇,續集《世仇的女兒》也同樣扣人心弦,我工作兼享樂,哪需要週休?一天敲鍵盤十四小時也不累,入行之初的幹勁又回來了。能天天翻譯亞契的話,Netflix都可以退訂。
假如年復一年都有這麼完美的工作機會,人生就不需要小確幸了。現實生活裡,有時因檔期喬不攏,再愛的書,例如新經典的《十月終結戰》,我也只能向編輯說抱歉,然後自費滿足按捺不住的閱讀慾,看看作者是怎麼未卜先知疫情。就算排得進去,有些好書就是來得不是時候。同婚議題達沸點的那年,麥田邀我翻譯文豪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的《波士頓人》,可惜當時我已連續接下兩本同志書,想換換文體,也避免被定型,考慮再三才婉拒。另有一次,時報有意推出傑佛瑞.尤金尼德斯(Jeffrey Eugenides)短篇小說,但我也因剛譯完兩本短篇集而含淚遙望大師。就算沒邀約,我讀到心愛卻無緣親譯的作品,例如沙林傑早期的短篇《致艾絲美》,見他用怪字 watty 形容燈泡刺眼,也不禁想對照繁簡版譯本怎麼翻,向高手偷學幾招。
愛太深呢?迷戀一本書到無法自拔時,譯者容易掉進超譯的泥淖還洋洋自得,向作者篡位。西方文化重視藝術表現,容許譯者恣意秀才情,但在中文圈,反客為主的譯者卻常遭撻伐。我在翻譯《霧中的曼哈頓灘》、《祖母,親愛的》、《親愛的圖書館》、《戰山風情畫》這些愛書期間,就不斷自我警惕:你只是一個小譯者。把愛擱一旁,故事原汁原味呈現給中文讀者才是正道,不許加油添醋。

比純純的愛更常發生的例子是愛恨交加。愛的是原文,恨的是自己不才,文采無法和作者匹配。《樹冠上》譯者施清真曾諷刺說,「譯得死去活來的書才是『文學巨著』。」我也有同感。另一種形式的愛恨是,封面吸睛,吸乾你荷包,你捧書回家讀了幾頁由愛生恨,再也讀不下去,譯者同樣有衝動接書卻秒悔的情形,沒啥好奇怪。較罕見的狀況是,譯書過程原本心曠神怡,後來卻因客觀條件影響而文思堵塞,例如我以35高齡罹患水痘時翻譯到某巨著,整個人被摧殘到心力交瘁,導致日後一見身上的痘疤就想起那本書,一見那作家大名就渾身爆癢。
就算是同一位作家,縱橫文壇數十年,早中晚期風格迥異,追書追到老的書迷想必在少數,而譯者更辛苦,忠於原文要擔心挨讀者罵,盡力承續作者早期風格又違背良心,於是鍵盤愈敲心愈恨。有些作家早期筆法明快帶勁,中期變得囉嗦賣弄,後期敘事流於拖沓,不恨也難。我每本必讀的一位美國當紅小說家出新書,我在有聲書上市的第一天買到手,聽了不到一小時就能篤定大魔王是誰,邊聽邊笑作者故佈的疑陣和假招多麼幼稚,結局果然被我料中。假如我有榮幸翻譯到這一本,四五百頁不知會折騰我多久。
有時候,恨書到極點,其實是早就愛上它而不自知。某年我匆匆接下一本輕小說,事後一讀內文,才知不是我的菜,但合約已簽,截稿日期在即,想悔約也來不及了,只好硬壓著輕視這作家的念頭,下巴仰角四十五度工作下去,結果挺過開場的黑影之後,恨盡愛來,翻譯過程變得異常輕快,猶如同步口譯時腦波和講者搭上線,講者才起個話頭,我就能接龍。再套一句施清真的諷刺語:「容易翻譯的書,肯定藝術性文學性不高。」哈,正中我下懷了。
全職翻譯以後,我才領悟讀閒書有多爽。讀《天使與魔鬼》,遇到太冷僻的教廷SOP,跳過。讀《三體》,天文學、物理學、「紅岸工程」,術語充斥,不懂就是不懂,跳過跳過再跳過,讀到最後一頁卻仍意猶未盡。譯者可沒跳頁翻譯的福氣,從頭愛到尾的書是屈指可數,但匪夷所思的是,再怎麼恨一本書,稿子一交出去,主觀的負面因素全豁然消散一空,幾天或幾年後回憶它,不再記仇,腦海裡只有它的好,恨過水無痕。
我喜歡用「代理孕母」來比喻譯者。孕母出借子宮九月後,把嬰兒交給卵母精主,可能會吐訴妊娠期的苦難,但絕不會當面嫌寶寶朝天鼻戽斗,譯者同理也會以假愛掩飾真恨,原文的缺陷就深深埋進心底吧,講出來傷到作者,讀者未必能認同,被出版社列入黑名單更得不償失。譯者作品集裡有哪些恨書,用不著摘除,就讓它們和史蒂芬·金最恨的那本一樣,繼續隱名好了。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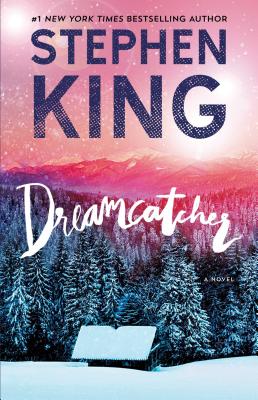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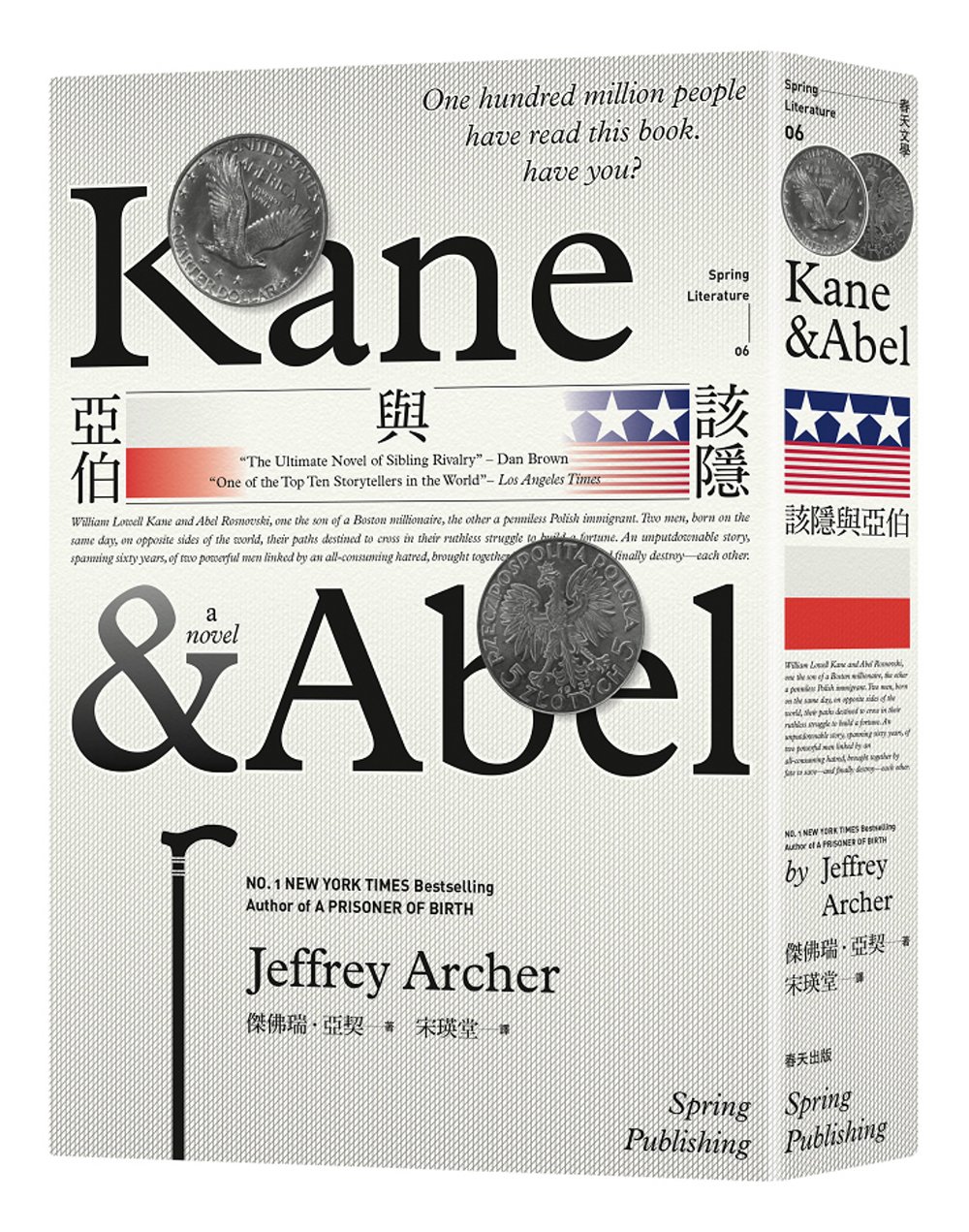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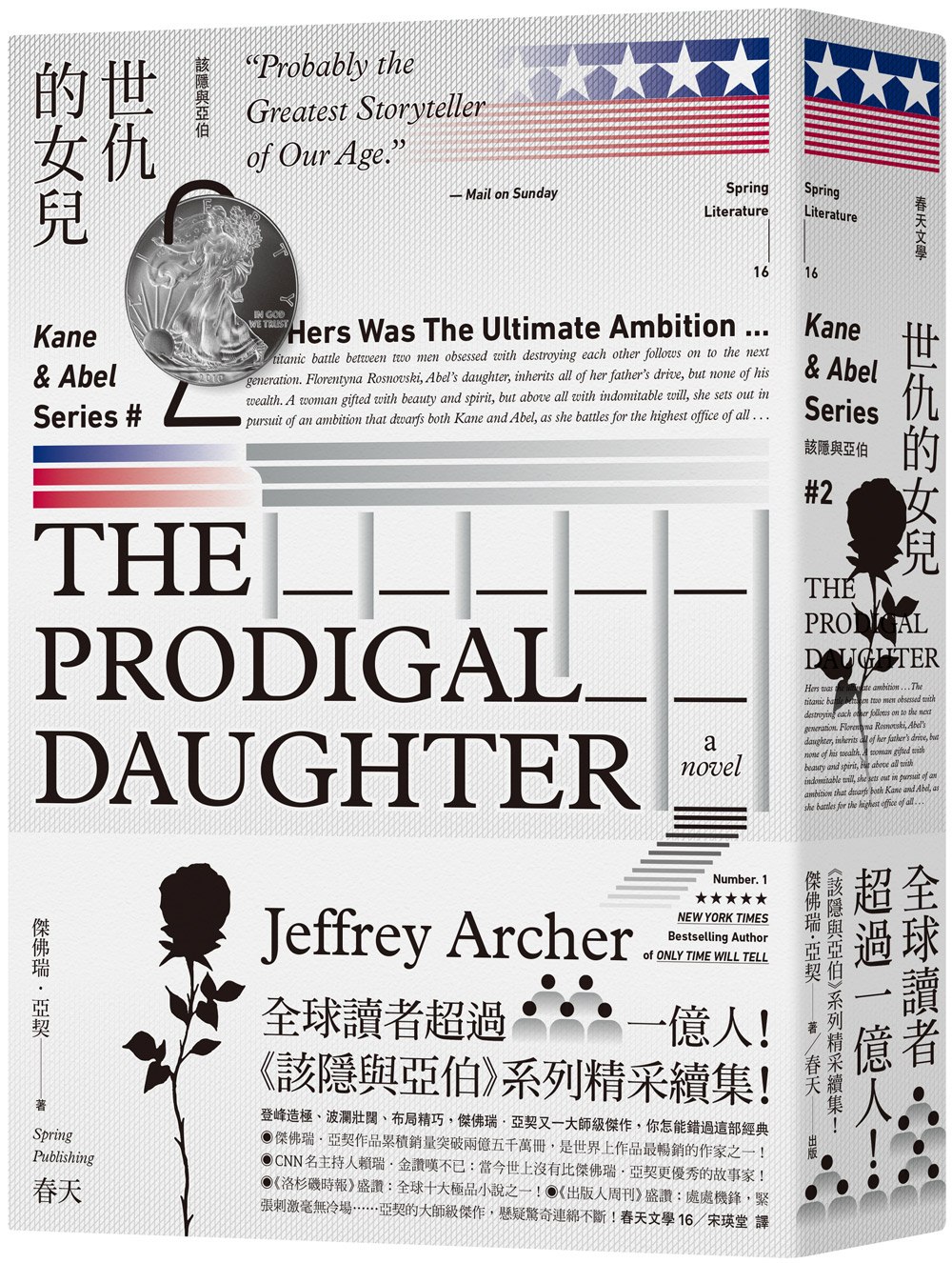


 致艾絲美
致艾絲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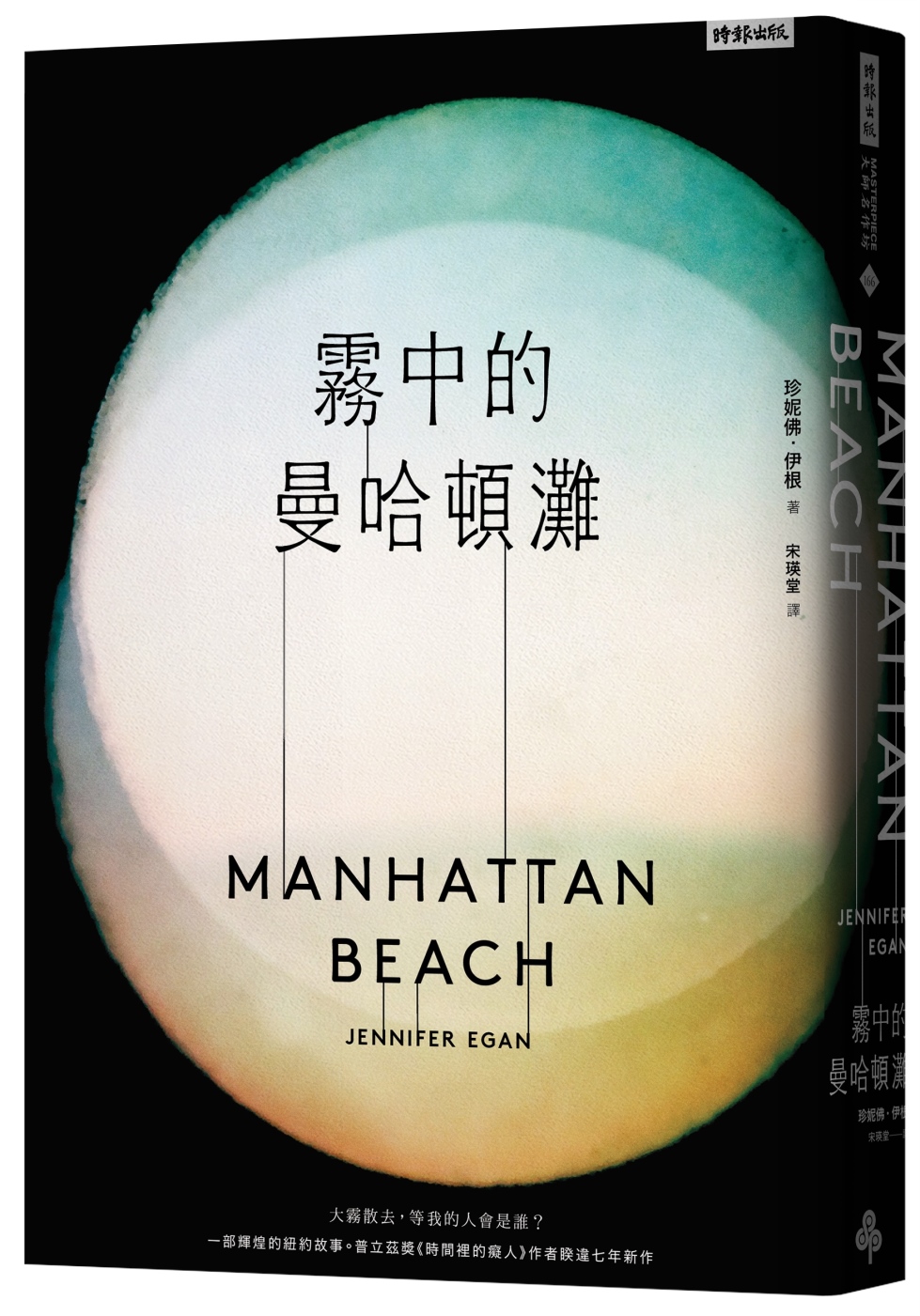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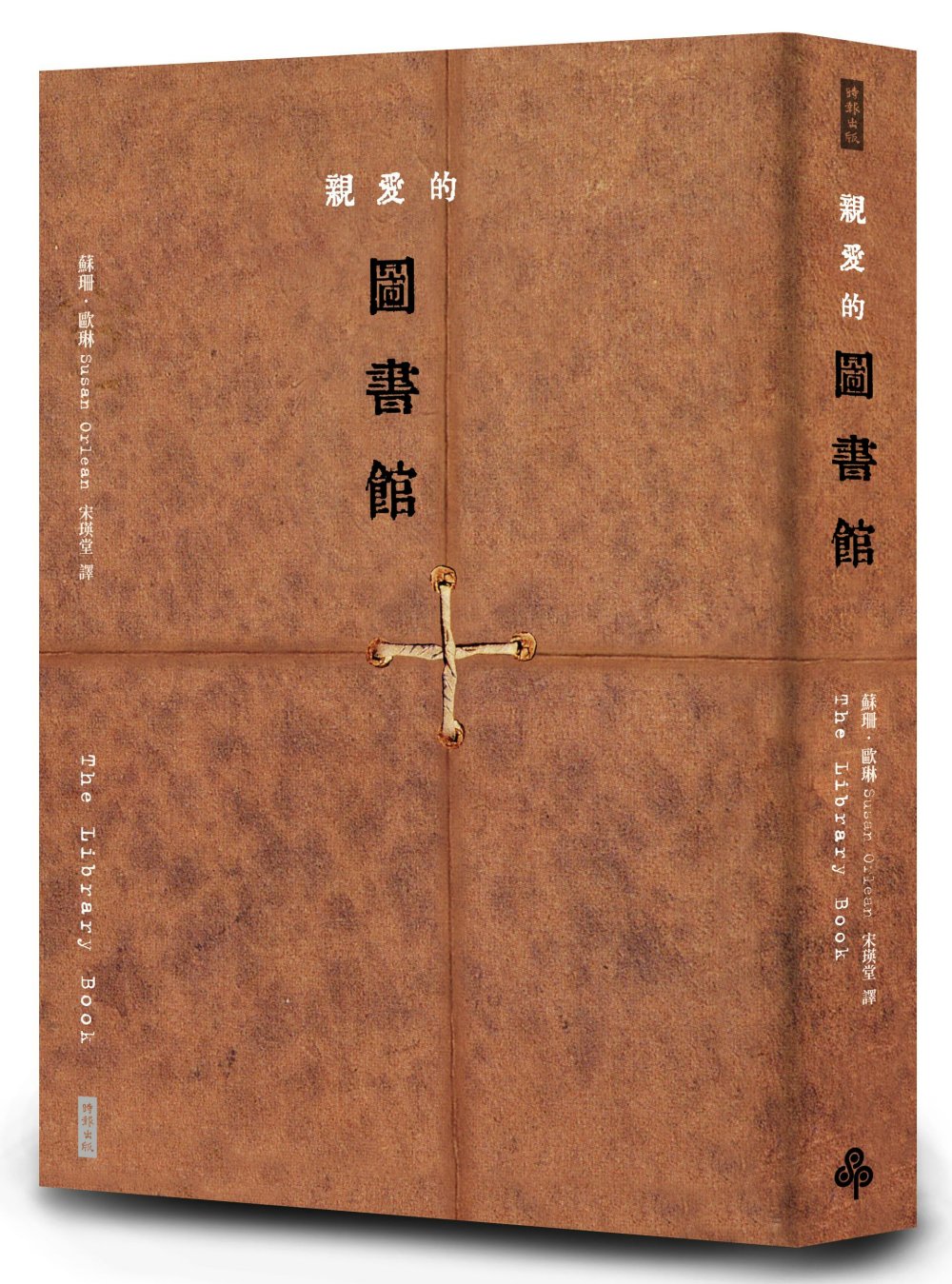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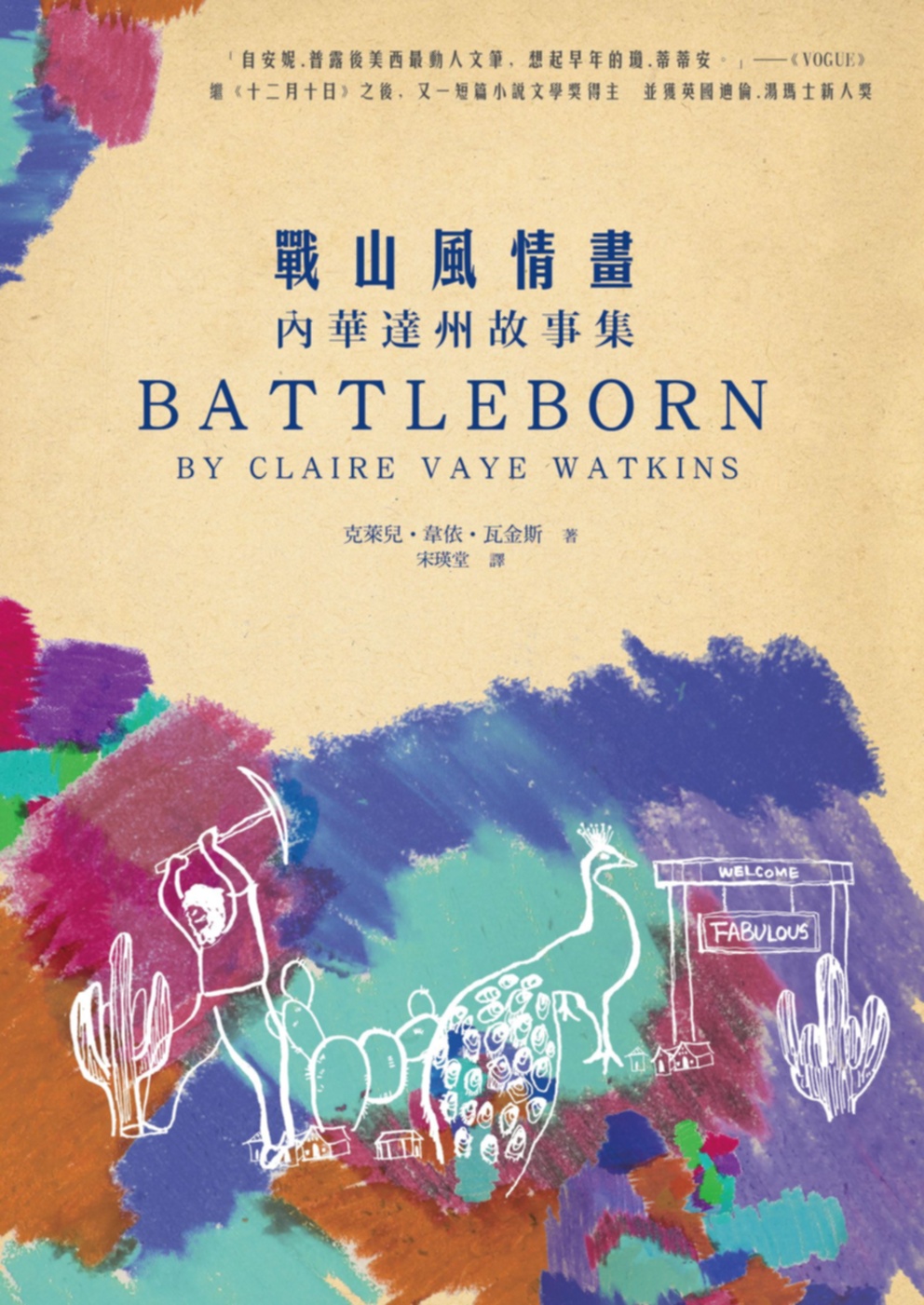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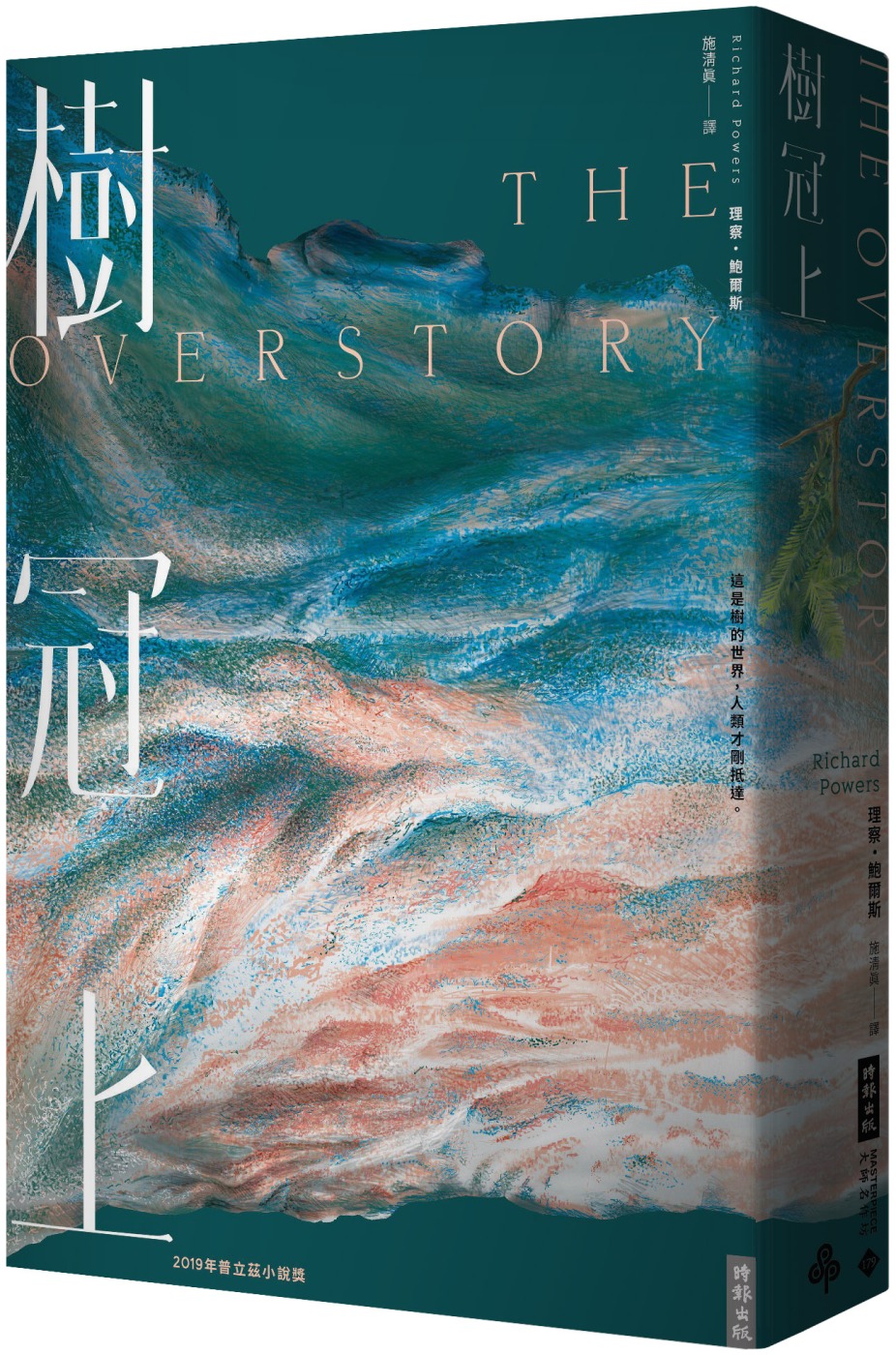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