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正翔的新書名為《旁觀的方式》,讓人膝反射聯想到八〇年代約翰.伯格與桑塔格的兩本影像巨作。汪正翔看似以憊懶的視角切題,實則精準捕捉我們的時代如何由影像衍生出許多歪曲行為與怪異現象。橫跨攝影大哥、採訪者、影像教育者、藝評人、藝術家等多重身分,他說自己最喜歡的還是在電腦前發廢文,一日一廢文有益身心健康,落漆版朵朵小語與超正經藝術思考的差別,僅在觀者轉瞬之間。
在新書裡,他從 IG 濾鏡談到數位 5G 對影像的影響,把班雅明的〈攝影小史〉挪移成當代的〈美照小史〉,身在這個靈光缺席、〈出門以前,旅遊就已經(在社群平台)完成的〉的 Meta 影像世代──我們還能從一張照片裡看到什麼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林君燁|A=汪正翔
Q:做影像創作的人總是被問這個問題:你是攝影師還是藝術家?你是怎麼開始拍照的?
A:其實我對名稱沒有那麼在意。當我們提出「人設」這個概念,就已經暗示人設是短暫的。所以我不是那麼在乎有標籤貼在自己身上。有人覺得講自己是藝術家很假掰;有人堅決說自己是藝術家,可能是希望在藝術世界有一個位置,不要被放在攝影這個比較小的範疇之中……我有時候也會有這個想法啦,也會強調自己是藝術家。
一開始動了想要拍照的念頭,是因為申請國外歷史研究所的過程真是太煩了,我覺得自己沒有做學術的天分,我本來做的研究也是偏藝術史,就想說為什麼不乾脆轉換跑道做創作?選擇攝影做為申請學校的媒材,部分是因為我眼睛不好,小時候我媽會有意無意地買相機望遠鏡放大鏡各種設備給我,所以看到這些東西我就很高興,這好像代表一種我的特權。
Q:平常少有人意識到你的眼疾,視弱是否有影響你的影像創作?
A:目前對我沒有太大影響,我覺得自己在視覺上的感覺蠻普通的,這也是我的創作中沒有偏向表現畫面的原因。所以談論視障這件事,就只能當作一個笑點來講,大家看到一個視障會拍照,連我自己都覺得有趣。
在一些很偶然的情況下,讓我真的意識到自己的視障。有一次我刷愛心卡通過捷運閘門,被攔下來驗票,驗票員後來把愛心卡「嗶嗶」兩聲的設定取消掉,所以現在我的卡只會發出一聲「嗶」。我也講不出來這件事到底哪裡嚴重,只有在那個當下才會有感覺。很多無意間的歧視甚至不構成歧視,它只是一種忽略。
Q:對你而言攝影算是半路出家,讀藝術學校更不會得到接商攝案的技能。你是怎麼從創作到開始接案?
A:我很怕無聊,在藝術學校裡沒事做讓我很恐慌,回台灣之後就努力找各種案來接,那時候沒什麼基礎,一開始接的案子比較脫離我的同溫層,像是拍苗栗的建商木屋之類的,現在回過頭看反而很有趣。我平常表現得像是一個不關心社會的人,但其實我很喜歡看到社會各個面向。
布列松說攝影對他而言,就是「做為一個人」,他走到街上,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世界發生什麼事情。我難得有非常認同布列松的時候。我可以體會他講的感覺,攝影不是做研究,或跟設計、商業結合,也不是嚴肅的調查,攝影就是一個人走在路上用眼睛去看。
Q:你會使用接案照片做為創作內容嗎?其實曼・雷(Man Ray)也算是接案攝影師,他本來是畫家,後來為了要生存就開始拍照。接案攝影是否有隨著時代改變?
A:現在很多案件非常分眾,不像從前的接案主題比較具有普世性,例如人類、家庭關係等,比較容易轉換成「創作」。另外一個差別是,現代主義跟報導攝影聯手的黃金年代過去了,以前做報導攝影轉身就可以變成藝術家,現代主義肯定這件事,布列松大部分的作品就是他接案工作的成果。可是我們的年代已經沒有這種信念了。我們平常拍照也不太去處理人的生命狀態或者內在本質這麼大的主題。接案拍肖像照,有時候我要假設照片可以表現出人的內在狀態;可是當我做藝術創作的時候,我不覺得那是一個令我興奮的東西。
接案某部分滿足了我去觀看這個奇奇怪怪的社會,過程中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很像到不同的部落,雖然我的移動範圍都在台北。某種程度上,我心裡知道那個「不同」只是一個奇觀,或者它背後有結構性的原因,我在接案過程中所看到、感受到的僅僅是一種新鮮感,這也是為什麼我沒有把這些都變成創作。
我覺得體認到自己是「半調子」很重要。你知道你是個半調子,就不會告訴別人你的作品在凝視弱勢、凝視他者。攝影這種「旁觀」的姿態,意義來自於滿足自己,半調子的觀察其實對世界沒什麼意義,就是對我自己而言有趣而已。

Q:許多攝影師的共通點,大概都很愛把自己想像成一個旁觀的、站在邊緣的人,而這也是你新書的題目。你通常會介紹自己是什麼類型的攝影師?
A:我一般會說我是拍藝文類人像的。如果認真回答,我會說自己比較偏向觀念攝影。
攝影創作常著重形式,覺得對象不太重要,重點放在經營構圖,透過形式去表現抽象真實,這都算在現代主義攝影的範圍裡;但別忘了還有觀念攝影,觀念攝影跟對象綁在一起,不是要把對象真的呈現給觀眾,它只是說「誒,我指著的那裡有一個對象」,我指示某個東西在那裡做一件事,我指示某個東西存在,或是指示我自己。就這點來講,觀念攝影發現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攝影並不是語言,而是一種更直白、更乾枯、更不具意義的東西。巴特、桑塔格、伯格那一代人努力地想要發現一種新藝術,所以把這一面提出來,他們覺得如果做攝影一直去搞畫面、搞像繪畫語言一樣的東西,這其實很不新。
今天「指示」已經成為起手式,在創作當中不是一件多麼特別的事情。可是對攝影來講卻很特別,攝影跟當代藝術的發展有落差,當攝影看到當代藝術運用攝影的指示性,而非運用相片的畫面,攝影就覺得這遠離了攝影本身。那並不是當代藝術的問題,而是攝影跟整個藝術理論的發展脫節。
Q:你是拍肖像、婚禮、展場的攝影大哥,同時也是創作者、採訪者,有時候還是攝影評論者。這些角色轉換有什麼不同之處?
A:我盡可能不要有角色區分。我的廢文跟我的藝評看起來很像,甚至跟我寫的採訪也很像。我覺得應該有既不屬於採訪,又不屬於評論,也不是學術研究的方式。我一直認為我想做的事情是在「類別之外」的。
做為評論者不可避免地會談到學術內容,我對這塊有點抗拒。當代藝術可以介入最學術的題材,可以用量子力學或者社會底層當做創作主題,但我認為「題材」跟「藝術好壞」完全沒有關聯。重點是,藝術有沒有提出學術以外的目的?如果用學術材料加上藝術方法,來實踐一個學術或是社會的目的,那推測設計(speculative design)做得更精準,更不用說那些真正從事社會運動的人。我覺得我們應該回過頭去想「創作有沒有自身的目的?」
Q:當代藝術的討論常有泛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的傾向,你在書裡寫到,有一次你直接對藝術學校的教授說「這些內容不是有人可以比我們(創作者)討論得更專業嗎?」對你而言,創作的強項並不在這裡?
A:台灣的創作者在運用學術材料的時候,有一種位階比較低的感覺,好像一面對學術,創作者的自信就不見了,我覺得最關鍵的還是:你有沒有創作立場、有沒有創作意識?
但這似乎被視為一個不成熟的問題,有朋友跟我說這不是菜逼八的藝術學校學生才會問的嗎?可是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我們做創作的,愈到後來愈發現這件事情難以回答,如果我們不一直死盯著這個問題,就很容易走偏,很容易做出「看起來很像樣」的作品,然後「創作」其實沒有發生。
我覺得一個要問的問題是:如果一個社會性的創作有效,那它的藝術性就變高了嗎?很多國外社會性的創作真的能造成影響,因此我們往往認為,在台灣跟社會議題相關的創作,問題是效用不夠明顯;可是對我來講,無論一個作品是否能夠產生社會效益,這跟藝術性都不直接相關,根本的問題應該是「藝術該不該有效用?」

Q:創作者總是在等別人來論述他們和作品,但你有能力論述自己,這點其實蠻少見的。你覺得這對你的創作有沒有影響?
A:以前我覺得一旦人家知道你會論述,就覺得你只會嘴,所以我後來寫論述比較像在反覆自我檢視「我關心的藝術是什麼?」「我想創作的藝術是什麼?」我覺得這種自己對自己的嘮叨是有用的。一開始我根本讀不太清楚什麼是觀念藝術,只是自己亂摸索,後來看多了觀念藝術的東西,寫論述的時候也會用到,慢慢發現自己的作品跟論述會有落差。文字提供了一個架構,我發現人一開始都不聽文字,而是相信自己的感覺,可是當你看一遍二遍三遍,你就會開始反省。這就是文字的作用,它就在那裡,一個字一個字不斷地提醒你。
文字可以另開觀點。創作是一種觀點,接案是一種觀點,寫評論是一種觀點,如果一直待在某一種觀點裡,很容易受制於那個領域裡的潛規則而不自知。可是如果我能夠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哪怕是接案對創作來說都有幫助。那是一種晃來晃去的感覺。
Q:有時候要創作者多說一點自己作品的什麼,他就不太自在,甚至有人覺得作品最好的狀態是不要發表,你怎麼看?
A:那他可能不愛現,但我愛現啊。我想到一個點子就要做出來讓大家感受那個好笑感。 我說要做個會「BB」的閘門,我就真的做出來。大家到展覽現場,就會看到汪正翔真的做了一個閘門。我覺得這件事很好笑、很有快感。
Q:你在書裡提到當代拍照的媒材轉變,小至手機攝影、修圖濾鏡,大至舉重國手郭婞淳抓舉瞬間的照片使用遠端遙控拍攝。我們很熟悉的街拍、新聞攝影等較注重「現場」和「隨機性」,但當代對這兩者的注意力似乎漸漸消退?
A:早期的現代主義攝影大師對構圖的講究不只是因為好看,而是他們認為把畫面裡隨機的元素串連起來,可以傳遞一個更抽象的真實狀態。從古典藝術到到現代藝術,「隨機性」都是證明藝術家有創作能力的一個重要方法。可是如果完全不理這一套,難道攝影就沒有別的實踐藝術的可能嗎?
不過隨機性如果消失,有一點會蠻可惜的。當我們愈來愈不仰賴隨機性的拍照方式,現場已經都被事先安排好,或者用遙控的方式拍運動攝影,我覺得現場帶來的細微體驗會消失。我說的現場體驗不是那麼紀實攝影取向的,而是一種很超現實的經驗,我看過一篇講 3D製圖的文章,他說 3D製圖或電玩場景設計的視覺美學其實非常保守,我們都以為科技會讓人天馬行空,但其實沒有。作者認為是因為人不在現場,無法感受那種現場的神祕體驗。
譬如你在現場拍草,跟你回家在電腦前要畫出一片草皮,意義不一樣。你用繪圖軟體畫草的時候,你調動的是你腦袋裡已知的草地模樣,可是我們每次拍照都會感覺到,現場拍的草跟你想像的就是不一樣。不管你經過那個草皮多少次。
Q:照片與空間之間的關係也發生了很大的轉變,現在最頻繁生產與發布影像的空間是社群平台。你覺得這種「展示空間」的挪移,是否對攝影有所影響?
A:對大眾來說,社群媒體早已是發布照片的主流管道,這導致影像愈來愈「關鍵字」化。在社群媒體上要吸引人,一定要讓人快速有感覺,而讓人很快有感覺的常是符合某些既有關鍵字的影像,社群媒體上的照片可能乍看很炫,但是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些照片愈來愈模式化,模式化才會讓人快速上鉤。社群上的影像不會反映真實,IG 裡的人都長得跟真實不一樣,連黃曉明這麼帥在抖音都要套小臉濾鏡。我不確定這會對攝影或藝術帶來什麼影響,我只是覺得這蠻有趣的,值得關注。視覺文化有比較多這樣的討論,但專門談攝影的書裡比較不講這些。
Q:21 世紀初期,部分影像學者對公民在社群上發布影像、使用自媒體抵抗暴政還抱持較正面的態度。如果以現在 2022 年的台灣為基準思考,你覺得影像對發聲或理解現實還有任何作用嗎?
A:極權政府帶來的網路監控很容易感受,可是臉書的網路控制也一樣誇張。我現在都不敢發裸體的行為藝術照,有次發了就被擋發文三天。臉書資本主義的控制力比想像中大太多了,大家的發文會愈來愈「安全」。
另外一個例子,我在書裡提到的華山「草原自治區」。按理來講那是一個具有烏托邦性質、想反抗現實世界的表現,當你發現來草原的人都是為了拍張照上傳到網路,就知道真正主宰我們的不是暴力或軍隊,而是網路機制。我們不知不覺就受到網路機制支配,所以任何影像或者生活方式到網路上都會變成「一個樣子」。影像受制於演算法,一切都均質化了,幾乎沒有逃脫的可能。這方面我比較同意中平卓馬,中平是一個左派,當年他的照片卻被東京鐵道局拿來做觀光宣傳,於是他發現,再有能動性的影像都會失效。中平所看到的問題現在只有更嚴重。我們的社會沒有像早年那些影像學者想像「透過影像去中心化的權力分散,讓世界變得更好」那麼樂觀。
我們上面談論的問題,其實是被表象取代的「景觀社會」之後,人要怎麼去回應的問題。我自己的方式是避免成為任何群體的一員,因為權力都是透過各種機制去影響你,它隱藏在公司內規、藝術圈內規,甚至社會對道德的一些正向看法之中。我要避免這種幽微的機制干預。一開始我們聊到我的各種身分,這些身分有點像是我維持中立的方法,我看到藝術圈,我可以說我是攝影師,我看到攝影圈,我可以說我是創作者,有的時候我寫評論,又可以跟所謂的創作拉開距離。這對我來講是很重要的,這個有點白癡的方法讓我保有自己的判斷。講起來有一種「我就廢」的感覺,可是我覺得在控制無所不在的當代,「我就廢」是一種滿積極的態度,可以拒絕任何機制對我的干預。
Q:你書裡的〈如何在影像中呈現「亞洲」〉及〈華國美學〉都有相似的國家、地方美學命題。身為台灣當代的影像創作者,有沒有一個跟這個身分相關的題目,等待你去發現?或者說,影像有沒有所謂的「台灣性」?
A:剛剛我一直在說自己不關心現實,但奇怪的是,我的作品都跟台灣相關,以前拍台灣的木屋,後來拍台灣的風景區、台灣聖山,甚至把「外拍」講成台灣的習俗。以我自己的創作經驗來說,「台灣性」是很好的東西,因為它就發生在我們生活周遭。可是我覺得另一個面向是,如果「台灣性」不是你的出發點,而是你的終點,那創作就會很受限──如果你的目標是要建構一個台灣主體,那你用解構的方法就背道而馳。我覺得我對台灣這件事,就像我對任何以社會議題為題材的創作一樣,可以從這方面出發,但是終點一定不會是台灣或是社會意義。
Q:書裡也觸及很多藝術、政治與道德的角力,社群時代藝術家因為道德被「取消」時有所聞,你如何看道德與藝術關係?
A:現在大家比較不接受藝術歸藝術、道德歸道德。有些道德有問題的藝術家,我們會說他的道德爛、藝術就爛,但這個說法有一個危險性,就是你把藝術跟道德連在一起了。所以當你說道德先於藝術,其實你仍是認為兩者會互相影響,因此「道德好,藝術就會好」。走到極端會變成,這個藝術作品那麼好,那他道德一定高,或是道德問題可以忽略,這反而是不對的。如果真的要解決藝術跟道德之間的問題,我們就應該徹底的把藝術跟道德分開談,你可以基於他的道德,否定他做為一個人的價值,但是你不能說他的藝術很爛。
就算這個說法成立,它應該在什麼範圍之內行使也是一個問題,所以有時候我覺得這只能「在嘴巴上說說」。我們嘴巴上討論複製人的技術,或是我們討論最敗德的藝術如何帶來美感,可是當這件事情實踐出來,帶來了不好的社會效應,這就成為一個道德問題,藝術家不能干預,你不可以說因為我有崇高的藝術目的,所以帶來的壞效應不重要,就像你不能為了講一個好笑的笑話去傷害誰,你不可以這樣自我說服。你如果認為藝術很重要你就做,但你要接受自己也許在道德上站不住腳。我覺得一切都可以依照道德標準,但是,我唯一堅持的是,你要相信藝術自有「另外一個標準」,只是要怎麼實踐這個另外的標準太困難了。
Q:所以如果你是觀眾的話,你不會因此再也不看這樣的作品?
A:我會不讓人家知道我在看,自己偷偷看……
Q:那如果有人詢問你對相關事件的想法呢?
A:我會說我沒看啊。
Q:所以目前完全沒辦法實踐,只好先在臉書上發發廢文?
A:對啊。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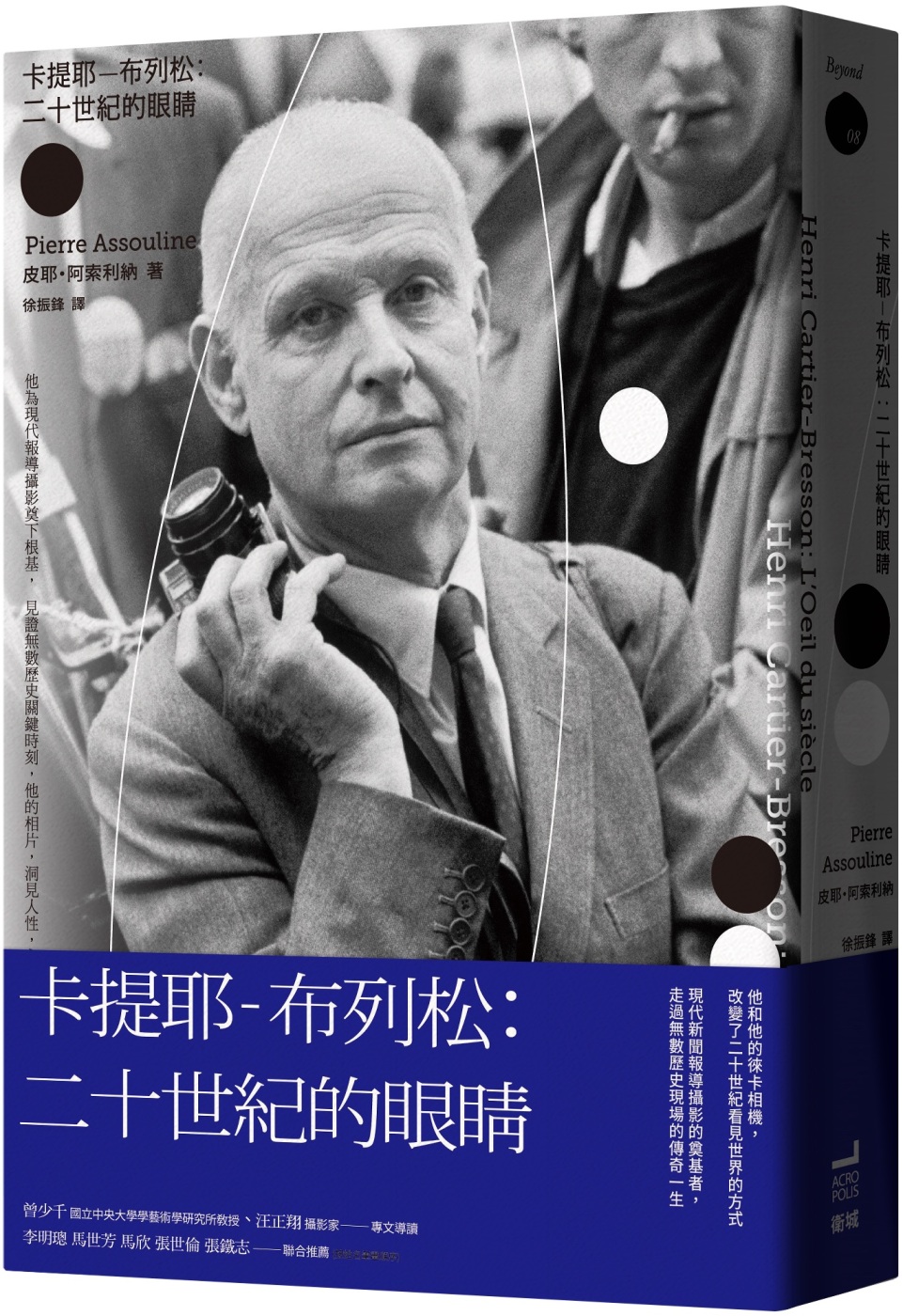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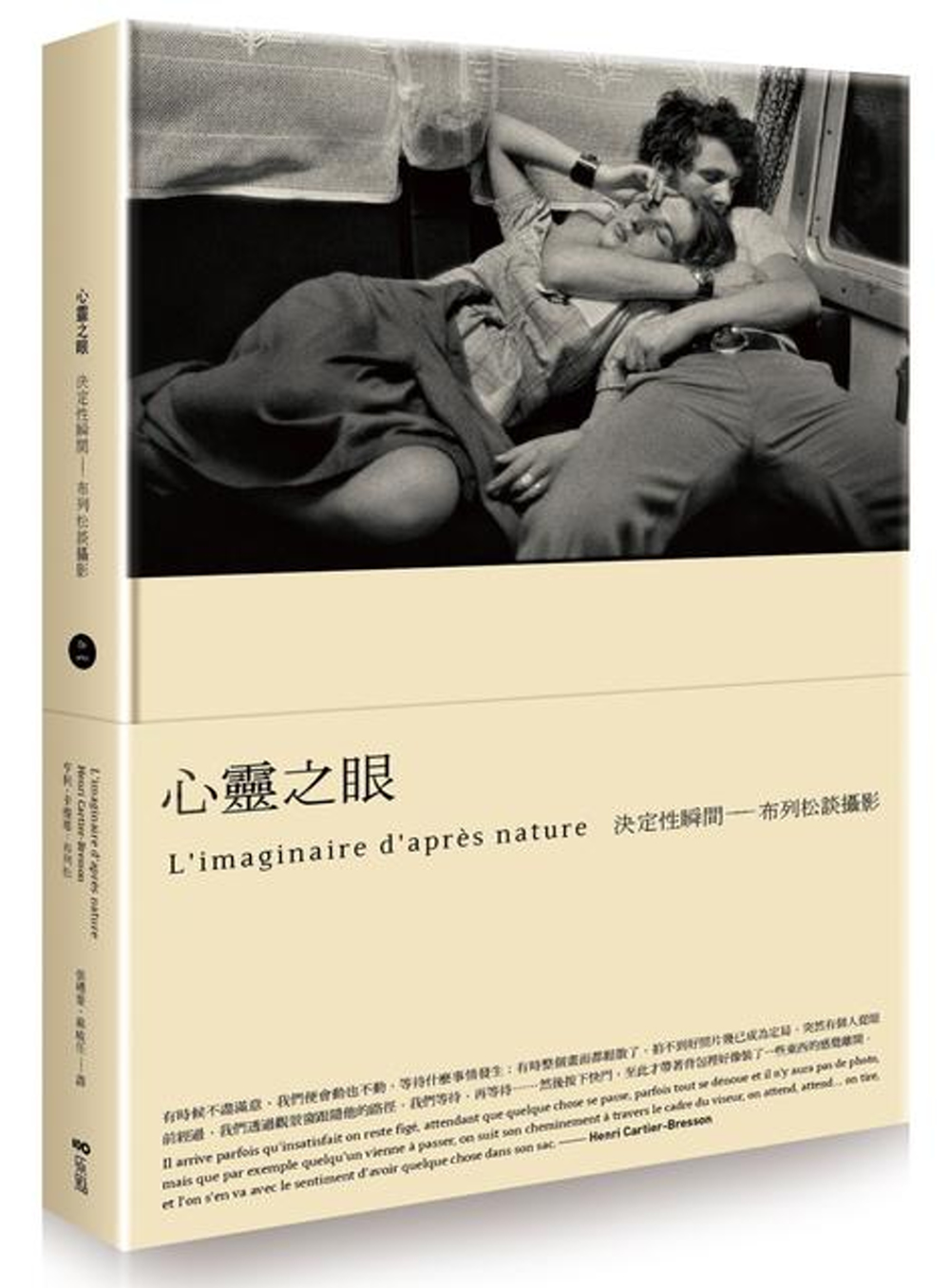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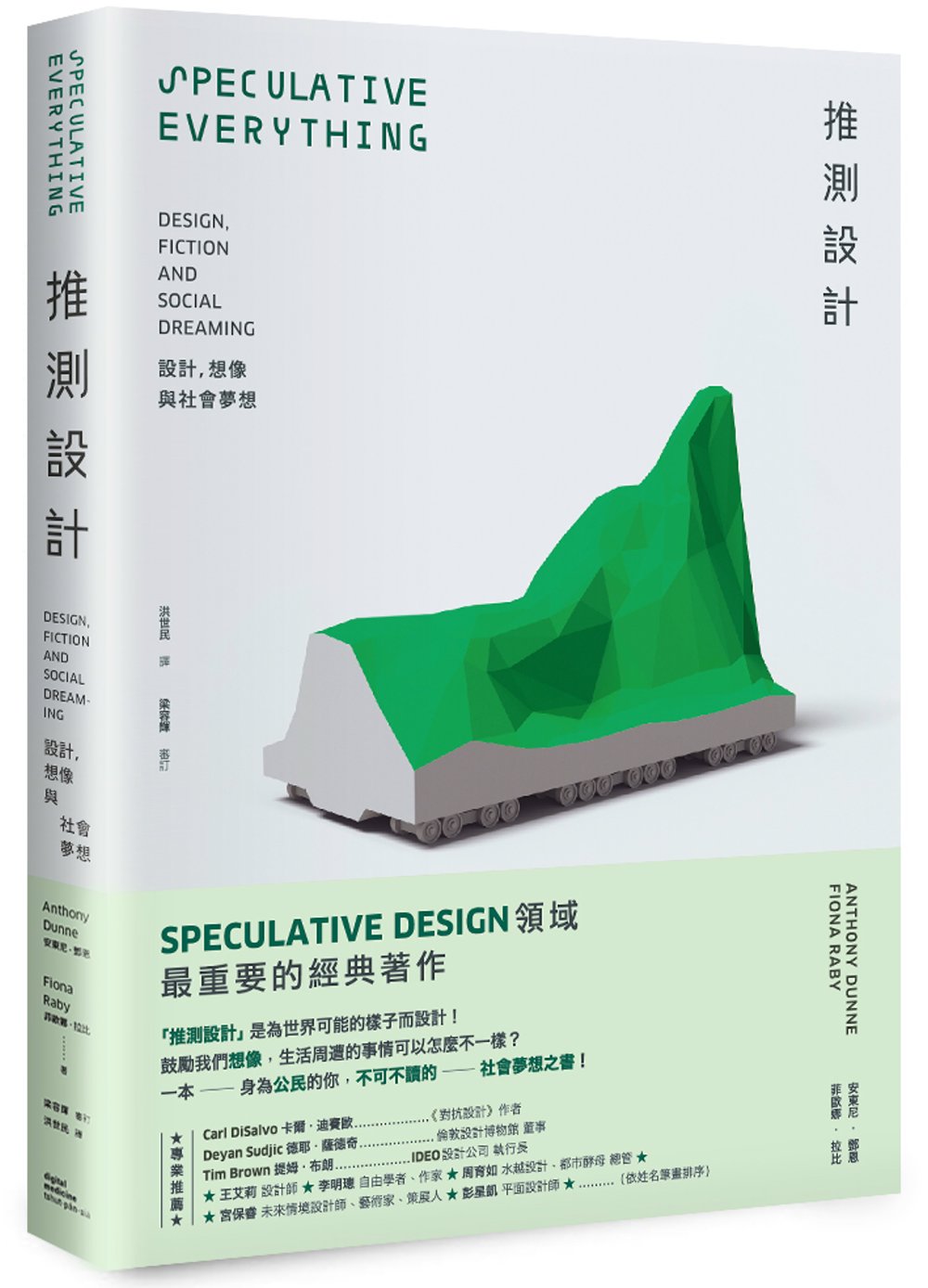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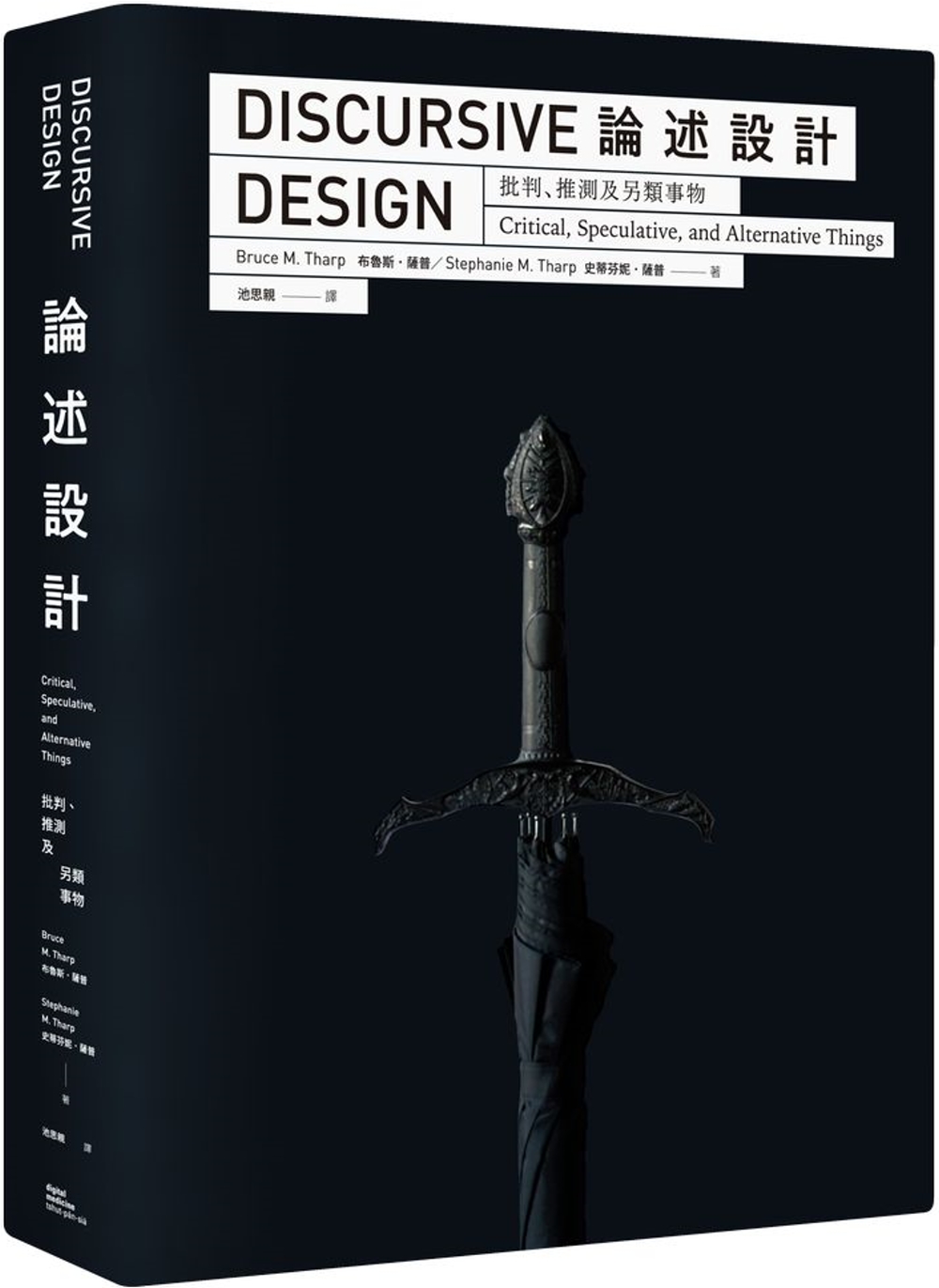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