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室報告】
青春博客來與織錦文學獎合作,節錄刊登優秀作品。
織錦文學獎為北市中山女高一年一度的文學創作活動,由女青社主辦,至今已經連續舉辦二十三年。 此文學獎提供校內喜愛文學、懷抱熱忱的學生們一個自由創作與發表的平台,期待能透過這個活動,讓學生有機會展現才華及想法,也使學生能從中學習,提升校園內的文學創作風氣。(中山女青第63屆提供)
青春大作家 ╳ 織錦文學獎 ╳ 2020散文組首獎

校安專線:02-2509-0833
文/中山女中 劉詠瑄
感覺自己最庸俗的時候莫過於上公車。
暗自計算初時速二十,一萬六千三百公斤重物體,在幾秒後將靜止於我面前三步處,經過數百次演練,偏差值已小到允許忽略。我竄過握著咖啡的上班族,掠經理應禮讓的老奶奶,再插在同校學妹前頭。
抱歉了學妹,這是競爭。我用緊繃的眉心低語道。
我蜷縮在塑膠皮椅上,冰涼和黏膩是公車座椅的標準配備,好像一條以人類皮屑體液維生的蛇,怎麼知道牠嗜食眼珠中最亮那處,每日舔舐。兩年流逝,光芒總也逐漸消去。椅面上兩條蒼白浮腫的大腿貌似正在發酵的麵團,柔軟且尚未成形,我總習慣用書包壓著,以為這樣物理上的抵禦已足夠應付鄰座潮濕溫暖的手掌。
搭公車從何時開始竟成了一場攻防戰?
第一次是高一的時候,我像所有中山女高的學生一樣把小藍短褲繡在身上,上車或者昏睡或者背背英文雜誌,除非瞄見那幾個大安高工的挺拔學長,隔壁乘客不曾被我放在心上。上班族大叔或者花襯衫婆婆,我側頭熟睡,唯一擔憂是不小心睡到光華商場,得多出五分鐘上學路?。
一次再平凡不過的早晨通勤,我平凡地坐著小息,感受隔壁平凡地沉下,原本還在想要不要偷看是不是那個總戴鴨舌帽的大安高工學長,暗笑自己俗濫的少女情懷後,我沒有睜眼。
「我應該要的。」這是當天日記裡唯一的一句話。
如果睜開眼就能知道他長相特徵,如果睜開眼就能投遞警告眼神,如果睜開眼就能增加警戒,如果睜開眼,我就能知道他在摸上我裸露大腿時的眼神有什麼成分。但我沒有。我只是閉著眼,默念蔣勳的〈願〉,告訴自己這只是一場夢靨,而夢靨往往與事實相反。我模仿母親的嗓音,夾雜熟練到可以反著背誦的詩句,命令雙腿停止顫抖。那只是短暫的兩三秒,他的手掌一觸即離,也沒有任何抓握的動作,就只是放著,再拿走,觸感卻深刻烙在我皮膚上,彷彿遭處炮烙之刑——但我沒有犯罪,對嗎?剩下的路程中仍沒有一絲光線潛進眼皮,一直到不得不下車,我才再度釋放肌肉和淚和呼吸,而臨座早已餘溫散盡。
那天之後我有幾週寧可在晃蕩中勉強穩住自己,於四十分鐘的車程中不斷變換重心,也不願坐上灰褐色漆皮刑椅。是,我無罪,我冤枉,但此案已結不允上訴,只留我難看地怨嘆,咒罵天理不公世間冷酷;像一個傳統社會中的寡婦,委屈卻也知曉自己定有過錯,大抵是天譴吧。
第二次我不記得細節了,只能確定又是一個平凡早晨,不過那時候我早就不再寫日記,平庸的繁雜瑣碎沒有紀錄價值,不如多算幾題簡諧運動。日後再憶才發現黯淡竟也有其路徑可循,但那都是後話。再次行刑時好像就不那麼痛了,至少能容我攢積力氣撐開眼皮:他的眼珠是黑色的。像家裡的大樓管理員,像捷運上頭髮梳高的上班族,像我爸,像所有有黑色虹膜的人。隨即他轉頭,然後下車,而我只記得他與一般人無異的雙眼。
沒有第三次,或許該感激我逐漸黯淡的面容、下垂的唇角,或者被消光的眼眸,我沒有再遇過第三隻手。
高中生活是這樣的,百般演練後我總算擠進一個無數人坐過的褪色空隙,卻把那絲冰涼誤當作新鮮感,縱容自己在日復一日的庸俗瑣碎中被打磨鍛礪,露出底下最最鮮麗的吊鐘花粉紅,而後蒙塵。原來座椅是這樣製造。
「下一站,長安松江路口。」按下下車鈴的時機往往需縝密考慮,不可提早也萬不能太過緊迫,這項規言對於熟睡的學妹也一樣重要,何況我身為一個亟欲逃離公車凝滯空氣的顫抖靈魂。不同於上車時的競爭,我跟在學妹身後步下階梯,短暫的一小段斑馬線,我轉向左側:松江路的陽光穿過台北清晨的清冽空氣迎面襲來,補足了我方耗盡的星芒,於是我邁開頹軟無力的雙腿。
下車後的女高中生,完全恢復社會化,謙遜有禮,努力不拒絕伸到面前的任何一張傳單:好一優良公民——如果撇眼不看她腿上手掌大深痕。
作者簡介

「
石平。
擅長與自己作對的矛盾存在,喜歡美、跳舞、水和蔣勳,討厭俗氣、趕路跟過短的指甲。
總是嚷嚷著自己的骨清高,總是毫不猶豫把髓賣了換酒。
期許自己未來某天可以不再執著於逃離。
」
看更多得獎作品
1.【青春大作家X2019織錦文學獎】新詩首獎:關於我愛你
2.【青春大作家X2019織錦文學獎】散文首獎:印
3.【青春大作家X2020織錦文學獎】小說首獎:看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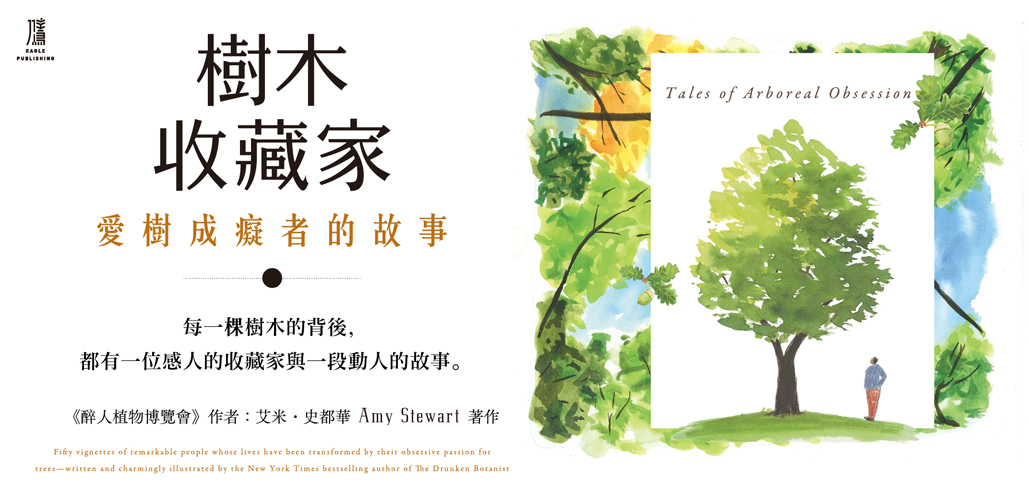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