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室報告│星空燦爛,像無數燃燒的小宇宙,創作的能量正在爆發。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為什麼要寫?要怎麼繼續?本企畫邀請六位深受年輕讀者歡迎、高中校園文學獎評審經驗豐富的作家,擔任三大文類導師,請他們回溯養成、相談創作之路。看青春與創作怎麼碰撞、怎麼摩擦?原來現在厲害的大人們,在創作的最起步也曾經猶豫徬徨。老師們又想給年輕創作者什麼建言?請看我們的訪問────
回溯養成:我對寫作一直都有一個不太公眾性的傾向,它是隱密的,
在世界的反面先完成它自己,才能是世間意義上的作品。
Q.還記得你的第一次發表的作品嗎?那次的發表對你人生的影響是什麼?
言叔夏:如果不計校刊或《國語日報》的話,我想第一次發表應是《自由副刊》的某個徵文。那時我約莫是高三,進大學前。投稿的稿子還是用手寫在稿紙上、很謹慎地對折放進信封裡,騎腳踏車到家附近鄉下雜貨店的郵筒寄出的。因為這個徵文,進大學後某一天忽然接到副刊主編蔡素芬的電話(那是一個編輯與作者的關係還很古典的時代),問我在哪裡讀書,以後若有稿子能寄給她。大概這樣維持了數年斷續通信,將稿件寄給我從未謀面的作家(這時就是電子郵件了),有時會刊出來,有時不會,但總會在信上談些什麼。其實蠻溫暖的。那時也常覺得,寫作這個工作很神祕,好像你跟收到這稿子的人之間有某種共同的秘密任務。可能是因為這樣,我對寫作一直都有一個不太公眾性的傾向,它是隱密的,在世界的反面先完成它自己,才能是世間意義上的作品。
Q.成長背景曾帶你創作養份嗎?你是怎麼使用(或遺棄)這個部份?
言叔夏:書寫者應該很難完全規避所謂的「成長背景」所帶來的影響,即使不是以題材的方式出現在作品裡,我想它也必然會消融進行文的節奏、腔調與文字的孔竅裡。我常覺得自己的作品裡有個背景音很像小時候地下電台的台語抒情歌,即使行文的內容和它完全無關,但那BGM就像小時候搭父親的車,老式錄音帶在車廂裡反覆A面B面地播,有個女人唱著鼻音很重的歌曲,南方的雨就斗大地掉落在父親的擋風玻璃上,雨刷唰唰的聲響。這個聲音常讓我覺得莫名有種安心感。我不太清楚這或許也是一種介入?但如果若要為我自己的書寫勾勒出一種類似底圖的東西,大概是這樣。
Q.曾讀過哪些顛覆你對散文想像的作品?
言叔夏:我對散文一開始沒有很固著的想像,沒有預設散文應該怎樣,所以散文對我而言一開始大概就是一種說話的聲腔。當然,話說著說著也會莫名地漂浮起來,這種狀況是常有的。有時走到自己都沒想過的路。我喜歡這種繞路的作品。那常常不是慣寫散文的作者的作品。如夏宇的某些單篇散文簡直是迴旋舞。我記得她寫過在屋裡有好幾張不同桌子的事,寫詩的一張,寫歌的一張,真的很簡單,但那種簡單的、幾乎是爵士鋼琴的單鍵裡有一種很個人性的東西,不跟著她一起繞路是不會得知那個謎題的。
Q.作品遭受批評、負面回應時,如何調適心態並堅持下去?後來做了哪些調整?
言叔夏:很年輕的時候難免會在文學獎的評審場合遭遇這樣的情境。當然當下常常很難從那些隻字片語的評斷中理解評審真正的想法。年輕的時候,其實很多技術常會有一個很像石頭般、壓在路中央的檻,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很難把它搬開。其實多年後想起來偶爾也會發出:「啊繞過去不就好了。」但那時好像整個身體與文字都躲不開那個障礙。我想我能做的可能就僅是坐下來陪那塊石頭一陣子。如果它來自我的身體,也是我的一部分。
精進技藝:即使擁有與他人類似的經驗素材,也沒有人會寫出一樣的作品的。
創作畢竟不僅只是一個輸入原料、產出產品的過程。
Q.你覺得好的散文最必要的條件是什麼?
言叔夏:散文的必要條件可能是「作者的聲音」,這是很微妙、很難形諸文字或規範的一種條件。那很像在KTV包廂裡所有人都點了同一首歌來唱,但唱出來的聲腔、轉音、甚至一個節拍的頓點,都完全不同。仰賴於一個作者如何同時駕馭語感與意義的共振。
Q.你認為創作是可以學習的嗎?你平常是怎麼精進自己的創作?
言叔夏:創作當然是需要學習的,而且學習的方式可能素樸、古典得不可思議。我覺得那其實很需要一種類似手藝人般日日溫習的手感,其中,重複可能是一種最重要的工作。所以過去常聽說寫作者抄書的練習。為了保持這種手感,我過去則常有隨身帶著小筆記本的習慣。不見得要記下些什麼,也不一定是文字,有時只是看不出意義的線條或插畫,像是採集人拿著捕蝶網蒐羅昆蟲那樣的工作,有點類似村上說的,在腦海裡擁有一間儲藏室,裡面不需整齊收納,但容許收容經驗的碎片。也類似班雅明的說法,某一日這些看似無用的瑣碎廢墟,會回來給予你啟示,你不會知道你什麼時候會被它所救贖。
Q.平時如何蒐集素材當作創作時的靈感?創作者眾多,如何避免與他人太過雷同的思考方式?
言叔夏:至今我仍覺得睡覺與作夢是創作最重要的一個環節(?)。當然我說的不見得是真正的睡覺。但確實很多時候,身體一旦鬆懈下來,文字就會自己找上門來。現今這個時代畢竟已經超級碎片化,其實作者要保持某種經驗上的完整性是很困難的。當然作為一個已在工作的前中年人,睡覺與作夢仍是相當奢侈的。故我現在常常喝很多水,使用牛飲方式,有時候水穿過身體時也會喚醒一些不是頭腦能掌握的事。至於如何避免與他人太過雷同的思考方式?保持社交距離或許是唯一解?但我其實仍認為即使擁有與他人類似的經驗素材,也沒有人會寫出一樣的作品的。創作畢竟不僅只是一個輸入原料、產出產品的過程。
致創作新鮮人:窠臼一旦成為慣性,是會妨礙某種思考上的可能性的。
Q.散文創作需要新人的理由?
言叔夏:其實每個文類都會持續有新的語言、語感生出,所謂的「新人」,也許是提醒我們地球仍有持續運轉下去的可能,它還會說話,也會唱歌,而即使我們活得再老,都可能會因為這些新語言的湧現而感到仍活著是一件還不錯的事。就像地殼底下仍有火山活動那樣。
Q.你參與過或評審過印象最深的高中校園文學獎是?為什麼?
言叔夏:應該是雄中雄女與道明合辦的馭墨三城文學獎,這個獎我從過去是參賽者、得獎者,一直到十數年後的今天,變成評審者。我高中和所謂的文學社團、校際間的文青寫作者是很遙遠的,但因為這個獎而知道了一些那個時候也在寫作的一些人,像林達陽、黃信恩等,過了這麼多年,這些當年的人也仍在寫著,其實蠻不可思議的。它很像一種年輕時就結下的什麼記號,當船往前動時,可能劍已經不見了,而記號還留在船身上,某些時候,它什麼也無法做;但某些時刻裡,你還真的有點需要憑藉它來記得一點什麼。
Q.你認為現在年輕的寫作者優勢是什麼?
言叔夏:我常很驚訝現在年輕的寫作者基本上已經沒有過去那種沉痾的負擔與界線了,所以常能走到我們所難以想像的地方。比如表達的媒介與形式,有時甚至會讓我覺得手裡只有文字的我輩此代,好像燧人氏在二十一世紀還高舉火把。媒介的物質基礎必然會改變一種觀看形式,也定會產生完全不同的主客體關係,相當期待下一個世代能開展出一種完全不同的感覺結構。
Q.評審過這麼多的作品,你認為現在年輕的寫作者最常犯的錯誤是什麼?
言叔夏:我不知道能不能這麼直截或粗暴地將它歸類為「錯誤」,但我比較常在高中校園文學獎裡看到的是一種比較安全的結構。這些結構包括時間的線性、篇章的佈局(起承轉合過了二十年竟仍然是暗黑勢力),還有太想快點給出一個確定的結語。其實十來歲的時候誰真的知道起源與結局是什麼?硬要在文章裡「合」,我覺得這不僅只是一個修辭的問題,而是語文教育的哲學本身似乎在起點上就搞錯了什麼。當然它是一個作文邏輯上最基礎的訓練,但有時也不免覺得似乎它變成了中學時代開始寫作的某些人的一種窠臼,而窠臼一旦成為慣性,是會妨礙某種思考上的可能性的。
如何定義散文 ?言叔夏X林達陽線上小對談
言叔夏:我認為散文的定義可能不會是由外部的技術去賦予的,對我來說,如果它有界線的話,那界線可能就是作者的「心」。如果散文是植物的話,「心」大概就是它的塊莖。散文的語感、聲腔、觀看世界的方式……都是從這塊莖裡長出的。
林達陽:覺得太厲害了XD,完全同意。如果也用比喻來說,我心裡的散文或許是一幢房屋,有遮風避雨的屋簷牆壁,有門鎖,有窗戶,有書和掛畫和紀念小物。有鑰匙,遙控器,密碼鎖著的電腦,可能是我的,也可能是別人的。
我最喜歡的散文,或許是一台符合這樣敘述的露營車,讓人安心生活,而且知道隨時都可以繼續上路。
林達陽:我對於散文的定義是──從自己既有的情緒與知識中,整理、進而創造出某一具有未來性、獨特性的自己。
這樣講或許有點太抽象了,如果取巧一點說,或許散文是「替未來更成熟的自己,陪伴過去更天真的自己。」
言叔夏:我很喜歡達陽說「繼續上路」的概念,或許散文的路就是作者的路吧!路會被走舊、走老,也可能踩踏出一條全新的小徑。換句話說它其實是作者生命本身修羅場的折射,跟作者每段時期的眼界、際遇與腔口是不可切割的。這麼說起來其實散文是相當殘酷的文類吧!
新星點名
潛力新星推薦:陳心容
推薦理由:我印象中在去年的高雄青年文學獎裡讀過一篇題為〈北風〉的作品,我與同場的評審都很驚訝作者只有十五歲。後來在頒獎典禮上見到作者本人,她發表的談話簡直不是中學生(其實那次頒獎典禮有許多年輕的寫作者都說了極為超齡的感言)。該怎麼說呢?那是一種在複雜的世局中,仍帶有一種質地上的乾淨,越過了文字與口語的形式,展現了作者這個「我」的獨特姿態。很期待一直能讀到她的東西。
三文類X六導師X致創作新鮮人寫作備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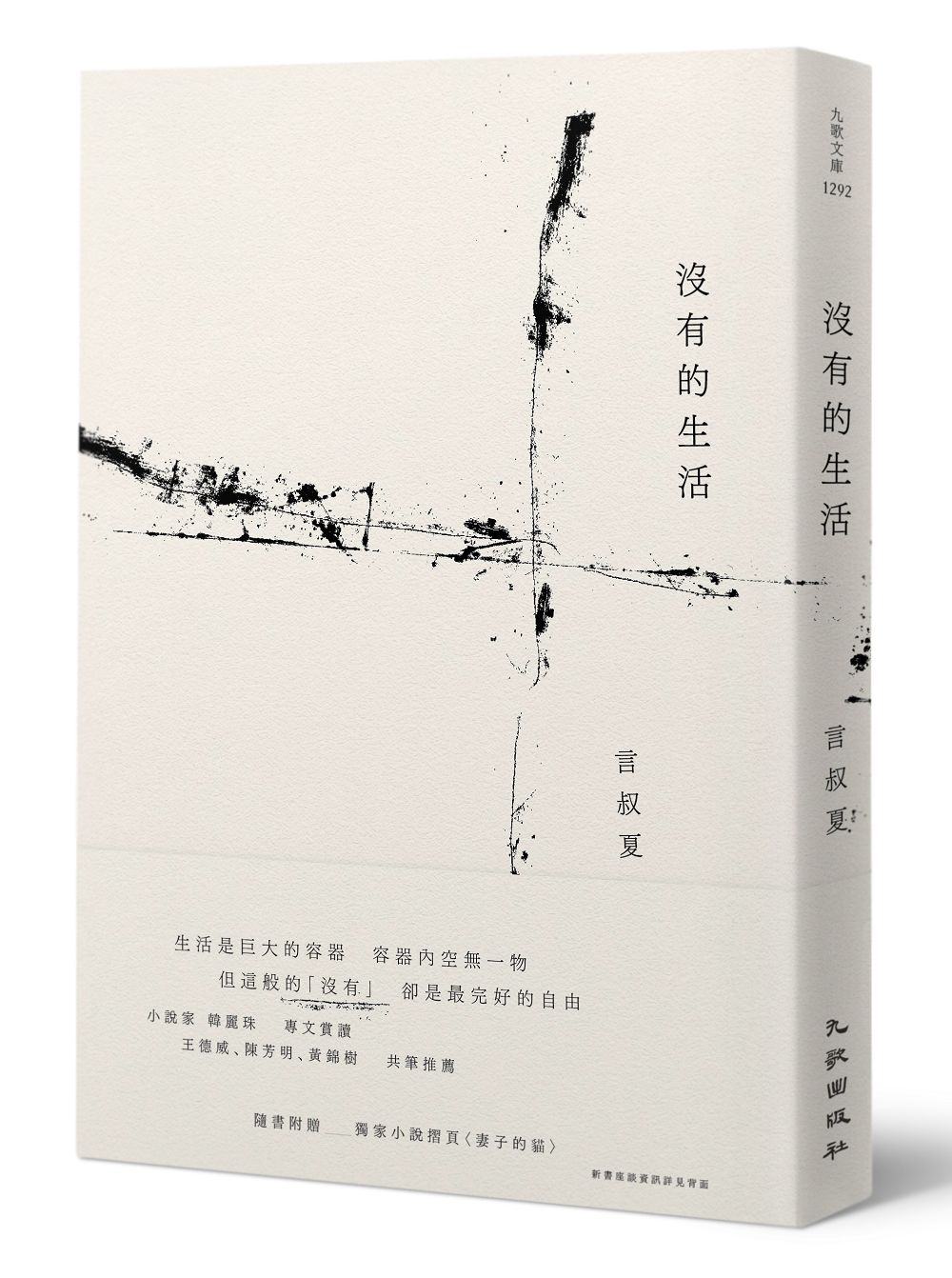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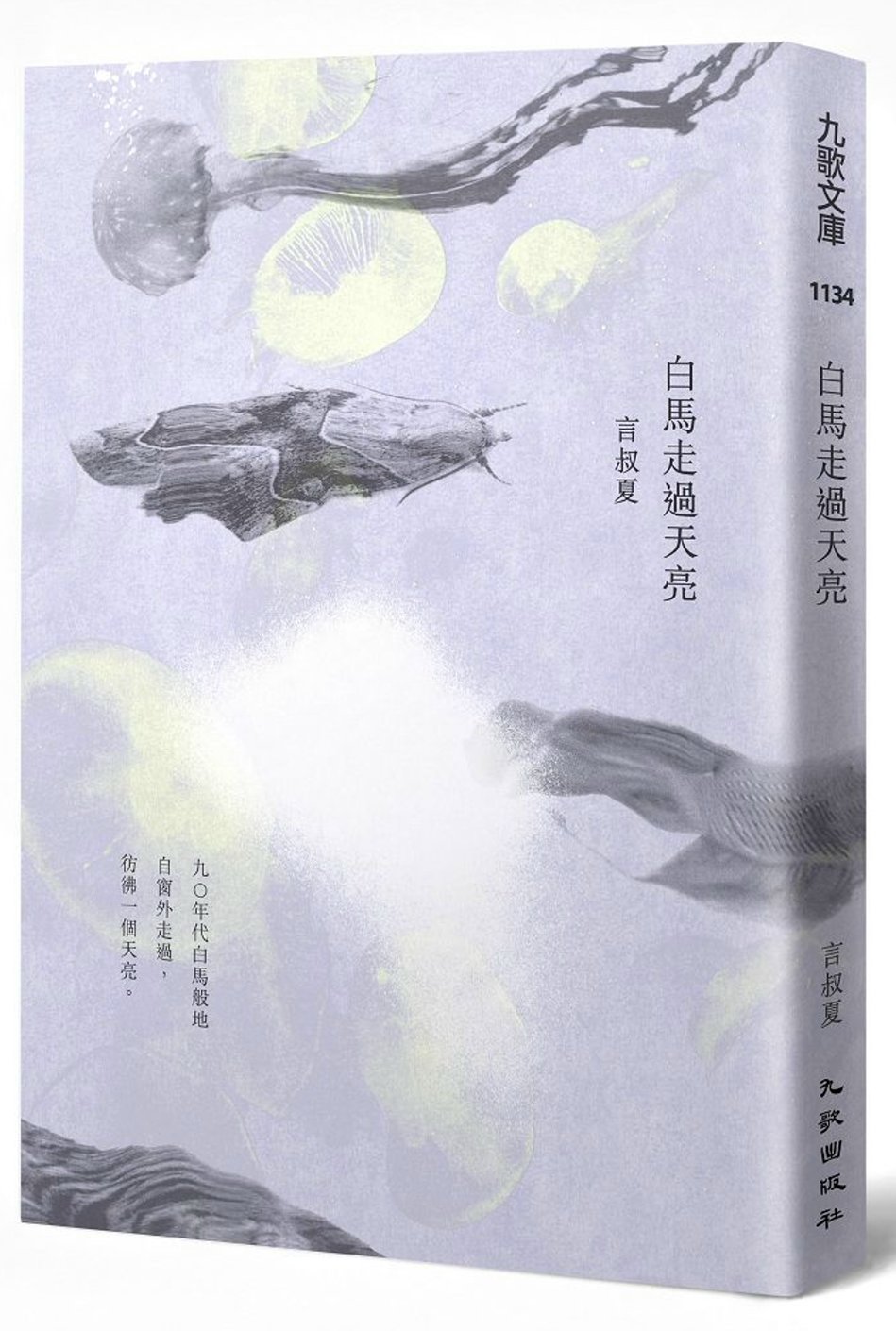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