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幾年前,一位訪問者問我,台灣的自然書寫是否正在衰微(正確的用詞我忘記了,但大意如此)?我說我不以為這樣,台灣的自然書寫正在演化,演化的趨勢是:科普作品會持續出現,且愈見多元,具有感性文筆的科學研究者會更願意寫作「和個人經驗有關」的自然相關著作;而文學出發的作者,會動搖「純文學」的定義,類型文學會更加蓬勃,而也會有愈來愈多喜歡文學的下一代,同時具有難以取代的自然體驗,寫出「根植於台灣」的自然書寫。
我當時提到一些名字,這些名字有的不幸在這幾年早逝,有的還在蘊釀第一本著作,有的則已出版第一本,或幾本書,但暫時還得不到兩方的肯定——文學以及自然科學。因為每個領域都有其「固定」的「肯定辦法」,這是好的自然書寫者往往「晚熟」的原因,他們得跨過幾個領域的基本門檻。不過,我相信他們終究如看似各自獨立的星系,彼此以神祕的引力相互聯繫著,時機一到,星圖自然浮現。
這篇文章,我意不在推薦特定作者或作品,而是想以一個曾經是這領域專業研究者的身分,概略性地談談,這些年台灣自然導向文學幾道演化的軌跡。
在西方的自然書寫(nature writing)研究裡,一開始研究者多半認為「非虛構」是現代自然書寫的重要特質。在非虛構的書寫系譜裡,有幾種類型或者用詞,比方說科學書寫(science writing)、歷史書寫(history writing)、傳記(biography)、論述性散文(essay)、報導書寫(journalism Writing)、自傳(autobiography)、個人經驗散文(personal experience essay)、抒情性散文(lyrical Prose, lyrical writing)等等。當然,這些類型不是可以涇渭分明地分開的,自傳與他傳自然也可能是歷史書寫,歷史書寫裡不乏使用抒情散文的筆法,當然,科學書寫也可能帶著個人經驗。但無論如何,讀者始終假定這類書寫有一個隱性的規範,叫做「非虛構」,這並非說這類書寫全無虛構或不能虛構,而是部分類型可以允許想像的虛構筆法去呈現(但不能虛構事實),也就是說,它們仍能以文學筆法去表現。不過,一旦讀者發現其中有經驗虛構、知識虛構、敘述虛構,它將很可能失去讀者信任,在評價上也會降低。比方像「新新聞」的寫作可以讓記者用像小說般的筆法去寫作,但材料必須(在寫作當下)是可靠的,至少有來源的。
你或許會敏銳地發現,我把這種信任感約略做了一個排序,從科學書寫到新聞書寫,幾乎都偏向具有「公共性」,因此它們如果一旦虛構,失去讀者的信任是理所當然;後幾類則較有「私人性」,它的經驗虛構與否比較難以查證,但一旦被讀者發現,也大多會失去讀者的信任,不過也不乏讀者寬容地認為,後幾類文字表現的魅力(文學性的一種),是極重要的特質,它會形成強烈的個人寫作風格,也就愈難辨識虛構與否。
自然書寫一開始被限定在光譜較強烈「公共性」書寫的一端討論,但因為有太多科學寫作者同時也具備敏感心靈,因此他們的筆記、文章,也會呈現抒情性;再加上有許多業餘的觀察者、探險家、自然愛好者也會試著參酌科學知識與觀察經驗寫作,他們的作品並不在追求「科學研究」這領域的評價,更強調個人經驗,自然也就更易被以文學觀點來評價。
還有部分的寫作者寫作的就是虛構文體——小說,以及以個人抒情性為根基的詩歌,這些作品,更難只以科學價值來衡量,因此,便有研究者(如派翠克.墨菲〔Patrick Murphy〕)用「自然導向文學」(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來稱呼這種現象(自然書寫指非虛構作品,自然導向文學則包括了虛構作品與詩)。自此,自然相關的書寫的討論,遂滿布非虛構到虛構的光譜,生態批評者甚至擴散到其他學門,讀者藉此觀察到了這類寫作多元且有魅力的演化,展示出人類與自然之間關係的思考。
我想藉幾本台灣近年出版的書,來說說這種演化,對一個如我這樣讀者的魅力,因為是重點舉例,掛一漏萬難免。
2
在接近科學書寫的這一端,自然史作品《繪自然:博物畫裡的台灣》(胡哲明等著),鳥類科普書籍《噢!原來如此:有趣的鳥類學》(陳湘靜、林大利),植物地理學的《通往世界的植物:台灣高山植物的時空旅史》(游旨价),乃至於植物愛好者胖胖樹(王瑞閔)關於熱帶雨林的通俗著作。這類作品,大概沒有人會認為其中可以含有「虛構」成分。而在評價這類著作時,相信也會以其資料是否翔實、科學研究的陳述是否周延為主,再來才是書寫者的個人眼光(包括敘述方式或情感表露)。
這幾本精彩的科普書,都讓我驚喜地發現年輕一輩學者的投入。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像《通往世界的植物》裡兩位自然繪圖家:黃瀚嶢與王錦堯,以及《噢!原來如此》的陳湘靜,都不只是傳統藝術領域的繪者,他們都出身自然研究專業。這種現象,最能說明它們的藝術性,根基在於「非虛構」與「科學性」之上的要求。

而另一批較從人文學門出發的寫作者,則偏向以個人經驗為主,擷取相關研究成果進到他們的著作裡,這類寫作有強烈的抒情性,好的作品會謹慎使用研究資料(而不是憑自身的好惡),他們或許沒有研究實績,但也會運用細膩的觀察能力,偶爾帶給專業研究者啟發。
不過,這類的作品價值重點還是在於與自然互動後獨特的經驗與思考反芻,因此,文字的抒情性裡最迷人的莫過於「情緒」、「哲思」以及文字技巧烘托出的「氛圍」,再加上對自然議題的「批判」。
曾與我有短暫師生之緣的劉宸君的《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可為代表。宸君和同伴梁聖岳在喜瑪拉雅山南坡附近山徑失蹤47天的事件是國際關注的新聞,離世的宸君從我認識他時就是個重度的書寫者,他的閱讀經驗以文學為主,其他登山知識、自然知識為輔。在受困山區時他寫稿不輟,遺稿經過梁聖岳和同樣愛好寫作的朋友羅苡珊整理後出版,書中從登山經驗與渴望出發,加上絕境時的心理變化,透過宸君特殊氣質的文筆表現出來,是一部不可再復的動人絕筆。(每回提到宸君,就讓我想起一樣正要發光時早逝的廖律清。)
此外,如栗光《潛水時不要講話》和山女孩kit的《山之間:寫給徒步者的情書》,也是這類調性的寫作。作者以自身的熱情從事自然活動,從許多層面獲得啟發,最概略的分述不免就是自然經驗裡最有魅力的科學知識以及美學上的陌生感——透過作者具有感染力的文字,自然會呈現出與一般文學作品相異的氛圍與魅力。
這裡還有一個重要的觀察點是,過去提到台灣的自然書寫,會提及的女性書寫者名字大約有徐如林、凌拂、阿寶、洪素麗、杜虹、張東君、蔡偉立、黃美秀……等等,但這五年內出現的女性自然書寫者,恐怕在這類作者裡比例過半,這在過去四十年來的台灣自然書寫史裡在比例上之高是罕見的。
因此,得知張卉君和劉崇鳳兩位已各自出過幾本書的作者,將合出一本名為《女子山海》的對話集時,不免覺得這書名或許可以用成標識台灣女性自然書寫者階段性形象的標題。

3
徐如林是登山、古道專家,凌拂開創的是植物書寫的路向,洪素麗以觀鳥為書寫主軸,杜虹則具有國家公園解說員的身分,阿寶是女農,張東君、蔡偉立與黃美秀則是專業研究者。這樣的多光譜面相,實則已可讓研究者繪製出一幅女性自然主義聲譜圖。這幾年的新進女性寫作者,則將這幅聲景的音域擴大中,崇鳳與卉君是值得注意的兩位。
崇鳳與卉君都是文學系所畢業,但兩人皆與傳統的文藝女青年的路向不同。崇鳳熱愛登山並成為嚮導,後曾申請壯遊後生活在都蘭,復回美濃隨家族耕作。本是文藝青年的卉君也曾在美濃參與在地團體,因緣際會來到花蓮加入黑潮文教基金會,一面學習海洋與鯨豚知識,一面投身環境運動。兩人從大學走來一路扶持,一路交換山海經驗,可以說《女子山海》的對話裡,體現了自然書寫考驗、養成,以及從文學出發作者在投入環境運動的辛苦歷程。

寫作個人經驗散文對她們來說並非難事,她們大可像一般的文藝青年寫類似的內容,然後投稿參賽。但我相信她們深入這個領域後,面對的第一個難處是自然科學在近數百年來突飛猛進,許多純感性的觀察若缺乏知識做為後盾,對多數讀者來說都只不過是一己的情思而已。那些感嘆自然風光的作品,美學力道已然遞減,難以長期打動讀者。
第二個難題是,當她們願意面對自身知識面的傾斜,而投身其他領域的知識體系後,又會發現所有的知識體系或許能解決「理解」層面的問題,卻很難處理環境議題社會化以後,在政治、經濟、社群層面上的糾結。於是另一個難關隨之而來:就算你懂得說明、分析問題所在,你願投身去解決問題嗎?
於是,這類作者從抒情性出發,卻隨著寫作愈走愈遠,終究來到「公共性」這端的光譜。他們或投身環境運動,或投身實地實踐,耗滅了一些青春,換取對實際議題的一些發聲權與能力。只不過,最終他們又會發現寫作可能被文學的評論質疑──這樣的寫作,還存在著文學性嗎?
我在觀察崇鳳和卉君的寫作,正是經歷了前兩個階段的追求與自我懷疑,現在正在第三個階段的門口徘徊。因為在黑潮工作,我與卉君較有說話的機會,曾不只一次聽她提及自己的疑惑。她不像同輩的寫作者獲得文學上聲量的肯定,但她又清楚地知道,自己這些年在環境運動、科學調查參與上的許多細節,充滿了人性與自我掙扎,那不就是文學的根源之一嗎?同樣地,原本只是熱情登山,而後返鄉耕作的崇鳳亦然。每一個實際參與生產的耕作者,都知道耕作不像棄官回鄉書寫田園那般清爽自在,耕作是體力的考驗,販售時將是耕者與巨大體系(現代產銷機制)的互動與對抗。這是在這類寫作者身上無可取代的經驗,卻也常常是傳統的文學批評者,無法從其間提舉出「文學性」的緣由──光是文學技巧,並沒辦法說明這類作品的價值。
《女子山海》正是崇鳳與卉君以往復信件形式來表現這些年來她們信仰、懷疑、轉變的剖白,對我來說,這是她們的真情寫作、身體寫作。沒有之前作品的包袱(環境運動者的身分、登山嚮導的身分……),不掉書袋,重點放在敘說自己的觀點、自己的記憶,引出自己轉變向「非文學科系式」的人生,而又深深受文學影響的生命經驗。
正如崇鳳所寫:「多慶幸我們回不去了……我們有幸看著一個海灣如何改變她的面貌,我們學會面對欲望」,又如卉君和崇鳳共同認識的,那個有著傳奇浪漫身影的阿古所說的:「起手不回隨風去。」
她們有時寫著自己的經歷,有時寫出對對方的想像,寫到面對自然時的寬闊、陰暗、死亡與救贖,偶爾觸及到生而為人與其他生物的差異,以及投入人世時對教育與改變他人觀念的思考。她們的作品都還提到「組織」。組織如何吸引、消磨熱情,卻也打磨她們的思考與行動。組織不是必要之「惡」,而是必要之「痛」。組織讓她們打消念頭,也促成行動。
這正是我要說的,卉君和崇鳳作品裡的價值。她們兩位或許在三十年前,都會發育成台灣女性散文家所追求的:談論成長經驗(如《擊壤歌》)、以詩詞文學做為抒情的聯想(如簡媜早期作品),或是追求某種優雅文化的美學(如林文月的作品)。但她們同樣以女性觀點出發,面對的卻是野地與野性,時而多感傷情,時而天真爛漫,時而包容孕育,時而帶出她們以性別出發的批判性。這裡頭的文學思考,體質已大不相同。
崇鳳談到雌性之美,香與髒的辨證(傳統我們總把前者歸給女性,後者歸於男性)、一般人對山間嚮導的刻板性別形象。卉君則以自身投入環境運動,時常被以性別的角度特殊看待的經驗,思考自己脫下「公鹿角」的過程。她們意在訴說,一個少女、女人、情人、妻子、媳婦,同時也是一個嚮導、農務者、NGO團體的執行長時,看待事物的方式有何特殊之處,而又是如何演化出她們此刻的視野。
對我來說,這就是《女子山海》的魅力。
而徐振輔的《馴羊記》,則是非常具有野心的寫作。
多年前我在振輔還是高中生的時候見過他,那時他已顯露文字天賦。我心底暗暗相信,以他的天賦,很快就能在台灣現行的一些單篇文學獎獲獎,走上他期待的文學之路。當時他問我,對於未來就讀科系的選擇,我當然不敢踰越自己的身分給予任何自以為是的建議,但我提到,如果是我再一次選擇的話,我應該不會再選擇文學系所就讀。因為以我個人年輕時對文學與藝術的熱情,那些師長們後來帶我讀的作品,即使我不讀文學科系,也都會在自己主動閱讀的範圍之內。至於文學批評理論或相關哲學對我來說也從未造成閱讀困難,我相信振輔亦然。
振輔後來就讀了昆蟲系,那正是一個從閱讀領域、研究方法,以及周遭群體都不同於文學系所的地方。
漸漸地,我聽聞振輔獲得一些獎項的消息,也在專欄裡讀到他的文字。那些他遠赴異地的生態紀錄,除了一再證明他的文字天賦外,也顯露出驚人的消化能力。他把他喜愛的國外自然書寫者、科普作品成功地消化在自己的寫作裡,而且不妨礙他散文的文學質素。我幾乎可以看到他若出版一本散文式的自然書寫,將會引發的讚許評論了。如果要說有什麼我自以為是覺得可惜的,大概就是在科學領域裡,他似乎沒有找到自己專注的「研究題目」。這可能是他的興趣太廣了吧。
不過振輔是一個有熱情、有冒險精神;更重要的是,有野心的作者,他選擇寫作這本《馴羊記》。這本作品依他的說法,包含了抒情性散文、知識性散文,也包含了小說的形制。這形制在我的觀察裡,類似於後設筆法的虛構術。小說內容時間跨度分別是七世紀的吐蕃王朝、中國1950至1960的革命年代,以及1980後的社會情境。而在內容上,則鑲嵌了人類學、生物學、人文地理學、社會學、宗教等等領域。
不過在我看來,這仍是一本自傳性強烈的作品。它雖然融合了大量非虛構資料,但其間的文學美學脈絡是清楚的,只要對文學有一定閱讀基礎的讀者,相信能在其間看到熟稔的班雅明、馬奎斯……。但像我這類讀者,才比較容易注意到它的美學精神,是根植於北美自然作家約翰.海恩斯(John Haines)。這對我來說,相當於一個創作者的「閱讀自傳」。
故事的主體是「我」尋雪豹的旅程,加上旅程中各種耽誤、錯過以及偶遇,帶出各個篇章,包括了一部稱為《馴羊記》的日本人宇田川慧海著作,振輔刻意把現實和虛構做了讓人更易混淆的機關。
簡單地說,《馴羊記》裡的《馴羊記》,以及〈豹子對你而言是什麼〉和〈雪雀〉是這部作品刻意暴露「虛構」文體的章節。宇田川慧海的《馴羊記》出現最重要的目的,便是在與自我經驗的非虛構部分做一個對照。對一個旅行者來說,路上經驗當然為真,但所聽聞的地方故事,包括從書中讀到的各種紀錄,都很難確定為「真」。那個「真」的認定建立在我們對書寫的信仰,對話語的信任上。但事實上,書寫與話語,都是容易造假的工具。振輔在這裡刻意用了容易顯露「假」的虛構文體,帶著讀者去感受他聽到的那些故事,讀到的那些似假還真的資料。
也可能是振輔的入藏之旅,讓他驚覺「圖博」這個詞的多層次精神,實在無法光以抒情或知識兼具的散文去表現出來。唯有運用虛構文體,把多個角度的時空與思考,不著痕跡接縫起來,才能表達他的「心意」。我想振輔的書等了這麼久,等的就是這個「結構」吧。不過,這些結構在藝術上是成功抑或失敗,還得經過讀者的認肯。
《馴羊記》的寫作,宣告了振輔的寫作並不想從自我經驗開始而已,他帶著更宏大的野心。這個宏大的野心也暴露他的寫作(或所有困難的寫作)是如何誠實面對力有未逮之處。人尋找豹子(有時為了打獵有時為了拍照有時為了紀錄)、豹子獵殺牲畜、人尋找人,人獵殺人,人馴羊,人也馴人。而唯野性如雪豹不可馴(尋)。
振輔的筆法老熟,已是一個成熟作家的樣貌,讀者進入這樣的一部作品,尋的是雪豹、故事的痕跡,以及振輔若有似無地要讀者去「尋」的一些物事——人與生物、環境的相處,和人最珍貴的那一絲覺明——唯有人(應該吧)會困陷其中的,關於生存的意義。
做為振輔寫作的同行,我不想去評價他這部作品的優劣價值,可能是因為我自己體驗過所謂的「寫作之路」。振輔的天賦讓他的寫作帶著野性,也因為天賦讓他的寫作帶著自我期許,因此想像雪豹一樣躍過絕崖。我得說這部作品讓我對振輔印象深刻,因為任何生命最有活力之時絕非「天人合一式」的譫妄與偽和諧,而是充滿野性的野心。那是種子不擇手段地散播術,是候鳥不辭千里的遷徙,是哺乳動物被家族逼走的擴張。
5
我相信未來幾年,會有幾位面貌各自不同的的寫作者會跨出不一樣的步伐(如還未出書的林怡均、羅苡珊、白欽源……),我像一位天真的自然書寫讀者,持續期待與觀察這個文類的演化與火花,這是老去的上一代唯一能做的事。演化安靜,卻從不回頭。
※ 我個人為免人情世故的麻煩,一向不為自己學生以外的書寫序(為自己的學生寫,當然就是生命有交會的私心)。但數本與我有因緣的作品出版邀我寫文章時,遂想到可以用過去研究者的身分來寫一篇綜觀的論述。這篇文章可能會收入不同的書裡或媒體,不是偷懶,而是不講述完整脈絡,單一作品的區位與價值便不易體現,讀者當可諒察。
作者簡介
現任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有時寫作、畫圖、攝影、旅行、談論文學,副業是文學研究。
著有散文集《迷蝶誌》、《蝶道》、《家離水邊那麼近》、《浮光》;短篇小說集《本日公休》、《虎爺》、《天橋上的魔術師》,長篇小說《睡眠的航線》、《複眼人》、《單車失竊記》、《苦雨之地》,論文「以書寫解放自然系列」三冊。
曾六度獲《中國時報》「開卷」中文創作類年度好書,入圍曼布克國際獎(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愛彌爾‧吉美亞洲文學獎(Prix Émile Guimet de littérature asiatique),獲法國島嶼文學小說獎(Prix du livre insulaire)、日本書店大獎翻譯類第三名、《Time Out Beijing》「百年來最佳中文小說」、《亞洲週刊》年度十大中文小說、臺北國際書展小說大獎、臺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金鼎獎年度最佳圖書等。作品已售出十餘國版權。
吳明益專訪:
《苦雨之地》,太初有字──重新定義小說的可能:專訪吳明益
細節打造的聖殿──吳明益《單車失竊記》
《浮光》吳明益:最初之火微小而明確地被點燃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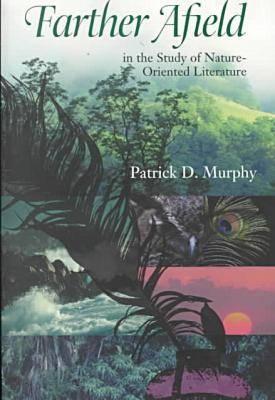
![繪自然:博物畫裡的臺灣[精裝]](https://www.books.com.tw/img/001/084/75/001084752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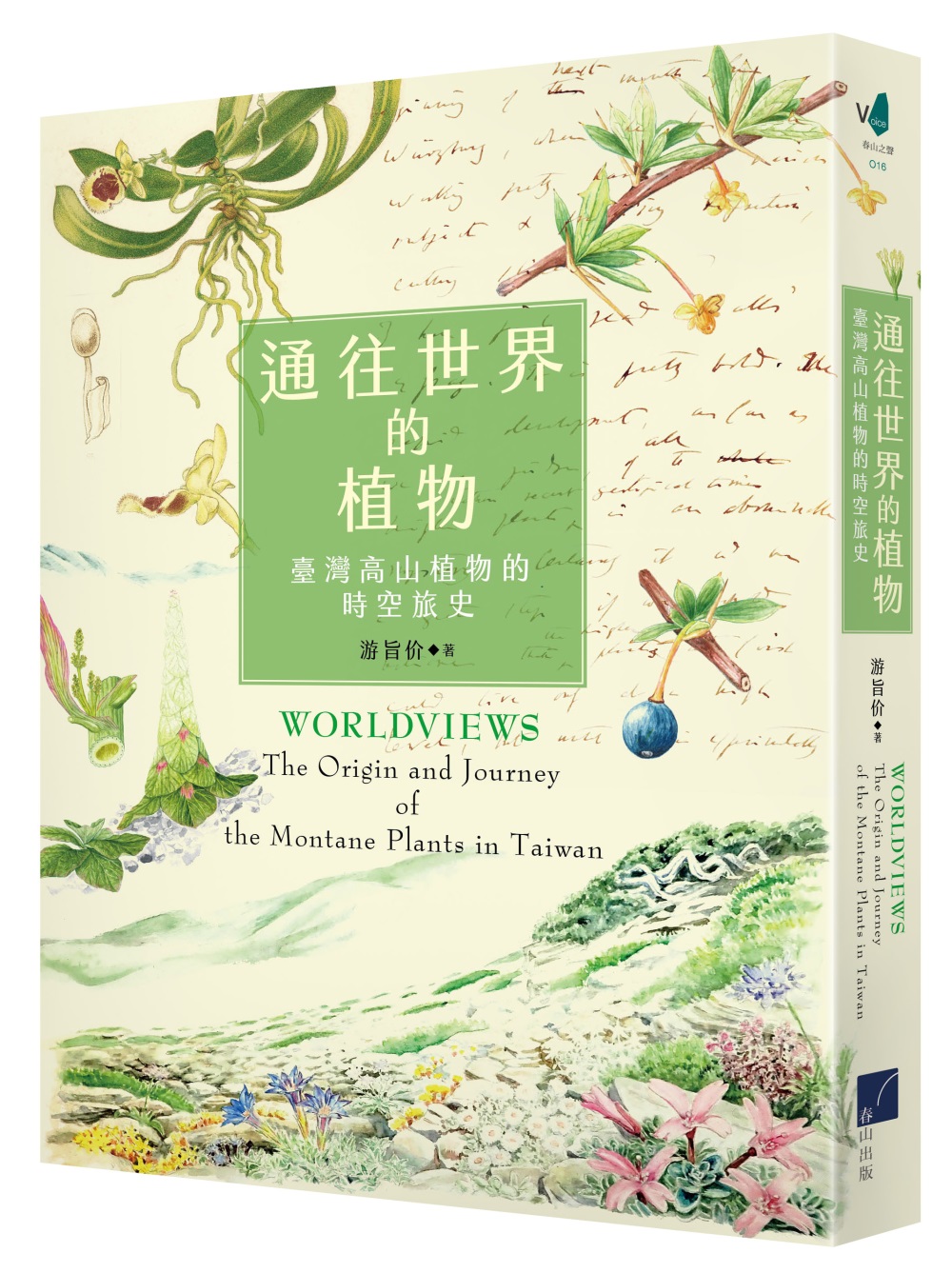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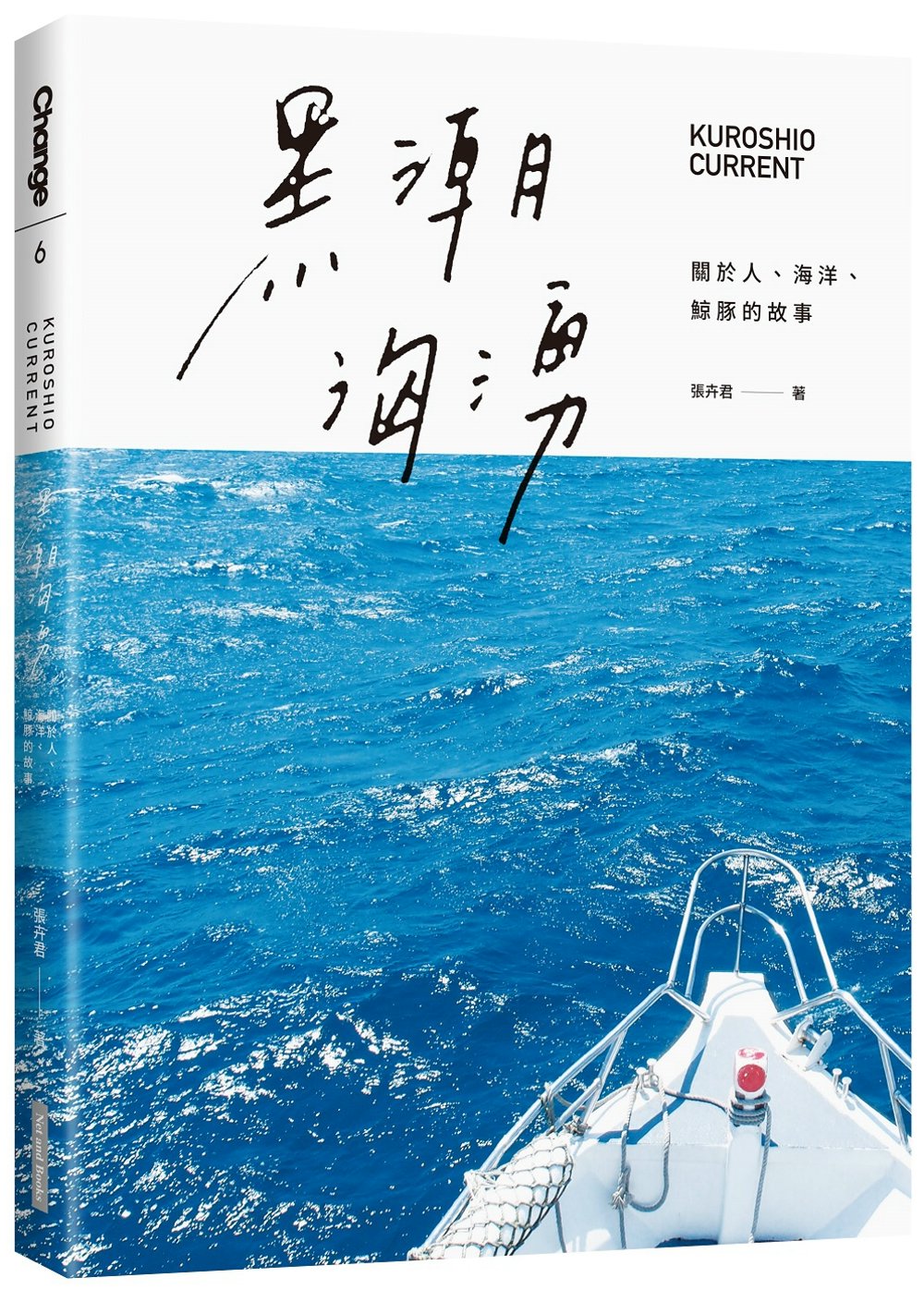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