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校早稻田大學畢業的青柳碧人想必頭腦很好,寫的推理小說也是「理科系」。他的《浜村渚的計算筆記》裡,恐怖分子透過教學軟體催眠了日本國民,要求政府全面提升全國的數學程度,否則就要開始無差別殺害人質;青春洋溢的《利根川莉莉佳的戀愛實驗》裡,最討厭科學的高中女生,竟然與古希臘科學家阿基米德、還有數學家牛頓等,展開了奇妙的同居生活,研究起她以前不感興趣的白努力定律與牛頓運動定律。
而到了去年,不按牌理出牌的青柳,又推出了一本大受歡迎的推理小說,名為《從前從前,某個地方有具屍體》:我們都很熟悉童話裡「從前從前」這種開場白,而這本小說,自然是一本取材自童話的推理小說。桃太郎、一吋法師、開花爺爺、浦島太郎等等日本人耳熟能詳的童話角色,或成為了命案的被害人、加害人、嫌疑犯或是偵探。當然,既然都有屍體了,這次這些童話也不一定會以老套的「可喜可賀、可喜可賀」做結。浦島太郎的龍宮城化為密室、桃太郎出征鬼島變成連續殺人事件、開花爺爺死前留下了死亡訊息……與看來刻意搞笑的封面、還有「改編自日本童話」這種人畜無害的宣傳不同,《從前從前,某個地方有具屍體》更像是推理版的《令人戰慄的格林童話》,你絕對不會想讓孩子們看到這本「偽童話」。
《從前從前,某個地方有具屍體》火速登上2020年度各式推理書榜之列,這只不過是說明了童話推理的魅力之一。
殺人不知何時變成了一門困難的生意,有屍體還不夠,讀者想要的是獵奇的屍體、難解的殺意、還有奇峰迭起的推理過程。簡單說,讀者期望在推理小說裡體驗的不只是追凶,而是顛覆的過程──否則讀者光看每天刊載偵破刑案的報紙社會版新聞就能滿足。我們在推理小說中期望的「一期一會」,是出乎意料的顛覆、是讓平凡生活失色的非日常驚喜。而童話故事呢,它們跟隨我們成長,從初次閱讀、喜愛、閱讀過無數次、最終對它無感……覺得它幼稚、老套……它們已經在我們的回憶中過完一生,化為往日回憶裡最無奇的塵埃。
然後有一天,有人來告訴我們,這堆塵埃底下,埋著一具屍體。

「誰殺了知更鳥?是我,麻雀說著。我用著弓與箭、殺死了知更鳥;」
「誰看到牠死了?是我,蒼蠅說著。我小小的眼睛,看著牠死去;」
「誰取了牠的血?是我,魚兒說著。用我的小盤子,我取了牠的血;」
「誰做了裹屍布?是我,甲蟲說著。我拿著針與線,縫了這裹屍布;」
我向你保證,這首兒歌聽起來沒那麼恐怖,讀起來(或是我現在翻譯起來)才會令大人毛骨悚然:一隻知更鳥被殺了,而12隻生物準備了牠的葬禮,沒有動物哀悼知更鳥的死、更沒有動物追究開場就現身的犯人麻雀,為什麼用弓箭射死了知更鳥?而童謠平鋪直敘後續那些蒼蠅與甲蟲籌辦葬禮的過程,像是在描述他們日常的一件小事一般,這種冷漠的氛圍更像在突顯一個殘酷的事實:沒人在乎知更鳥的死……或者說,也許知更鳥原本就該死。
童謠推理比起童話推理可能更殘酷一點,因為童謠的篇幅更短,敘事空間更小,無法鋪陳複雜的來龍去脈,大多只能描述主角的行為,而留下更多隱藏在行為背後的空白心境。這難免讓小說家有了用武之地,在純真的空白上蓋起染滿鮮血的墳場。《鵝媽媽童謠》根本是推理小說家的空白繪本:〈傑克與吉兒〉(Jack and Jill)裡,兩個人到山上去取水,傑克突然從山上摔了下來撞到頭,而後吉兒也顛簸著下山──傑克為什麼會摔下山?他是被推下來的嗎?會是吉兒下的毒手嗎?

謀殺天后阿嘉莎.克莉絲蒂想要回答這些童謠背後的祕密,她的《一個都不留》(And Then There Were None)裡,被害人像〈十個小印地安人〉(Ten Little Indians)歌詞裡一個個死去;《黑麥滿口袋》(A Pocket Full of Rye)裡,童謠〈六便士之歌〉(Sing A Song Of Sixpence)卻成了偵探瑪波小姐解開謎底的重要線索;《國際學舍謀殺案》(Hickory Dickory Dock)的書名就是童謠名稱,自然故事也與童謠有更多連結;《一,二,縫好鞋釦》(One, Two, Buckle My Shoe)也是直接以童謠作為小說名稱,它更像《一個都不留》,謀殺的順序隨著歌詞進行下去;童謠〈五隻小豬〉(Five Little Pigs)本身就已經有點獵奇──誰會喜歡小豬哭叫「wee, wee, wee」那一段?《五隻小豬之歌》(Five Little Pigs)說實話跟童謠沒有太多關聯,只是剛好出現了五個死者而已,這種有點牽強附會的安排,也許證明了,克莉絲蒂有多麼喜愛在她的謀殺之中,來點令人發毛的純真童謠,讓你從此對《鵝媽媽童謠》產生心靈陰影。
西方的謀殺天后,在1940年代充分享受童謠推理的樂趣,而在東瀛,青柳碧人之前也有許多大師撰寫類似的作品:推理界宗師佐野洋在73歲高齡,寫了一本以〈龜兔賽跑〉與〈猿蟹合戰〉等等日本童話有關的短篇推理小說集《兔的祕密》(兎の秘密―昔むかしミステリー);榮獲江戶川亂步獎的將棋狂小說家齋藤榮,也在1980年代寫過以〈剪舌雀〉與〈咔嚓咔嚓山〉(這個童話本身非常殘暴)為改編基礎的《童話殺人事件》(お伽噺殺人事件);而小說家鯨統一郎,更有一套「櫻川東子系列」,描述非常了解童話的美女大學生東子,以格林童話作為破解不在場證明的武器、還要破解日本童話裡的真相,可說是一口氣顛覆東西方的童謠了。
哈哈大笑,可能不會是讀者閱讀新生代小說家陳浩基的《13.67》過程中會有的情緒,這樣說來,他最新的作品《魔笛:童話推理事件簿》裡,三篇以童話為題的推理短篇,倒可以稍稍顛覆這幾年他帶給讀者奇詭沉重的氣氛,多變的巧思仍在,但有更多幽默風趣的喜劇橋段。難得的是,不同於如今談到「顛覆童話」,便一昧染黑染黃我們印象中純真無邪的童話人物。陳浩基的顛覆,是紮實地從現實世界的物理邏輯,去合理化「解釋」童話中魔幻元素背後的機關設計。他能在2008年就有這種不走捷徑的巧思發想,可以想見今日他能每每驚訝讀者的寫作功力,並非只是花拳繡腿。
童話童謠推理不只是推理大師們喜愛的類型,在好萊塢更是屢見不鮮的改編基礎,每幾年就要推出顛覆觀眾想像的作品。喜愛哥德式美學風格的提姆.波頓,每部作品都像一部黑色幽默童話,自然免不了踏上改編童話或童謠的路線。1999年的《斷頭谷》(Sleepy Hollow),便改編自鄉野傳說演變而來的短篇故事〈斷頭谷傳奇〉(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2005年的《網交陷阱》(Hard Candy),乍看之下只是另一個天真小紅帽、踏入網路大野狼口中的悲劇重演,但這部僅有兩個演員演出的電影卻超出觀眾想像、顛覆了被害者與加害者的定位。
當然,小紅帽幾乎是好萊塢顛覆童話劇最愛的題材,《血紅帽》(Red Riding Hood)與《狼之血族》(The Company of Wolves)等電影,都試圖由愛情與恐怖類型等不同分野,解構重組這個經典的被害者故事:如今新聞報導還會用「小紅帽」來形容那些無辜受害的被害者,但在這些電影裡,小紅帽卻沒有我們想像地那麼無辜。
安徒生在他著名的童話故事《小美人魚》裡寫過這樣一句話:「人魚沒有眼淚,因此她隱藏了那麼多的痛苦。」童話與童謠的背面,有太多隱而不言的痛苦、殘忍與不公,等到我們長大、受過現實摧殘,才懂得去品嚐那些糖霜底下的酸辣苦、理解那些悲苦可以化為對人類最極致的傷害手段──有時可以化為推理小說家最殘忍的幻想,讓我們愛不釋卷。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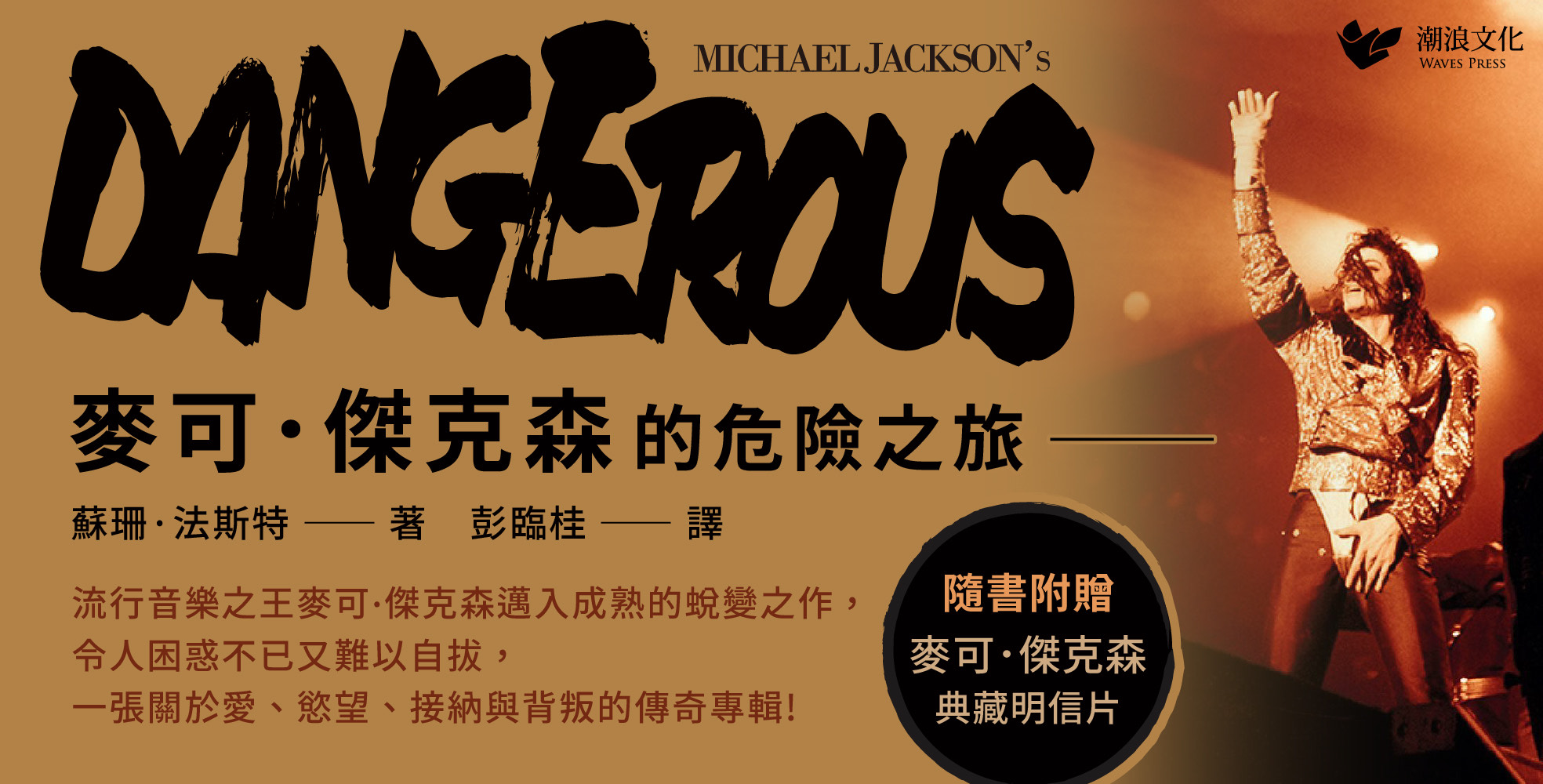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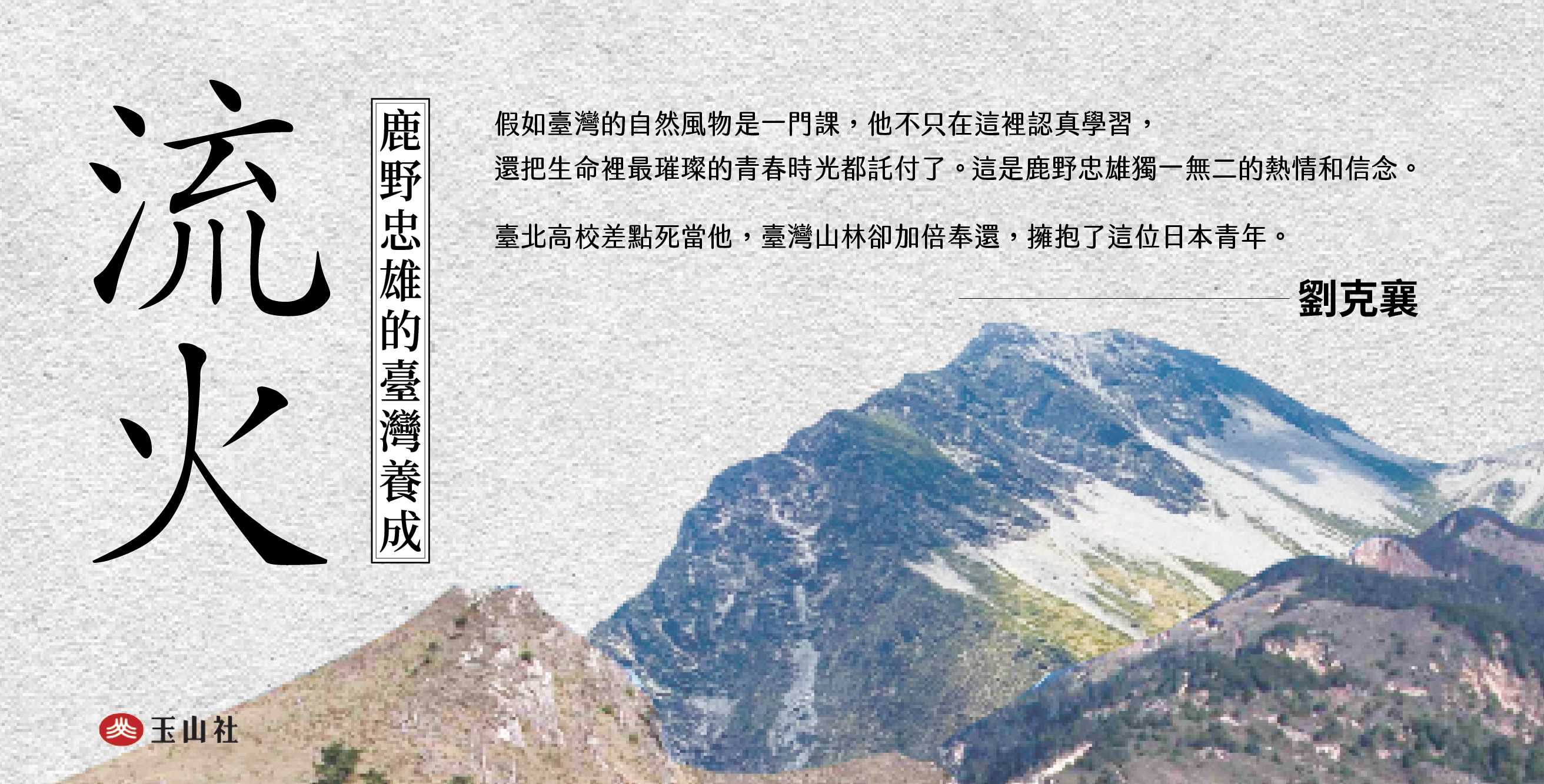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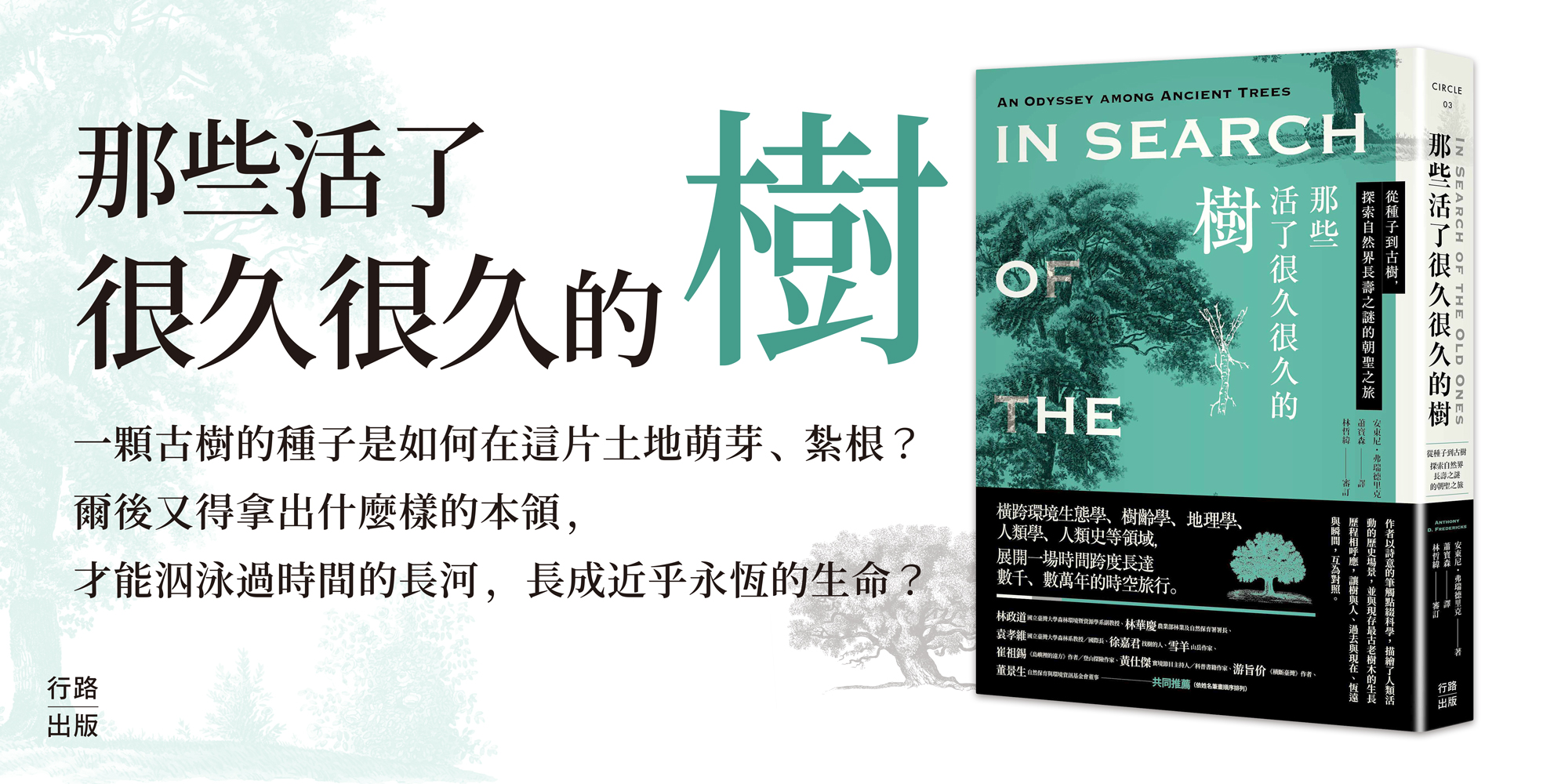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