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室報告】
青春博客來與中一中女中聯合文學獎合作,節錄刊登優秀作品。本獎由臺中一中青刊社和臺中女中編輯社共同舉辦,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為兩校學生提供相互競爭以及切磋文藝的平台,是中部目前歷史最悠久的文學獎,目前文類有新詩、散文、小說和極短。
青春大作家 ╳ 中一中女中聯合文學獎 ╳ 小說首獎

21世紀失去姓名
文/台中女中 劉格雅
瑞奇從睡夢中驚醒。他感覺身子異常的沉,而心臟留有餘悸、不穩的跳動著。在重返現實世界的那瞬他完全清醒,就像是突然從那裏,跳回了這裡。像是種逗號,卻沒有承先啟後的意義,成為突兀而又強迫接受的語句。夢境的一切彷彿是上一秒的事情,他幾乎記得所有細節,而且清清楚楚。
在夢的最後他聽見一個聲音,一個非常熟悉的聲音。那個聲音正在問他甚麼,那似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的字句間透著急切、痛苦,然而那卻成為整個夢境裡唯一模糊的印象,他努力回想那個聲音具體想對他訴說甚麼,卻徒勞無功。
他坐起身,揉揉他的一頭亂髮。深夜的低溫沁入他的皮膚,他不禁打了個哆嗦。
瑞奇走進窗台,眺望不遠處漆黑的海,底下的馬路沒有半台車經過。路燈點亮了整個海濱,沿著海岸公路一直排列到遠方。
他隨手拿了一件外套披在身上。開門、下樓,再輕輕關上大門。整個過程流暢的好像流過山間的溪澗,而瑞奇是優游在溪澗中的魚。這種完全自由的時間,使他的心輕盈的像水花。夜晚的冷寂敷在他身上,形成一種令他感覺安全的保護膜。
淺而踏實的喜悅在他心中迸發,就像仙女棒末端脆弱卻閃耀的星火,他覺得他快樂極了,他沿著濱海公路往前走,直到在路邊看見一個字幾乎都已經被鏽蝕、邊緣環繞著藤蔓植物的招牌。他走下招牌旁邊的木梯,轉了個彎,看見了那間還微微亮著燈的酒吧。酒吧下邊就是沙灘,還有近在眼前的大海。從瑞奇童年到現在的印象中,這間酒吧一直是像燈塔一樣的存在。有點神秘、但卻充滿安全感。他雀躍地走到酒吧的門口,海潮的聲音在他耳邊翻滾。
酒吧澄黃的光線給他一種走入別的世界的幻覺,瑞奇傻愣愣地眨了眨眼。角落的唱盤嗡嗡的轉著,流瀉出一種舊舊的,有貯藏室味道的歌。
「嗨。卡夫爺爺,我來找你了。今天……可以出海嗎?」
「你最近怎麼了,昨天不是才剛去過嗎?」
「不行嗎?」
卡夫爺爺為難了一會兒,也不是不行,他說。
「可你不是該為你的考試保留體力嗎?每天睡得這麼少可以嗎?」
「我知道。」有些心虛,瑞奇轉移了視線。看向一旁架上排滿的各種唱片。
「可我還是想出去。」
「唉……你想要一直這樣下去嗎?乖乖的回家睡覺,好嗎?」
「我睡不著。」就像耍賴的孩子,他用乞求的眼神看著卡夫爺爺。
「卡夫爺爺,拜託您。」
他沉默了一會兒,最後無奈地笑了幾聲。那笑聲帶著溫柔的憐憫。那是一種會讓人感覺舒服的、一種溫暖的理解。
「謝謝您。」瑞奇說。
隨著船離港越來越遠,來自海濱的光芒也越來越微弱。卡夫爺爺在船的頭尾各設了一盞照明。光照不到的地方,是全然的黑暗。
有時候瑞奇會從他的房間看出去,想像這種黑暗,一種好像所有的東西都被吸入,眼睛好像是盲的,甚麼也看不見的那種黑暗。如果那時候他獨自一人在船上隨著浪起伏、漂流,聽著海潮拍打的聲音,那是甚麼樣的感受?那是真的這樣沉重、濃稠的黑嗎?還是可以看見星星?會很孤獨嗎?會很害怕嗎?
有時候他真想嘗試這樣有點瘋狂的事,可惜他的勇氣很小,最後他還是只會躺在柔軟的床上,閉上眼睛安靜的想像。這個做法出乎意料的令他感到平靜,呼吸承著他想像的浪潮載浮載沉,於是他很快的進入深沉的睡眠。他本是容易失眠的孩子。
「蠻冷呢。」
「是啊,已經入冬了。」卡夫爺爺說。
「真討厭。」瑞奇緊緊皺著眉頭。
「怎麼了。」
「考試是在冬天的時候啊,爺爺。」
他感覺他的時間就像樹梢的葉子一樣,等它掉光了,就用盡了。本來就無法阻止的事情,卻更強調了失去的意涵,現實於是越發愁悶。其實他很害怕,卻也只能絕望地看著時間在他眼前的流逝。他每日埋頭苦幹卻絲毫沒有長進,他真討厭自己。
明明他們從小就被教誨:考試有多麼重要。你知道的,辛苦只是現在而已。撐過就好了,撐過就好了。可是那些人沒有說,一直以來都沒有任何喪志的餘裕,不管是在考試前還是考試後,在體制裡你只能不斷的往前進,不能休息、不能停止。就算跛著腳也必須難看的奔跑,如果不這麼做,彷彿就會跌進某種可怕的深淵。
船的行進切開了平靜的空氣,在那瞬間送來的風——揉合浪花與夜晚的氣味的風——給瑞奇窒息的世界開了自由而救贖的窗。他輕輕閉上眼睛,想著他
的夢與責任,而侵擾著胃的那股壓力,彷彿自己有意識似的,在他體內膨脹著。
「卡夫爺爺。」
「嗯?」
「我改天想叫科文一起來。」
「恩,當然好。」
他看著卡夫爺爺的背影,那瞬間彷彿又身處在夢境裡了,這次是更加安詳平靜的夢,他的潛意識無時無刻都在嚮往著。好一陣子他對周遭的一切感到麻木,有時候甚至感覺不到自己的存在。他欠缺一個具體的目標,萎靡後強烈的空虛感佔據著他的身軀。
在停滯、努力、迷茫、萎靡的循環中他尋求不到一個出口。更糟的是,他對於未來的不安與日俱增。比起黑暗中的大海,他對於未來的不安更加尖銳,我會去哪?變成甚麼樣子?我不行的吧?會一敗塗地的啊。到處都是危險。這是一個變動的、混亂的世界,要是做錯了選擇怎麼辦?就照著他們說的那樣前進吧?不要想著自己想怎樣了。
他們會這麼說都是有原因的。要是不照他們說的做會更痛苦的吧。他無法克制地想著,每夜在床上的蜷縮成懦弱的模樣,渴求著睡眠。
瑞奇接到輔導室的電話後,從教室裡半夢半醒的走出來。他慢吞吞地下樓梯、走過沒有人的走廊。過了很久才走進輔導室。老師面無表情地看著他,像是一種無聲的責備。
「請進來裡面坐好,謝謝。」輔導老師疲倦的說,隨手拿了一本筆記簿。
「我們接到你們班導師的消息。」他瞄了瑞奇一眼,在筆記簿上開始動筆記錄。筆尖摩擦紙張的聲音填滿整個小隔間。
「你以前不會如此的,可是現在你總是在課堂上睡覺,原本不錯的成績也一直下滑,你是否能告訴我你究竟發生甚麼事呢?」
「喔……不,我不知道能告訴您甚麼。」
「除了讀書我也不能做任何事啊。」瑞奇緩慢的一個字一個字說著,像演員在排練時斟酌台詞。
「我們擔心你和科文最近的狀況,我們擔心許望帆的事影響你們太久。」
「聽著,我們可以幫助你。」
「甚麼意思?許望帆的事又是甚麼?我們很好,我也很好。」
輔導老師嘆了一口氣,他疲倦的眼神無力地打量著瑞奇困惑的表情。
「我很好,真的。」
瑞奇扯開他的嘴角,展開一個不差的笑臉。
「希望如此。」輔導老師又嘆了一口氣。
「總之,接著我們會密切注意你的成績。你媽媽也經常打電話到這裡來關心你的狀況。她說,你總是交到一些壞朋友。」
批評的眼神落在瑞奇身上,他不自覺地低下頭。
「好了,沒什麼事了,只是提醒你一下。你可以離開了,你讓我們失望太多次了。我們曾經以為你是資質優於常人的學生,看來是我們錯了。」他冷淡地轉身,為自己盛一杯剛煮好的咖啡。沒有再看瑞奇一眼。
凌晨四點半,科文掙扎著睜開眼,桌上的咖啡是前幾天的,一本本講義之中夾雜著各科小考卷、模擬考卷、成績單。他不小心在書桌前睡著了,依稀記得強撐眼皮的時候電子時鐘好像顯示一點多。
「這樣下去身體會不好的。」他記得瑞奇曾經無數次的跟他說。
「你這人怎麼有資格說我。」他總是倔強的回答。
天還沒亮。科文先是收拾好書桌,打包了書包,然後帶著淺薄的睡意走出家,走過那條曲折的巷弄。一路上只聽見書包摩擦衣物、遠方車子呼嘯而過的聲音。出口的地方有家總是最早開始營業的早餐店,他在那邊安安靜靜的坐著,配著蛋餅或三明治,讀著化學或是英文。
「又看到你了,怎麼每次都這麼認真啊。」結帳的時候老闆娘用開玩笑的口吻又說,真希望我孩子有你的一半就好囉。科文禮貌的點了點頭。
五點十分,天空開始出現漸層的顏色,表層的世界往上浮起。他想,昨天夜裡的所有思緒已經不再重要了,從此刻開始,從這個善意的問候開始。就會被各種喧嚷給覆蓋,一層又一層,直到失去知覺。他的生活便是如此,和大多數的人一樣,一天又一天規律的生活著。規律這個詞,其實大多數都挺好的,也總是被人稱頌著。不知道別人怎麼想,可是屬於他的這種「規律」死氣沉沉。就像年久失修的機械還被強迫要持續運轉一樣,他的感覺從早上起床開始就漸漸變得遲鈍,一波接著一波的事務接力將他掩埋,他也沒有空閒再去思考。
備忘錄上排得滿滿的代辦事項,沒有一個是他真正想做的。資訊爆炸的時代,在享受著膚淺、簡單的快樂的人群裡,他偶而迷失的沉浸著。
沒關係,這樣下去甚麼也感覺不到了,他想。
在他從早餐店走到公車站的路上,他一直有種感覺,許望帆會從後面靠近他,摘掉他一邊的耳機說,「今天聽甚麼?」
她是他很珍惜的一個伙伴。許望帆、瑞奇和他,他們三個人是卡夫爺爺那裡的熟客,他們一起玩音樂,一起成長。他們會在卡夫爺爺的酒吧從早上聊到晚上,過節時在沙灘上幸福的烤肉。他們會在練團室裡說笑,準備表演、排練、彩排,弄的筋疲力盡。他們一起看海、一起吃飯、晴天雨天揹著樂器上學放學。他們某種程度上是極為相似的人,無論如何都能夠理解對方,於是更加珍惜彼此。
至少在她做出那個選擇前都是如此的。
他盡量不讓自己去想,回憶卻還是想要折磨他似的竄進他的腦袋。
「做夢很容易。但如果要做那種無論如何都要去追求的夢想,未免也太累了一點。」
他在回憶裡聽見她的聲音,那時候她曾經這麼說過。
「真的會很辛苦啊,你們敢嗎?老實說。」
「我不知道。」科文看著她。
「可能也沒有敢不敢的吧,自己也沒辦法控制啊。」瑞奇說。
「一旦有種感覺,我有自己的理念!我有想做的事!就會變得又矛盾又痛苦啊,假如那不是別人期待你的,那件事只對你自己有意義,你不只要背負罪惡感還有壓力,你還要承擔你那個夢想的重量。」
「恩……」
「所以到底要怎麼做?」
「就做好妳能做的吧。」科文思索了一下然後說。
「不然我知道了。我不要有夢想,說真的。」她想,順其自然,會成為誰就會成為誰,雖然那樣會不會比較不痛苦,她也不知道。
科文停下了腳步,看著她。
「有夢想有甚麼錯啊,很好啊。」
「是啊是啊,我也覺得……」瑞奇在一旁附和著。
就像是命運一樣,她的夢想推著她,給予她繽紛又充滿喜悅的想望。可在她說出那句話時,她只覺得無比疲憊,她沒有和其他人說過她的夢想,就像怕被嘲弄般,她將這個秘密藏的好深。她不敢做她想做的任何事。現實催促著她放棄,今天和明天,看不見盡頭。很多人不知道,那看似頑強的熱情其實容易消失,沖刷殆盡。就像是命運一樣,她的夢想推著她,也逐漸的將她推入深淵。
「我們可以好好討論一下啊。我想知道我們彼此的夢想是甚麼,我們以後要做甚麼?這樣我們說不定就會更清楚……」瑞奇說。
「可能有沒有夢想都一樣吧,開心就好,真的。」科文說,淺淺的笑著。
「開心?」
「我也不知道了,到底怎樣才會開心,我也不知道……」
起初只是緩慢的,微小的情緒震盪著,等那股能量越積越多,便會漸漸地不受控制。等到意識到的時候,壓抑的情感就會像巨浪般,一瞬間猝不及防的將你吞噬,使你意識到你自己。她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她不想看起來這麼情緒化,卻悄悄紅了眼。
科文默默地注視著她,注視著他想忘也忘不了的回憶。他想,那時她一定過得很辛苦。他感覺的到,不只是她,他身邊的人也時常感覺到不安、徬徨。在看著那些人說話的時候,會發現他們的眼神晃動著,就像搖搖欲墜的枯葉。
科文斂下眼,那時他把另一邊耳機也拿下了。慰藉的旋律還迴盪在他腦海。如果她也能感受到這樣的平靜就好了,他想。他緩緩地走向她,為她戴上耳機。
「是妳最喜歡的歌。」
「沒關係的,人生很長。妳可以、妳可以慢慢來。」
公車在他面前駛過時科文才回過神來。許望帆不在這裡,他明明知道。卻還在期待著她會在某個地方會突然出現。
她的眼睛曾經閃閃發亮、盛滿了希望,就像當初他站在舞台上時,看見的她。那時科文正唱著那首歌,而許望帆的眼神閃耀著名為喜悅的星辰。在看見她的那瞬間,他不禁想,那是個連著靈魂也閃耀著的人
成發已經過去幾個月,他們熱音社的海報卻還沒撕去。科文站在空無一人的走廊凝視著他們的海報,很容易的就能想起關於成發的一切。說不定它的潛意識裡總是捨不得離開在熱音社生活的那段時光,以至於他總是夢見成發那天的他與他們。與音樂在一起的時候,他感覺他的靈魂輕鬆的搖擺著,如果是雨天,那他會是穿著黃色雨衣在公園蹦蹦跳跳的小孩;如果是晴天,那他會是在森林裡掬起甘泉啜飲的獼猴,或是翩翩起舞的蝴蝶。與音樂在一起的時候,他的感情飽滿如清晨的露珠,沉重的思緒在節奏與旋律的安撫下,睡一覺就會蒸發。
他迷戀那樣的時光,和朋友一起闖蕩在音樂的世界裡,在舞台上對親愛的人們揮著手,幸福又緊張地進行著短暫卻在記憶裡永恆的歌曲。這樣想多了他會越想不顧一切的回去,或在未來追求這個很有可能變得不再純粹的音樂志業。這是不可能的事,他自己、以及他的家人都不會允許。他只得讓自己感性方面渴望過頭的時候,用無數個理性的理由約束自己。
傍晚,卡夫爺爺在酒吧外面的座椅疲倦的坐了下來,又過了一天,溫度也隨著冷氣團的到來下降了幾分。他望著海,也望著日暮時分融化在雲霞裡的夕陽。他的人生像每天的海以及晚霞,當然依循著一定的平靜而祥和的規律,卻是瞬息萬變的。那不是令人招架不住的那種劇變,而是一種適合他的「規律」,當他承受著他的挫折與試煉的時候,他不會忘了自己。
「卡夫爺爺!」
卡夫爺爺回過頭,看見站在不遠處的科文,他站在靠海的馬路邊。
剛放學,科文還背著高中書包。看見他的模樣,卡夫爺爺彷彿看見以前的自己,那個自己雖然無時無刻都在迷茫,卻有會像傻子一般堅持的事。科文現在露出的就是那種笑容。暮色柔和了他身後的風景,暖暖的色調輕輕的沉澱在他臉上。科文對著卡夫爺爺快樂的揮手。
他知道,每次科文或是瑞奇來找他的時候,多半都是有些心事。他從小看著他們長大,多少也能感覺到一些。
「來吧,我這邊有好吃的,不過沒有酒喔。」
「酒吧沒有酒,不是很奇怪嗎?」
「啊不是,我是說,你還沒成年,不要總是想偷喝喔!」
「你忘記了嗎?再過一天就是我的十八歲生日了,到時候我怎麼喝,你也管不著了不是嗎。」
「阿……」
科文開心地笑了,一屁股坐在卡夫爺爺旁邊的躺椅上。書包已經被他隨意的丟在沙地上,他卻還像緊握某種責任一樣緊握著英文單字本。
「壓力很大嗎?」
「其實我也感覺不到壓力甚麼的。」他尷尬的笑著。
「如果像上場表演,那就可以很明顯地知道自己在緊張。從瘋狂留著手汗的手、肚子的疼痛就能發現。可是那種長期下來的緊繃要怎麼發現呢?要怎麼知道到底累積了多少壓力?就算隱約的知道自己負荷太多壓力我們又能怎麼辦呢?我們又無法讓自己立刻從這種情況脫身,就是無法說逃避就逃避才會有這麼多的壓力不是嗎?如果環境就是如此,那我們要逃到哪裡去?」
他暫停了一會兒,對話的空白被永恆的海潮聲填滿。有些話變得不再難以啟齒。
「其實我想過很多,或許想得有點太多了,但沒辦法,因為我想處理我的情緒。為了能夠好好的處理我『多餘』的情緒,我必須不斷思考。我不想在你們眼中成為抗壓性低的年輕人,因為我就只是疑惑著每一件事,並且發問著。為甚麼?為甚麼我會面對這些,還有我該怎麼辦?當我尋找到我想要也需要的答案,誰知道呢?說不定我就會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他們聽著波浪翻滾又嘩嘩落下過了良久。
「如果你覺得很累的話,那麼就逃跑吧?」卡夫爺爺看著科文說。那時候,他的眼睛裝了科文很喜歡的那種寧靜的夜晚。
「我是說『真的』逃跑,我可以帶你走。我會陪著你。」卡夫爺爺堅定的說。
溶溶的暮色漸漸變的黯淡。科文的眼睛也跟著夕陽一起,漸漸的沉靜下來。
我們都在海裡。大家都必須竭盡全力的游泳,直到抵達對面一座小島。那是一段很長的距離,我實在很害怕,不停地大口吸氣,但這麼做使我更加疲累,無時無刻都感覺快要窒息。
科文在遠方大聲呼喊,我不知道他喊了甚麼,好像在呼喚某個人的名字,叫他清醒之類的。大海跟天空一樣黑,我甚麼都看不到。在視覺幾乎起不了作用的狀況下,我只好憑著聲音奮力的往科文的方向游去。在我游的時候我撞到了某個東西,那時我還不知道那是甚麼。一番努力之後,我終於能看見科文,他的那種表情我只有看過一次,那是大概一年前他狀況非常不好的時候,就像整個人都要碎了。
我看見了科文旁邊的許望帆(她曾經和科文走得很近,但從幾個月前我就沒看過她了。)她失去意識了,正在往下沉,科文拉著她,試圖阻擋她不斷下沉。他不停呼喚她,但怎麼都沒有用。
我四處張望尋找幫忙,而這時我才發現我剛剛撞到的都是一些失去意識的人,他們漂浮在海上,而剩下的人正在拚了命的在向前游。我倒抽了一口氣。我應該害怕的,在震驚之餘卻麻痺般的甚麼也感覺不到了。只有一種模模糊糊、也說不上來的無力感,那像薄紗從天空降了下來,蓋著我、蓋著所有的一切。我大聲的呼救,可是沒有人看我們這邊。科文絕望的看著我,那時候我好想給他一個擁抱。
我又聽見那個模糊的問句,它好像把它之中飽含的感情傳遞給我了,我的內心被急切又痛苦的情緒給填滿,混合成一種近乎尖叫的求救訊號。
「瑞奇……」
「瑞奇!」
瑞奇從夢中驚醒,等待來自夢裡的緊張與恐懼慢慢逸散在空氣中。確認自己活在安然無恙的此刻時,他鬆了一口氣。又是和昨天一樣的夢境,差不多的黑暗、令人不安的真實感、一樣莫名其妙的問句。他的頭隱隱作痛著。
「你昨晚是不是沒睡好,都睡了好幾節課了。我真的要叫你一下,好確認你沒事。」瑞奇還帶著倦意,耳邊熟悉的聲音起初並沒有甚麼好奇怪的,不過就是他認識的一個朋友,等他漸漸清醒過來才發現不對勁。
「你怎麼會在這裡?」
「你在說甚麼啊?」許望帆愣住了,滿臉疑惑的看著瑞奇。
「不是啊……妳不是……?」他本來說去留學了,但瑞奇發現他的記憶開始錯亂。因為某種原因他突然不確定她為甚麼消失了,可能是因為剛剛的夢,可能是因為現在她突然出現在他眼前。他關於她的記憶陷落成一個窟窿,一個沒有邏輯的、等待被重新定義的區塊。
「你是不是壓力太大啊?」她說。
老師走了進來,那不是瑞奇熟悉的面孔。可是除了老師和許望帆,其他的同學們都和平常一樣,他強迫自己慢慢接受眼下的環境。
「隔壁班的科文已經失蹤一天了,請問有人認識他,能夠猜測他的行蹤嗎?」
老師說,環視整班的同學。瑞奇直覺想到了卡夫爺爺的酒吧,他卻沒有發言。
「好吧。下課的時候,認識他的人再來找我。我們今天要做一點不一樣的。我想聽聽你們『真正』的想法,不是作文紙上那些。誰想先分享?甚麼都行。」
教室靜默了好一陣子,直到瑞奇左前方的人站了起來。
「我沒有夢想。」他垂下頭,靦腆而卑微地笑了。
「我把別人希望我成為的,當成我的夢想。我每天都很努力,獲得好成績,在各種競賽中獲得認可,同時我卻也經常不知道為甚麼要努力。我的目標很明確,但最終我也只是在我有限的、某種程度下『被提供』的選擇中做出看似自主的選擇。我一直在想我可能是升學體制下複印出另一個人而已,而不是我自己。或許我曾經可以找到我想做的事,只是我再也不想找了,因為我內心深處知道那不是這個社會需要的,不是我的家人想要的。我也會自己抗拒自己的慾望,因為那不是『對的』。或許有人覺得我很愚蠢、很奇怪,可是我總感覺身上背著無數個義務的重擔,而我沒辦法忽視它。我喜歡聽別人說;『我們應該為自己而活。』有一部分的自己卻想著這麼做會不會太自私?或是太衝動了一些?疲憊的一天下來我甚麼都不想思考了,我得準備好,明天繼續拚了命的努力。因為眼下的困難才是現實,對吧?」
瑞奇開始注意到有甚麼事情開始脫離常軌,偏離了現實,他卻不知道那是甚麼。他下意識地看向許望帆,許望帆也看著瑞奇。瑞奇想,那時候她的眼睛好像裝著飄著霧的夜晚。許望帆舉起手,站了起來。
「我有夢想。」許望帆善良而稚氣的笑著。
「可是我也沒什麼了不起。我很長一段時間感覺不到任何的希望。剛開始我以為我有那個才能,對未來也充滿憧憬,但時間久了,我對一切都感到不安,非常不安。我知道我其實並沒有自己想的那麼有才能,我知道那些我可能永遠也辦不到的事,我知道有的時候我可能必須放棄甚麼。我看見夢想與現實的落差,我看見滿是缺陷並因此自卑的自己。我看著夢想離我好遠,而我確實時時刻刻在與它遠離、下墜著。我永遠也不夠努力,就算我已經拚上了我最後一口氣。因為甚麼你知道嗎?因為我覺得那就是我的模樣,我再怎麼努力還是做不好。我並沒有足夠的才能,還總是被自己不怎麼積極向上的負面情緒給淹沒。我的爸爸沒收一切會讓我快樂但無助於成績的事物,我甚麼話也不會說、也不會反駁,因為我覺得他可能才是對的。看著他或是老師們的時候,我常常為我的無能而充滿罪惡感,感到自卑、感到無力。我總是被周遭的一切斥責,我應該做甚麼,我應該學習成為甚麼樣的人……我為甚麼做這些做那些,我做那些有甚麼用嗎?我有的還不都是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我為甚麼不繼續在書桌前學習直到我累的再也做不到為止?」
「其實我就只是個極其普通的平凡人,常常卻也不想承認。我想要碰觸到夢想的邊緣,於是我每天努力的奔跑。我以為我抵達我的終點就好了,可是現實告訴我,我沒有所謂目的地,我永遠不能停止奔跑。我的背後緊追著一個深淵,它如影隨形,隨時將疲憊的再也跑不了的我吞噬,被吞噬後,我將在這個世界裡陷入失敗與自我厭惡的迴圈。」許望帆說著說著停了下來,她依舊溫柔而委屈的笑著。瑞奇很疑惑,他關於她更遠以前的記憶碎裂成一塊一塊不規則的圖形。
「許望帆……我很抱歉。」瑞奇顫抖的說,他好像快要想起些甚麼。
「不,這些都不是誰的錯,更不可能是你的錯。如果硬要說的話,可能是我。」
「不是,那絕對不是妳的錯。」
瑞奇舉起手,換他站了起來。
「我打個比方好了。」他的聲音顫抖著,還是撐起一個不自然的笑容。
「我們剛開始都是未知的種子,我們前面立了一個牌子,每個人走過來,都在那個牌子寫上他覺得這個種子未來會長成什麼模樣。有的寫了他們各自私人慾望的投射,有的期許被重複刻寫,刻痕變得越來越深,像種傷痕。每個人或多或少都關注著它成長,為它澆水、除草,有的甚至刻意扶植它成特定的形狀。但是,沒人知道它最終會長成甚麼樣子吧,如果它長得跟它的面前的立牌不相稱,不是大家所預期的,為甚麼就是它的錯了呢?為甚麼它就會是失敗的、不美麗的?假如它真的按照它被規定的模樣生長,它就不可能自己還沒盛開就枯萎了嗎?不管怎樣,讓這株獨一無二的植物繼續自由的,以它的方式生長著,不傷害別人也不至於傷害自己,不就好了嗎?不就好了?」
瑞奇紅著眼望著許望帆,他看著她的眼睛從飄著霧的夜晚轉變成下著雨的深夜。他感覺他破碎的記憶正在一點一滴緩慢的恢復原狀。可是那記憶似乎會讓他痛苦無比,他感覺頭痛欲裂。「如果堅持下來,會有甚麼改變嗎?」瑞奇痛苦地說。他看見許望帆微笑著搖了搖頭。
「這我也不知道。」
「妳不想念嗎?以前我們三個在一起的時光?就這樣快快樂樂的啊,有甚麼做不到的。」瑞奇說著,他說出來的每個字都輕輕的碎了。
「我對不起你們。」
他發現她漸漸變得透明,而教室跟同學們的面孔都逐漸模糊歪曲。
瑞奇拼命搖著頭。
「不對啊……我們一定可以辦的到的。」
「真的對不起……我不該就這麼消失的。」。
「但是你該醒了。『真的』從這裡醒來。我沒辦法,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你是誰?你要怎麼成為自己?』」
飽滿透明的淚珠滑過她的臉頰。許望帆一說完,她和那個場景瞬間像蒸發乾淨似的完全消失了。瑞奇眼前驀地一黑。
與卡夫爺爺一起搭船出海的時候,科文一直遠遠望著這座小島,卻從來沒有真正踏上這裡的土地過。現在他在這裡,站在這島上吸收了滿滿陽光的沙灘上。他光著腳,沁涼的海水淹過他的腳踝。昨晚,他跟卡夫爺爺在這裡搭帳棚過夜,他久違的睡到將近中午才起床。
「我在你睡覺的時候,在酒吧很臨時的做了一個蛋糕,不要介意喔。」卡夫爺爺端著蛋糕,走到科文身邊。
「十八歲生日快樂。」卡夫爺爺溫暖的笑了。
科文緊緊抱著他。
「謝謝您。」
「有甚麼願望就快點許吧。」
「長大之後好像就不太想要甚麼生日願望了……」
他的願望其實沒甚麼。就像夢想一樣,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可以一直變,只要開心就好。甚麼樣的夢想都可以,沒有夢想也沒關係。就像電影說的,看不到未來的時候就走好當下的路就好。有時候需要點堅持,有時候需要點改變,有時候需要點勇氣,還需要相信自己。
他閉上眼,最後他還是許了願,吹散的燭火消失在遠方。他希望他身邊的人都好好的,他希望瑞奇好好的,他希望許望帆知道,他們都很想她。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蠻對不起你們的。我們應該讓你們這群年輕人有更好的環境發揮你們的才華。我們不應該總是拿著分數或金錢威嚇你們,或只依靠它們決定你們是誰。像«車輪下»裡的漢斯面對的一樣,有太多人被體制與不合理的要求壓得喘不過氣了。」卡夫爺爺說著,握著他的手。科文回握著他。
「我一定常常有意無意的,給你們壓力了。」
「不會,沒關係。我也常常覺得,畢竟大家都在這整個充滿競爭、現實過於殘酷的環境裡……我要謝謝您,謝謝您還願意傾聽我們。」
瑞奇在他的房間醒來,做了一個太長的夢,他覺得有些頭昏腦脹。這個夢讓他想起很多不願想起的事,也讓他明白很多事。他想到自己這陣子混亂又有點滑稽的生活,不由得笑了出來。陽光透過窗照射到他的床鋪上,他在那方陽光坐了一會兒,甚麼事也沒有做。後來他走到卡夫爺爺的酒吧。發現酒吧的大門是關著的,他知道鑰匙在哪裡,之前卡夫爺爺答應他隨時可以來的時候告訴他的。他打開門,發現任何人都不在那裡。他走上二樓,走進一個像閣樓的小房間。些許裂痕爬過那房間的牆壁,一塊一塊的紅磚露了出來,淡淡的木頭味道飄散在空氣中。
他在桌上發現了幾張散落的紙,跟被裝訂好的一疊又一疊紙本。他發現那是科文的字跡、科文寫的一篇又一篇日記,或可以說像是信的東西。他看著最皺最舊的那疊裝訂好的紙張,第一張的日期是許望帆離開的日期,而桌上散落的紙張則是前幾天寫下的。
瑞奇讀著最近的那幾張。
「我想了以前妳說過的話,妳說我們應該辦一個海邊音樂會,邀請我們認識或不認識的人來聽我們的音樂,那時我一直說我們沒有這種時間,我現在覺得我那時簡直是個蠢蛋。」
「早知道就該好好實行妳的想法了。在這種感覺總被某種命運的波流撥弄的時期,踏出的每步好像都會造成長遠的影響,我是在害怕這個?我到底是在害怕甚麼?如果我當初嘗試一下也好,就不會有那麼多遺憾了。」
「我希望妳在那裡一切都好。在我真的辦那場音樂會,或離開這個城鎮、回來這個城鎮的時候,我會緩慢地告別我現在寫的這些日記。也就是說,這些紙會陸陸續續化為灰燼。」
「請別為我們擔心,我們會好好的,妳也是。」
透過房間的窗戶,瑞奇看到一天又要過去了,太陽漸漸沒入海中。他拿了一張空白紙,開始動筆寫了起來。
「活著不是為了甚麼目的或變得『有用』。很多時候就只是活著、珍惜,愛著生活裡那些平常看起來微不足道,對我們來說卻必要的事物而已。現在很多事情都變了,變得太複雜了。當我們還為了我們自己而堅持,我覺得已經很難能可貴了。」
「所以呢,其實我一直想說,你已經做得很好了。你們都做得很好。希望你們都可以知道,你們在我眼中有多麼耀眼。不要對自己太殘忍,記得好好吃飯、不要像傷害自己一樣放棄一切、早點睡。如果能做些好夢就更好了,不然一覺到天亮也可以,不要太強迫自己,有時候就應該好好休息。」
「現在,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期許自己、祝福大家的未來,我知道現實一定不會像祝福語那樣簡單,我知道一定會有很多現在也說不清的阻礙,可是我想我們可以陪伴彼此,漸漸地學會如何相信自己。或許不一定要成為更好的人,我們成為自己就好了,一個最舒適的、不過於沉重的自己。」
「我們會試著找到自己的。」
瑞奇在酒吧待到將近午夜。
他走出酒吧,走上階梯,沿著沒有車的濱海公路一直走著。天還未亮、夜還很長。他徘徊在人生的交叉路上,總是帶著淡淡地、可能會被輕視成青少年內心戲的憂傷。依靠著他生命中時有時無的月光,他也想要看清未來的模樣,看見自己的模樣。
他看見科文坐在不遠處的公車站。他緩緩走上前去,想要和已經十八歲的他說聲生日快樂。
「你要去哪?」科文說。看見瑞奇的時候他笑了,他感到純粹的快樂、安心。
「我不知道,可能我之後就知道了吧……總之,考完試之後我們可以辦個海邊音樂會?」瑞奇開心的笑了,淺淺的月光灑在他們臉上,海上、濱海公路上,還有卡夫爺爺的酒吧。
作者簡介

劉格雅,水瓶座,18歲,目前就讀於台中女中。大學考上了台大外文系。一直以來都十分喜愛文學,希望能寫出忠於自己內心也能感動別人的作品,也希望能擁有複眼般多面,同時飽含著堅定善良原則的思想。在寫作的路上將會繼續努力。
看更多得獎作品
1.【青春大作家X第22屆馭墨三城文學獎】散文首獎:告別式
2.【青春大作家X第22屆馭墨三城文學獎】新詩創作者獎:傷口
3.【青春大作家X第22屆馭墨三城文學獎】小說創作者獎:席地而坐
4.【青春大作家X第22屆馭墨三城文學獎】新詩首獎:你還是需要人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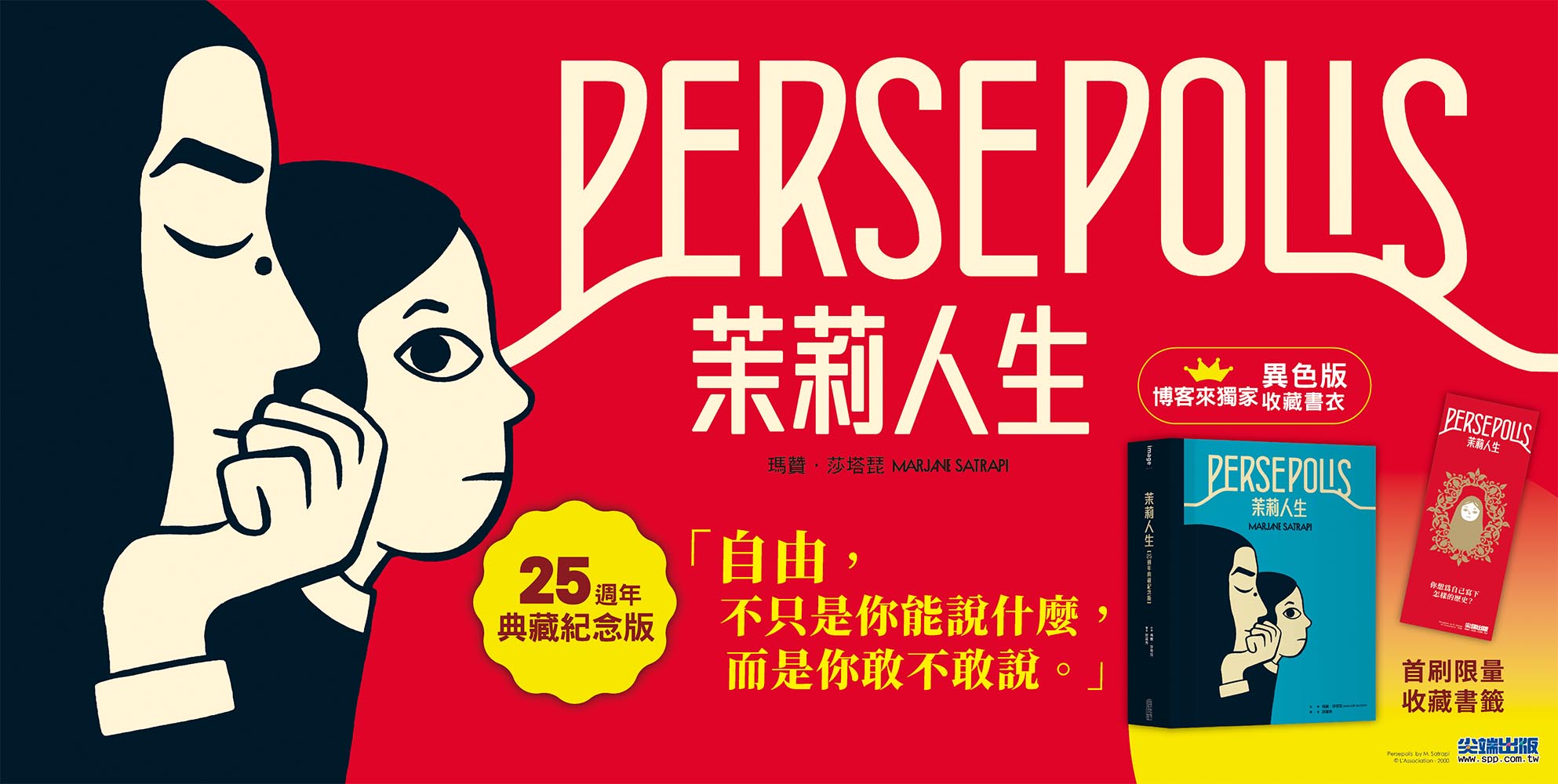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