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短片般的輕盈機靈,帶著恐怖怪誕的詼諧,簡短,互不連貫。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波蘭小說家奧爾嘉.朵卡萩的《雲遊者》,乍看像是旅客在機場、旅館和車程間浮想聯翩、快筆寫在登機證背面的旅行奇想短篇集,用小說家卡爾維諾連對海浪都要分析出一套規律的好奇心去觀察歸納每件事,或藉機場巴士鄰座女乘客之口說出雋語:「定居、務農的民族,比較喜歡循環時間所帶來的樂趣,每件事都必須回到開端,蜷縮成胚胎,重覆成長和死亡的過程。不過遊牧民族和商人……的時間是線性的……每個時刻都不同,永遠不會重覆,因此有利於冒險……當時間中的改變是不可逆的,失去與哀悼便成了日常之事。正因如此,從他們口中永遠都不會說出,像『枉費』或『用盡』這樣的字眼。」
●
人生沒有枉費可言,唯一該做的就是枉費時間離家冒險。
如此奢侈的豪語,是真的嗎?
農、牧時間的價值觀差異,令人想起朵卡萩《太古與其他時間》各篇描述村民各自的祕密心事,篇名依照各章主角名字,稱為「某某的時間」。《雲遊者》第二章〈腦中的世界〉裡,敘事者「我」厭煩父母的農民時間:父母一整年久坐不動,即使全家開車去法國南部、雅典衛城旅遊,也只是照本宣科拍照向親友證明到此一遊,在家和景點之間的封閉軌道上巡迴,無趣得令人打呵欠。所以「我」成了過遊牧時間的流浪者,以旅行作為生活方式。從不落地生根,而從飛機火車的震動中獲取能量。「我」到處跟外勞、難民一起打零工,每賺了點錢就辭職旅行。
「我」在斯德哥爾摩機場遇見了瑞典女子亞歷珊卓,她到全球各地調查虐畜成書:隆冬牧人讓成群綿羊在雪地受凍、羊的胎兒被剝皮做成皮草……滔滔不絕控訴人類殘酷後,她居然說:「真正的上帝是動物。」因為動物為人類犧牲自己,捐出肉、皮、命,讓人們活得更久、過得更好,所以各國的掌權者都要來朝拜犧牲的羔羊。
看來虐畜為她帶來的,不是罪惡感和義憤,反而是榮譽感、親密和炫耀,應該將虐畜進行到底。為什麼?作者沒回答,把讀者扔在錯愕中,繼續前往下個目的地:論證傳說中衣索比亞的無頭人、埃及森林的狗頭人民族,長得像野獸,能像人類般獲得上帝救贖嗎?聖奧古斯汀說,只要有理性,無論外貌,都能獲得救贖。
這麼說來,動物也該多享有一點平等?然而作者心不在此,要隔25-篇以後,〈約瑟芬.索利曼致奧地利皇帝法蘭茲一世的信〉系列,講述宮廷黑人大臣死後被製成標本展覽,女兒三度寫信要求國王發還遺體埋葬,本書才會再回應眾生平等的主題,呼籲「黑人也是人」。


●
此時作者早已轉機踏入戀童癖的一連串輝煌變奏:〈後宮(曼朱的故事)〉描述沙漠綠洲小國的國王無心政治,西方白人軍隊即將兵臨城下,他卻不備戰也不儲糧,只帶一群年幼兒女逃入沙漠。原來他是太后垂簾聽政的傀儡,後宮妻妾都讓他覺得噁心,只有細瘦裸體孩童圍繞,他才睡得著。
接著,作者親訪歐陸多處人體標本博物館,在〈蠟像收藏〉中修辭極盡華麗,歌頌維也納約瑟夫博物館的人體蠟像,沒有皮膚、由肌肉肌腱編織成的男體,優美如藝術雕像。下淋巴網絡、淋巴結擺在珍珠光澤的絲綢上,就像星星、別針擺在珠寶櫥窗。在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體收藏後,〈布勞醫生的旅行〉描述布勞醫生拍攝他女學生的幾百張性愛裸照。忽然間,展覽的人體標本、少女的陰道照片、聖人遺骸,被歸為三位一體,在鑽研遺體保存術的布勞醫生眼中同等珍貴。
續篇〈布勞醫生的旅行〉說,保存術權威勒伊斯死後,近60歲的遺孀,邀布勞醫生來參觀不傳之祕。布勞醫生雖垂涎祕密,卻發現要繼承就得上床當她老公,於是逃跑。原來這篇回應了〈後宮(曼朱的故事)〉結尾國王往太后揍過去的那一拳,暗示國王會變成戀童癖,是因為太后為滿足野心而犧牲他,所以他不相信成年人了。布勞醫生的故事,一個字也沒提到他母親,可是全都在寫他對母親的戒懼,遺孀形同他母親的投影。
沿續解剖的主題,〈阿基里斯腱〉、〈菲利浦.費爾海恩的故事〉寫比利時解剖學家費爾海恩,28歲時因破傷風感染截肢。每到夜裡,「滑入意識與夢境間的模糊地帶」,他就受幻肢痛所侵襲,感覺一邊膝蓋以下已消失的小腿疼痛難耐。「在痛楚與搔癢逼得他快要發瘋的時候」,他就搬出泡在白蘭地裡、自己的斷腿,解剖、描繪。〈寫給斷肢的幾封信〉是他寫信問斷腿,身體已分離,靈魂為何還感到斷肢在痛,莫非身體和靈魂只是更大共同體的一部分:「我的痛楚就是上帝嗎?」
在虐畜調查員亞歷珊卓的時間裡,上帝是犧牲的動物。在費爾海恩的時間裡,上帝就是幻肢痛。兩者有關嗎?
●
這篇結尾,費爾海恩說,他一生都在旅行,在身體裡遊歷,進入自己的斷肢。算是把主題圓回旅行上頭,誠意可感。全書各章就以這種似有若無的關聯相繫。若在旅途候車、坐車的空檔漫不經心讀完,那麼這本書是行文輕倩流麗的娛樂旅伴,書中即使對虐畜或性別歧視表達義憤,也輕柔得不著痕跡。但讀者卻會從旅館床上午夜驚醒躍起,狐疑真相不只如此。朵卡萩想說什麼?
全書首章〈我在這裡〉,描述「我」年紀很小時,回神突然發現自己被世界拋棄在靜默、令人窒息的黑暗中。原來他們把「我」獨自留下待一段時間,卻沒先講清楚。「我」感到受困,無路可走,無計可施。其實這就是「我」旅行的起點。文中那些故作雋語的農民時間、遊牧民族時間,都是講好聽的、煙幕彈而已。「我」只想逃離那股受困的心慌。
〈旅遊心理學(一)〉說,渴望「只是指出方向,而不是目的。因為目的總是像幻覺一樣,模糊不清,越是接近,越讓人感到迷惑。不管用什麼方式,都沒辦法達到這個目的,也沒辦法藉此滿足渴望」。讀者會問:為何目的只是幻覺?因為主角不是想抵達,而是想逃離。
〈腦中的世界〉說,定居者的能量來自扎根,「我的能量來自動作──公車的震動、飛機的低吼、渡輪與火車的晃動。」能量從何而來?〈浪跡者〉回答了:女街友告訴剛踏入流浪生涯的少婦「動起來,快動吧。只有這樣你才能躲過他」。因為,他,那個主宰世界的人,只統治靜止不動的,沒有意志和沒有生氣的東西。
能量來自逃跑。不是為了追求海闊天空的自由,而是為了逃離自我被吞噬、被拋棄。總以為抵達目的地就會好,沒想到每次抵達後,焦慮仍如影隨形、揮之不去。原來目的是幻覺。
〈聖灰饗宴〉說,船員艾瑞克返家之旅花了十年,「每當他已自我演練好,要登上返家之船,都會突然冒出新契機,而且通常是完全相反的方向。」小說沒講,是新契機來找他嗎?當然是艾瑞克自己去找新契機,但他卻不知道。原來他不管去哪裡,都比回家好。艾瑞克受躁鬱所困擾,在幾小時或幾天的幸福感過後,他總覺得自己比別人差,所以他尖酸又愛找碴。艾瑞克自覺像個被罰關禁閉的孩子,看窗外孩子開心玩耍──〈我在這裡〉被獨自留下的「我」,化身為艾瑞克再度出現了。
「我」小時候總想要變成隱形人,以便觀察別人而不被人看見。另一章說,成年後,「我」旅行喜歡偷聽路人英語對話說什麼,又擔心英語人口的祕密會無所遁形,需要另一種母語來隱藏才好。又有一章說,「我」出國意外聽到波蘭同胞對話時,雖然偷聽很開心,但又怕被認出曝光也是波蘭人。這些在讀者看來,都像是孩子只要言行一暴露出自己想法與父母不同,就會被家人無情糾正。因此自慚形穢,怕暴露人前就會遭受攻擊,自己卻忘了原因。
旅行,是逃家。
布勞醫生的故事,後宮國王的故事,和另外幾章獨立故事,都不是旅行、而是逃家的故事。虐畜調查員亞歷珊卓藉美化傷害想化解傷痛,解剖學家費爾海恩想藉傷痛連結萬物共同體。這些詮釋,僅是防衛的心理盾牌。「我」全都試過了。都沒有用,再往前走。只能再走。


●
《雲遊者》要說的,是不可說之事。「我」大學讀心理學,痛恨心理學把人當成固定不變、可用測量來簡化的對象,設法掙脫它武斷的審判。在〈維基百科〉一章中,她說「人類把所有知道的事,全都放進維基百科」,那麼講不出來、沒有文字可以形容的事,「應該藏在這部百科底下」,「因為它的內容太過龐大,我們沒辦法踩著文字一步一步探究,只能把腳步放在文字之間,擺在概念之間的深淵中,每向前滑行一步,我們就跌得更深。」
〈旅遊心理學(一)〉也把生活看成是講不出來、沒有文字可以形容的事:生活「沒辦法建立一連串符合因果關係的論點,也沒辦法建立源自事件本身、並以個案方式相繼出現的敘事」,因此要重現經驗就該「將重要性相當的零碎片段,以同心圓的方式置於同一個平面上,組成整體。事實的載體不是序列,而是群集。」這是朵卡萩的小說論,以反資訊的方式提供資訊。
那麼講不出來、沒有文字可以形容的事是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解釋斷肢是什麼。
朵卡萩的觀察,設法將現象拆成基本單位。解剖,將人體拆到淋巴、肌肉、神經等基本單位。〈阿基里斯腱〉一章,說勒伊斯解剖人體,是「將它分解成基本的零件,就好像在拆一個複雜的時鐘。死亡的威嚇消失,沒有什麼好怕的。我們是一種像惠更斯時鐘那類的機械裝置」。解剖,是主角面對無可承受的痛苦時,什麼也不能做,只能反覆拆解這份痛苦,試圖減低它的威嚇。
俗稱致命傷為「阿基里斯的腳踝」。患肢就是你的阿基里斯腳踝,一想起就痛到不行的回憶。
什麼是截肢?〈清理內心的地圖〉說:「我會把傷害我的一切都從我內心的地圖上抹掉。我受困、墜落的地方,打擊我、讓我畢生都忘不了的地方,讓我感到痛的地方,都不復存在。」這就是朵卡萩的截肢。
〈布勞醫生的旅行〉說布勞醫生幼時得到一個玻璃人解剖模型,「他可以控制玻璃人的隱形狀態」,「要是他覺得當下有哪個部分沒有意義,就可以讓它消失。」截肢,是想用遙控器一鍵消除痛苦的回憶。
想要消除,卻在每晚睡前、醒來,更深陷於強迫思考,被幻肢痛般的回憶糾纏不休。費爾海恩寫信給斷肢,《雲遊者》本身就是寫給難以擺脫的痛苦的一封信。
講不出來、沒有文字可以形容的事是,「我」有多痛。


●
〈清理內心的地圖〉說,在被「我」從地圖上抹掉的城市,「困在這些城市裡的可憐人早已被抹去。我會對他們微笑,對他們所說的話都點頭同意。我不想把他們搞糊塗──說他們已經不存在了。」「我」再發豪語,宣布正向思考無敵,萬事境由心轉,此刻回憶的威嚇已不存在。
實際上,不是「他們」,「我」想忘掉的只有一個人。本書寫虐畜也好、皇帝把黑人大臣做成標本展覽也好、戀童癖也好,「我」都在對那個人說:
你對待我,就像人類把群狗丟到無人島相殘至死。
你對待我,就像把我剝製成標本公開展覽。
你對待我,就像在收集幾百張歷屆女學生陰道照片的其中一張。
〈在空氣中溺斃的鯨魚〉講述女生物學家研發消除害獸黃鼠狼的環保毒劑成功,一日接獲早已遺忘的故鄉前男友來訊。原來他成了漸凍人,緩慢惡化等死,希望她下毒幫他安樂死。事後走在老家街頭,她發現這裡路人根本沒在看她,視線直接略過她。她實現童年願望成了隱形人,卻只覺淒涼悵惘。
這在說什麼呢?也許是,就像艾瑞克躁鬱交替,「我」每逢心情愉快、萬事光明,就想著加害者已不存在,無法威脅「我」了。等到重歸鬱症,才知道結果不存在了的並非加害者,而是自己。
《雲遊者》隔著一重難以看穿的帷幕寫傷痛,憤怒又絕望。像是說,「你傷害我,只不過為你一時之快,轉身已忘記。而我,我一輩子都逃不出去。」甚至連寫出來都沒辦法。
幻肢還在痛。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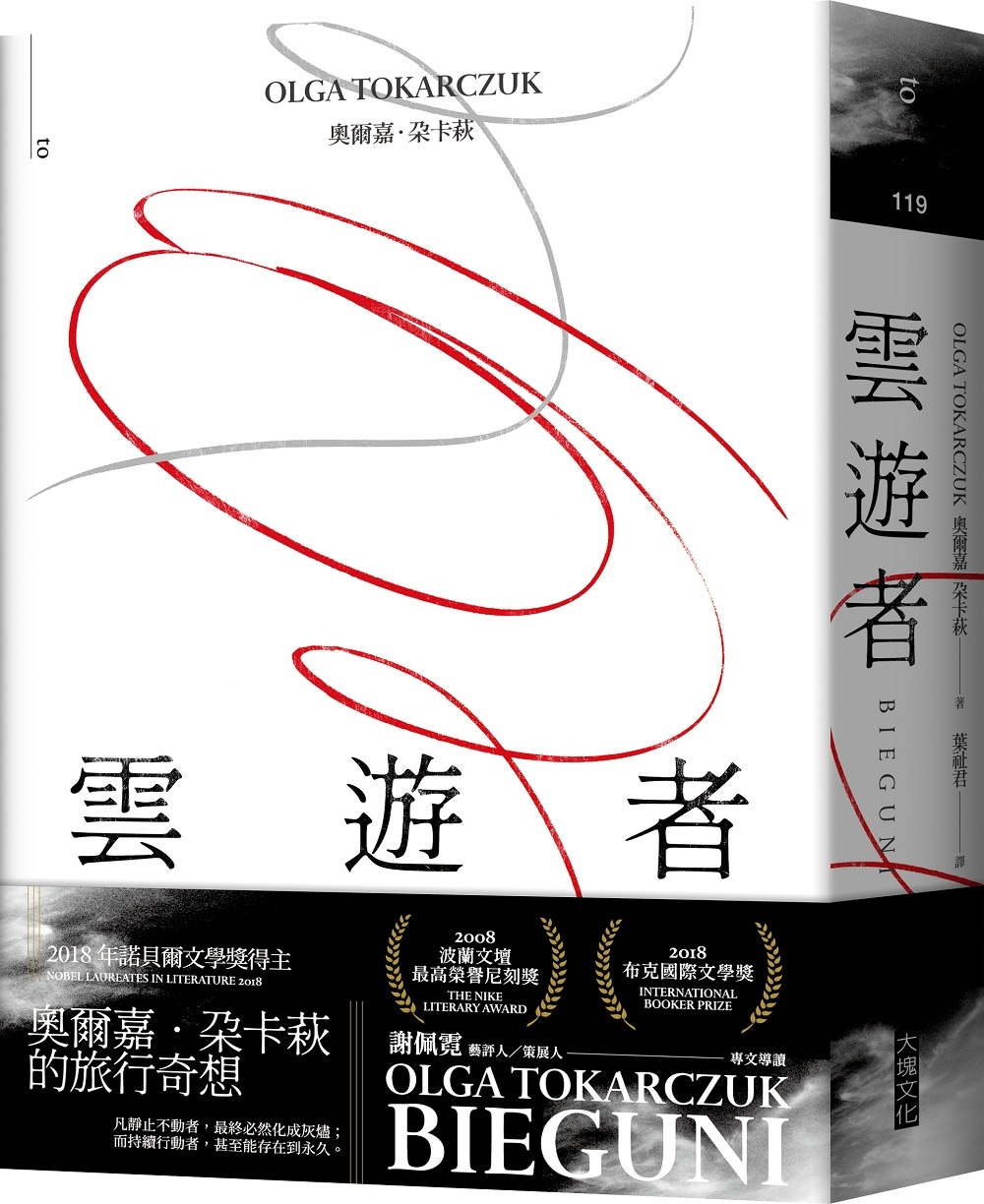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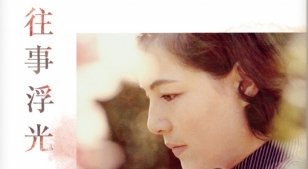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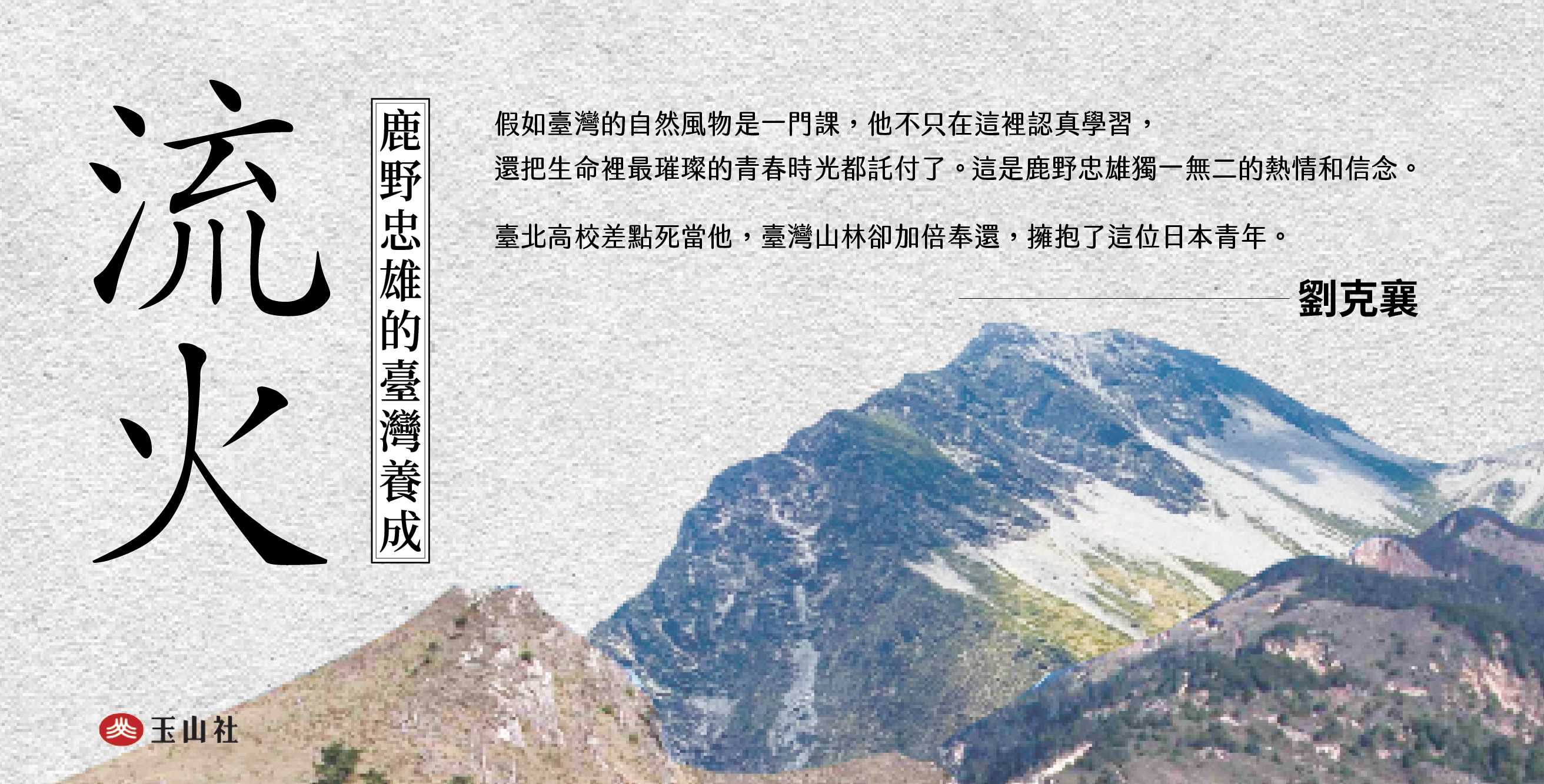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