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於自然環境的惡劣,反應到俄國文學上,有三大特色,一種是強調角色的心靈世界,丘光形容讀俄國小說可以讀到「人的靈魂」;其次是小說通常充滿人與自然對抗的精神;另外一個特色便是無所不在的嘲諷,「可能是環境太惡劣、無聊,於是以開玩笑、嘻笑怒罵的方式來對抗。」
大學念的是政大俄文,畢業後還到莫斯科念俄國文學的丘光,剛好趕上俄國小說在台灣的輝煌年代,「我高中就讀俄國小說了,70年代流行存在主義,杜斯妥也夫斯基是重要的作者之一,藝文圈很流行俄國小說。再加上,社會氣氛壓抑,俄國小說的特色就是在壓抑的氣氛下尋求寧靜。」丘光引用萊蒙托夫的說法:「一個揚帆出海的青年放棄安逸的生活,去尋找暴風雨,彷彿唯有走在暴風雨之中,才能得到寧靜。」外在環境如此惡劣,但個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所以人的意志要不停的去克服外在的惡劣環境,藉由掌握困境才是完全延展個人的自由意志,個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伸展了,也才有真正的寧靜。
然而,困境沒了,人們也不需要追求「寧靜」了,80年代後,社會開放,閱讀選擇變多,此後俄文小說猶如遙遠記憶裡的化石,沒有讀者,也就沒有新的譯本,流通最廣的仍是1930年代的譯本,「那個時代動亂,翻譯得很匆忙,有些錯誤。」加上年代久遠,譯筆文字與現今閱讀習慣不同。如此惡性循環,讀者跟俄國文學的距離就更遙遠了。

還有更多是關於情境、語氣的,「果戈里的小說人物講話常會在字詞後加 S,那是俄國人以下對上、表示卑微的特殊語氣,若翻譯沒辦法將這種S的味道翻出來,果戈里的小說世界也就只是個COMIC(鬧劇)而不是COSMIC(宇宙)。」再者,俄國小說的嘲諷特色,夾槍帶棍的酸人酸語就夾在字句之間,「俄語有些語助詞,一樣的句字可能會有完全相反的意思,但中文不見得可以找到相對應的詞。」
一路被俄文小說餵養大的丘光企圖補足80年代後,俄國文學譯介的空窗期,他看到《夜巡者》的成功,選在2010年契訶夫150歲誕辰,趁勢推出新譯的《帶小狗的女士:契訶夫小說選》,讀者反應不錯,今年(2012)六月將再出版被契訶夫尊為小說教科書的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他重新摸索新一代讀者對俄國文學的接納度,「通常娛樂性的類型小說,比如《夜巡者》,或是知名度高的,像契訶夫都賣得不錯。」
在台灣做俄國小說翻譯應該是很孤獨的吧?「能和原作者有精神的交會,我並不覺得孤單。」俄文已是一項冷門的門檻,丘光挑譯的作品又是另一項門檻,像是「契訶夫選譯的並不是他早期直接、易讀的,《帶小狗的女士》裡都是一些需要年過30、感情有點經歷的人才讀得懂的。」他引用萊蒙托夫的說法,「這個時代甜食大家已經吃得太多了,需要一點苦藥和苛刻的真理了。」唯有在痛苦中才能尋得幸福,在這樣的時代重新出版《當代英雄》,「我只是想告訴現在的年輕人不要太安逸,他們需要有一點暴風雨。」
30年前,俄國小說是苦悶台灣青年的明燈;30年後,俄國小說在甜點過盛的年代,成了一帖醒腦的苦藥。
丘光譯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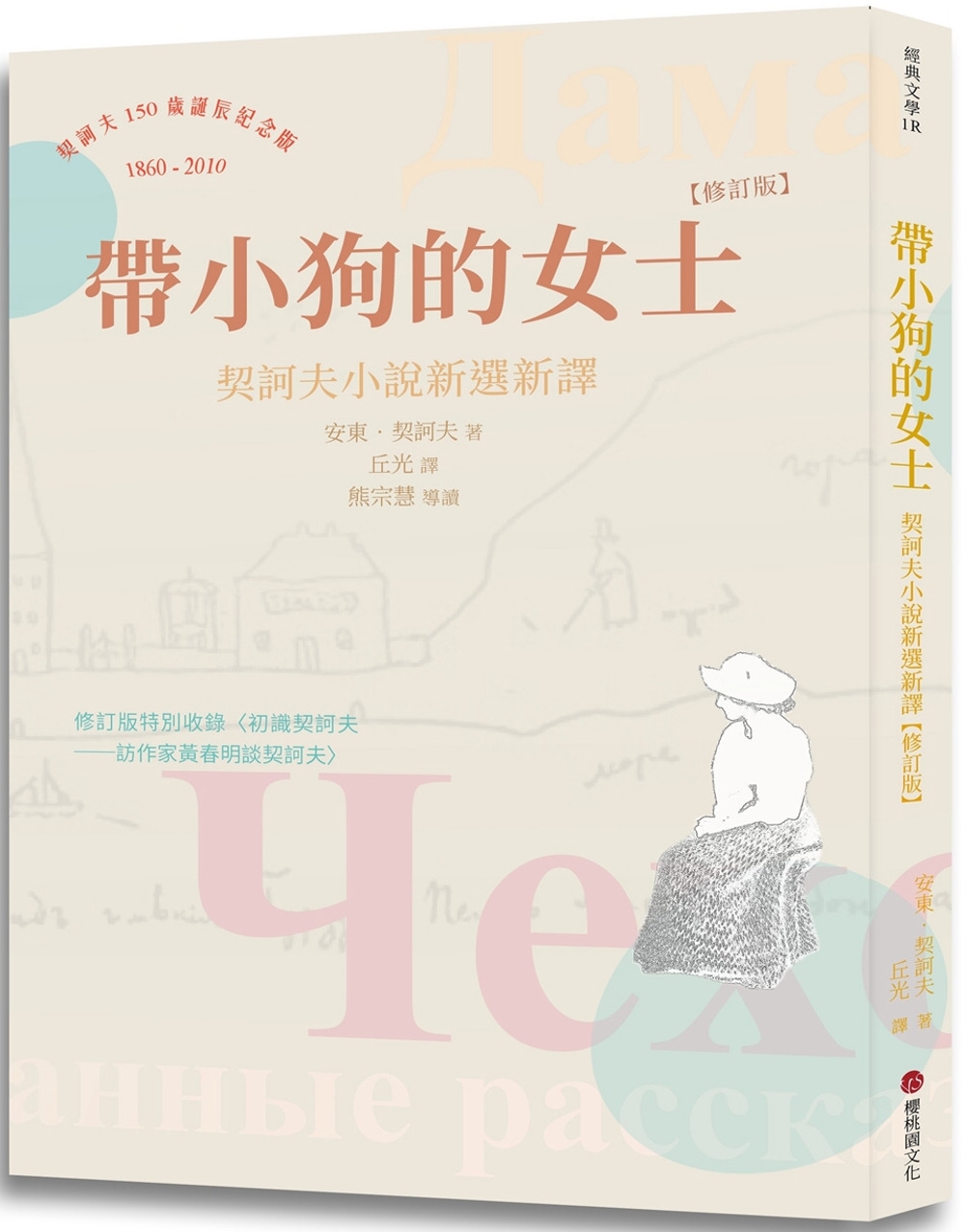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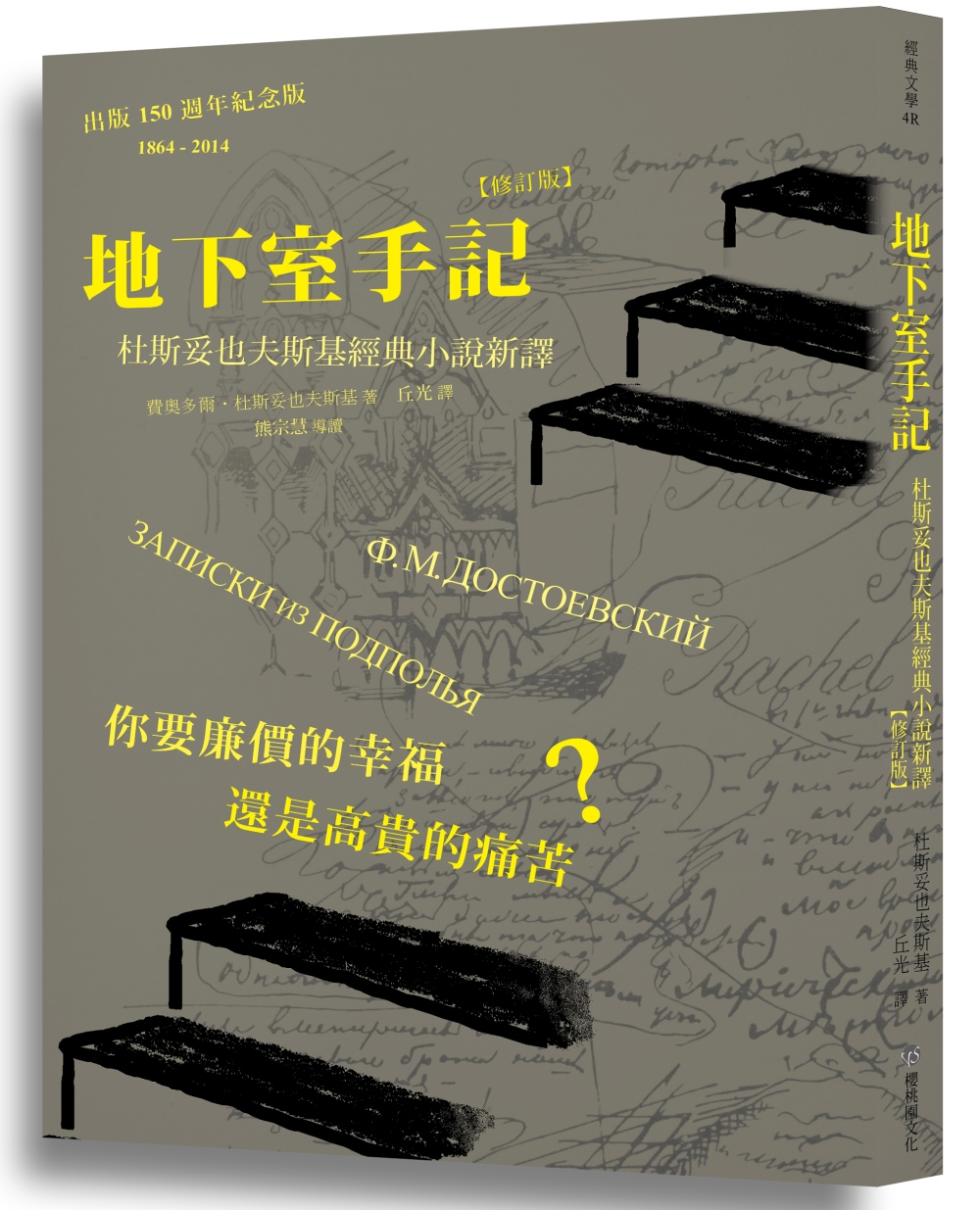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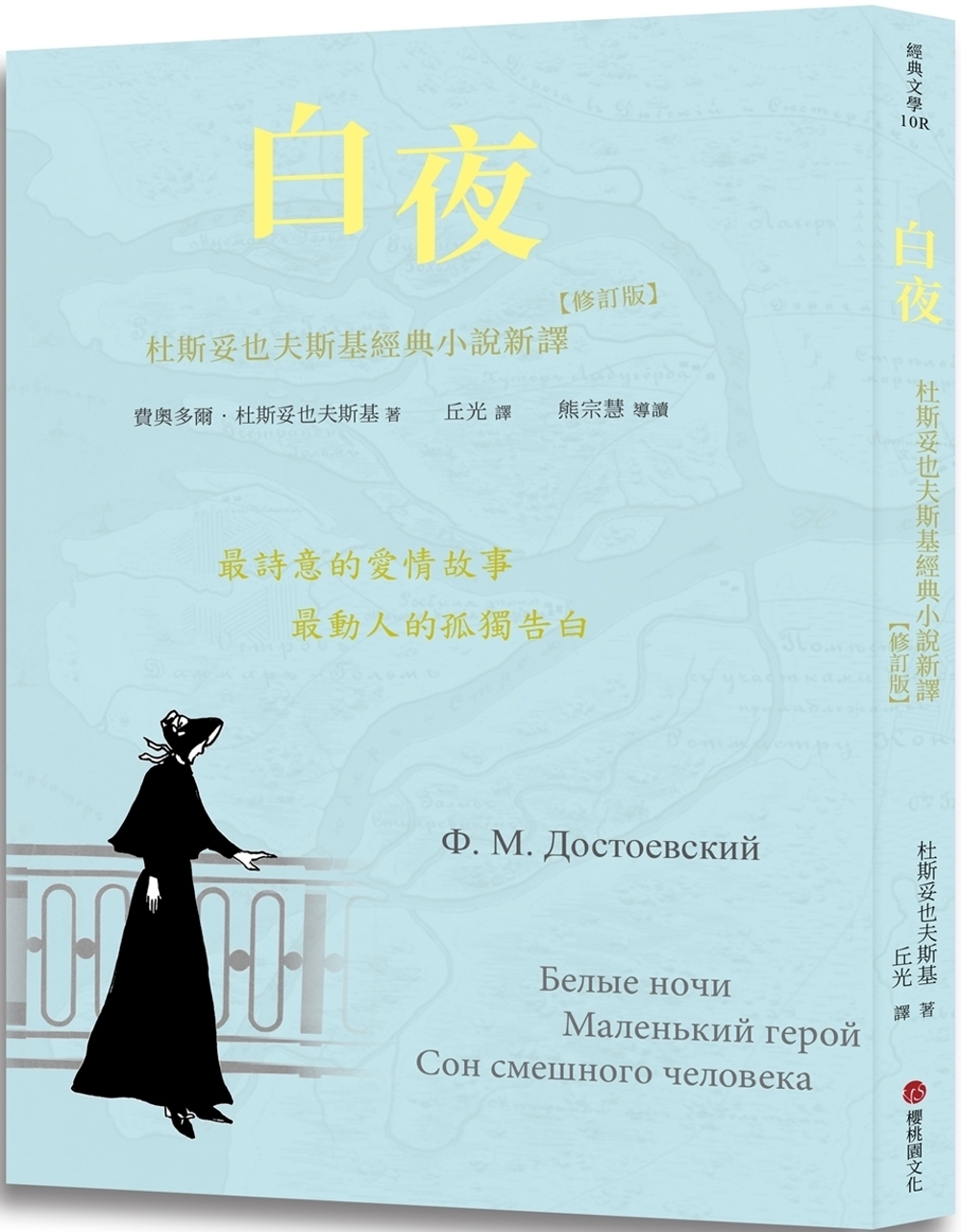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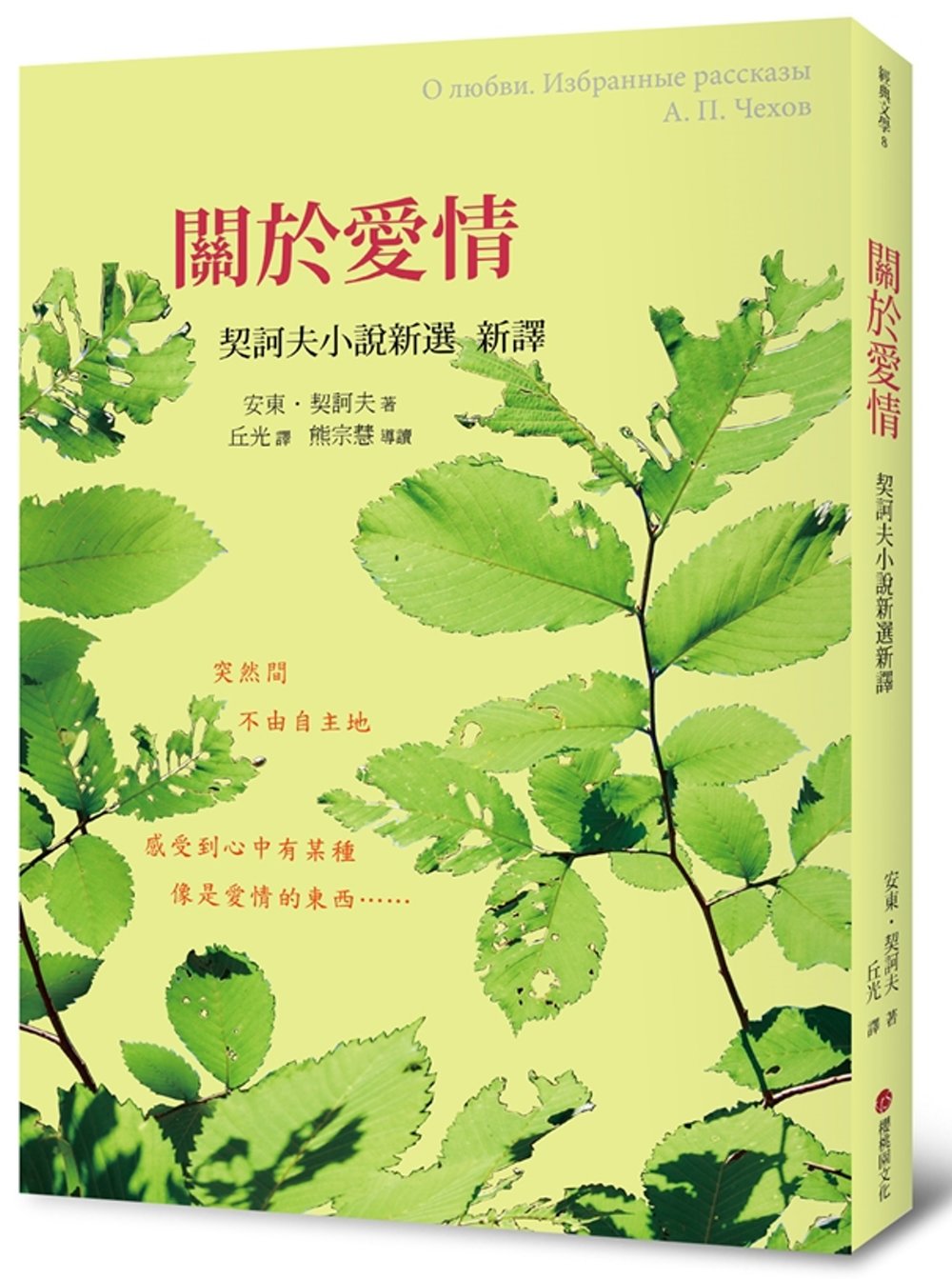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