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與電影裡,三似乎是一個魔幻數字,「三部曲」(trilogy)的概念遍及文學史與電影史。於是,我們看到從巴金、李喬、吳濁流、施淑青到兩個托爾(托爾斯泰與托爾金),甚至李安(喜宴三部曲)、王家衛(蘇麗珍三部曲)都曾燃心焚志的處理與面對他們必得行過的三步與三部。陳雪的《無父之城》,也正是她「空間三部曲」(樓、鎮、島)的第二樂章,但2015年的首部曲《摩天大樓》並非憑空現世。我相信小說家與小說的關係,始終難逃波赫士預言般直指的:「所有文學作品都帶著自傳的傾向。」但故事終會耗竭,自我難免掏空,這時小說該何去何從?如果說陳雪的第一組三部曲是自傳色彩濃厚的《橋上的孩子》、《陳春天》至《附魔者》。那《摩天大樓》是陳雪挑戰過去陳雪的第一步棋,到了《無父之城》這一著,終於定好江山,強虛構三部曲的野心,正熾且美。
 自傳色彩濃厚的《橋上的孩子》《陳春天》《附魔者》可視為陳雪的第一組三部曲。
自傳色彩濃厚的《橋上的孩子》《陳春天》《附魔者》可視為陳雪的第一組三部曲。
《無父之城》是一本必須以推理來轉動的小說,消失的美少女與人間證詞、寫不出來的小說家與失意的私家偵探,推理啟動,但核心與此無關,陳雪不以推理為奧義,推理不過被她視為一種小說趣味,並只是其一。正如陳雪的「空間」,是如此的直覺型,不需取道空間詩學、繞徑奇技淫巧的後設與結構迷宮,就能以自身結出華麗手勢、開出超異空間。所以小說中,那一處以苗栗為骨的「海山鎮」,縱然有桐花、螢火蟲、海水浴場與綿延的火力發電煙囪,它仍是一座處處熟悉卻無從比對的台灣小鎮,這使得《無父之城》的城,不是城市,而是幾乎臨繞整座台灣風景線的城鎮之「城」、家鄉之鄉。
正因為我們都熟讀陳雪,所以更加能讀出這本小說的自我,被小說家稀釋到最淡。很多書迷或許會將「同女」與「惡女」的缺席視為缺憾,卻難免因此忽略了陳雪這次的勇敢自剖是以「虛構他者」觸摸到自己的寫作核心。小說中的小說家汪夢蘭,對於自己不斷追尋、書寫早逝父親的原動力,是這麼說的:「我能夠透過書寫、虛構、創造,將生命裡我無能改變的加以改變,我可以因此設法觸摸、探索、接近,那我接近不了的真實。」她甚至能更進一步,告訴他人:「真實,可以奠基於空無。」這是局中局、書中書,更是裡外兩個小說家對真實的虛擬、對虛擬的真實。
談《無父之城》,無法略過的一道題是:那些父親都去哪了?無父者,如父親自殺的汪夢蘭、如白色恐怖受難者林俊才的兒女,追尋父的路上,他們都長成了趨光植物。但缺席者並不只是父,汪夢蘭自己也參透了:「我的小說裡總是充滿缺席的人,過早離世的父親,永遠不在場的母親,不知何故離開的人,無法成為父親的父親,不像母親的母親,成為我書寫長久的命題。」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千古難題如上,陳雪藉汪夢蘭與小說眾生試圖作答,答案清晰卻是自傷:「留下來(活下來)的人總在揣摩死的模樣。」
與此相對,如果小說也是一種虛構對真實的揣摩,回到「小說」這件事,我想談的是陳雪的本事。從過去訪談與作者的自陳中,當陳雪進入小說模式,總不免令我想到法國哲學家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曾經提過的「日夢」(daydream)狀態,「像從已經建構好的世界,移向一個夢境世界,我們已經離開了小說(fiction),走進詩歌裡。」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你自己必須先沉溺(abandon)其中,毫無保留,否則將不得其門而入。
陳雪進入了,並開展出更多的幻象,華麗崴顫,比如小說中的「神水社」。它不是純然的邪教或是詐騙集團,因它被注入真正的信念,水中有人神,正如化名龍小姐的李靜君所言:「大病一場,一無所有,就會看見自己真正的路。」路是末路也是花路,但只有一條,你非走不可。神水社的落俗與荒唐,與它的神聖和純潔是朵兩生花,開在小說園林裡,讓無父之城的林相魔幻了起來。但真正的奇幻日夢,非得是「書中書」裡汪夢蘭所寫的小說《我鍾愛與遺失的小鎮》,其中的〈月蝕〉。
小鎮的歷史,一路陷落。從前鎮上的望族海山蔡家,男子皆有惡疾如咒,終致失明。蔡家可能是最後一代的獨子在家財散盡、失明後,成為了盲人按摩師,多年後從女客人的肌理中想起從前自己瘋魔的雙眼。正因前路無光,他更得看清現在,「現在」於他是各種女人:「他向櫃檯要來火柴,燒一枝,點著鈔票發亮成小團火光,直燃到燙手方停。日光燈、電燈泡、輾轉映入的路燈、月光、燭火、紙鈔的臭味,然後星星火柴微亮,每一種光線因其強度、亮度、曲折照射的方式,將眼前女子的裸身反覆照亮、很亮、漸亮、落入朦朧,然後剩下猜想。」不斷魘語著的「我要看」,將母姐們逼上近前為他裸身,他才終於說出「我不看了」、「你們別這樣」。
帶慾的觀看與被觀看,附魔般的肉身現場,這是陳雪過去最擅長與深刻震懾讀者的能力,它依然都在,卻成了不經意間的書中書。是書中的情書,更是遺書。小說的最後,陳雪選擇處理的竟是白色恐怖受難者林俊才的故事,野心的龐雜,由此可現。
小說裡,還有段被隱藏的密語,或許可以解釋每個角色都顯露的急迫。小說家急於寫、偵探急於尋找、修行人急於堪破,而遺族與老者更急於留下記憶,一切都正如那句通關密語:「被遺忘很痛苦嗎?」,他們齊聲答是,因為「被遺忘等於不存在。」或許,也有一些例外,小說的核心人物、失蹤的美少女邱芷珊卻硬要唱起反調:「我很抱歉,請將我遺忘。」有人渴求遺忘,也有人從未被正確記憶。
《無父之城》的陳雪,用一本長篇小說展演了小說所能做到的事。比如,重寫死亡、接近真實,甚至是找到身分。不只是角色的身分,可能也是寫者自己的叩問。海山小鎮是陳雪一手形塑的家屋(house),不一定生於此,卻都能在此找到庇護,山林、河道、海水浴場、咖啡屋到舊旅社,所有的記憶都有地方藏身。包含她自己的身分,也幾乎清朗如汪夢蘭的自述:「我想寫作,我非常想寫作,寫小說是我的本命,沒錯的。我找到那種感覺了。」陳雪一直都在。小說本就沒有正解,但好看,就是正義。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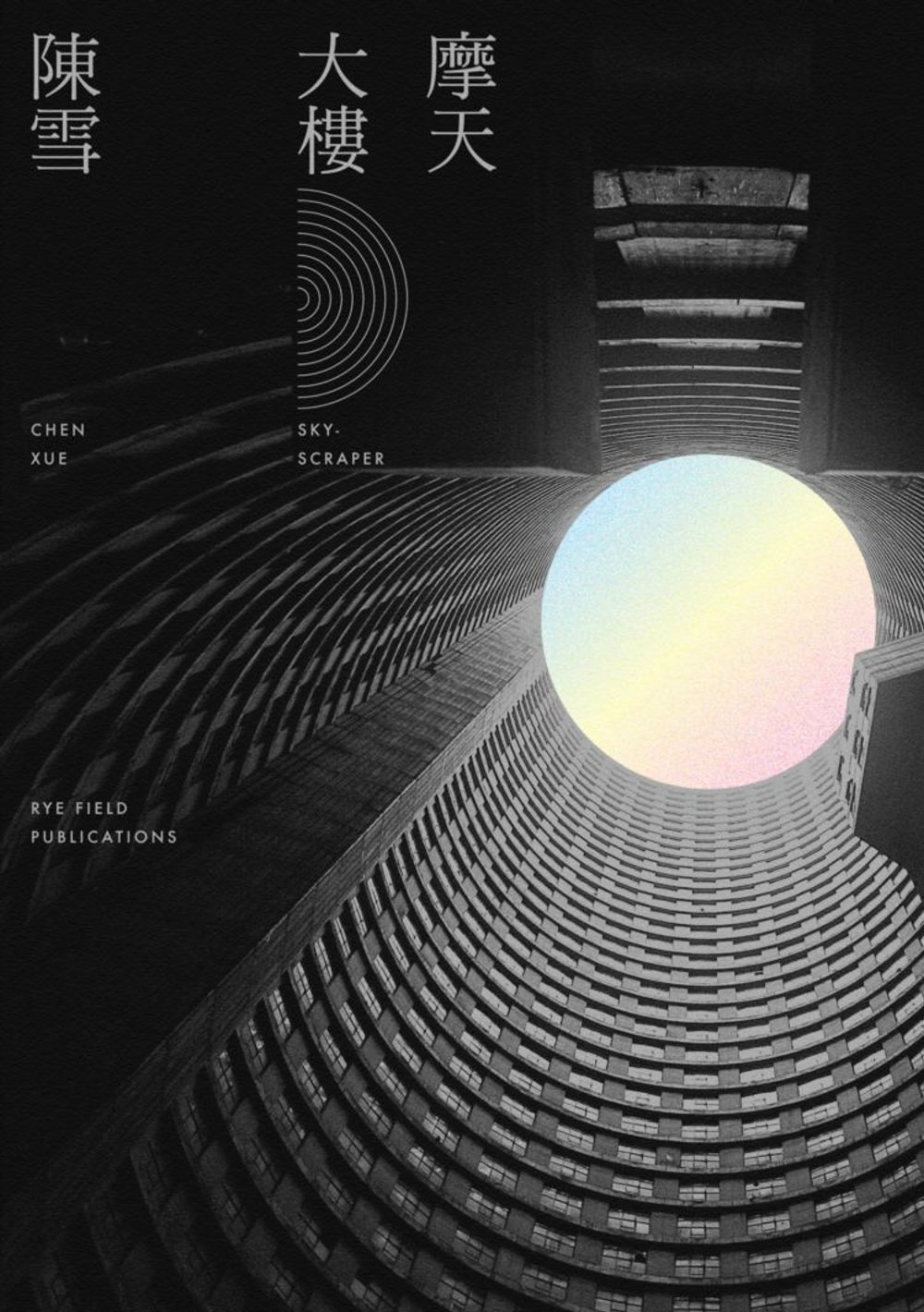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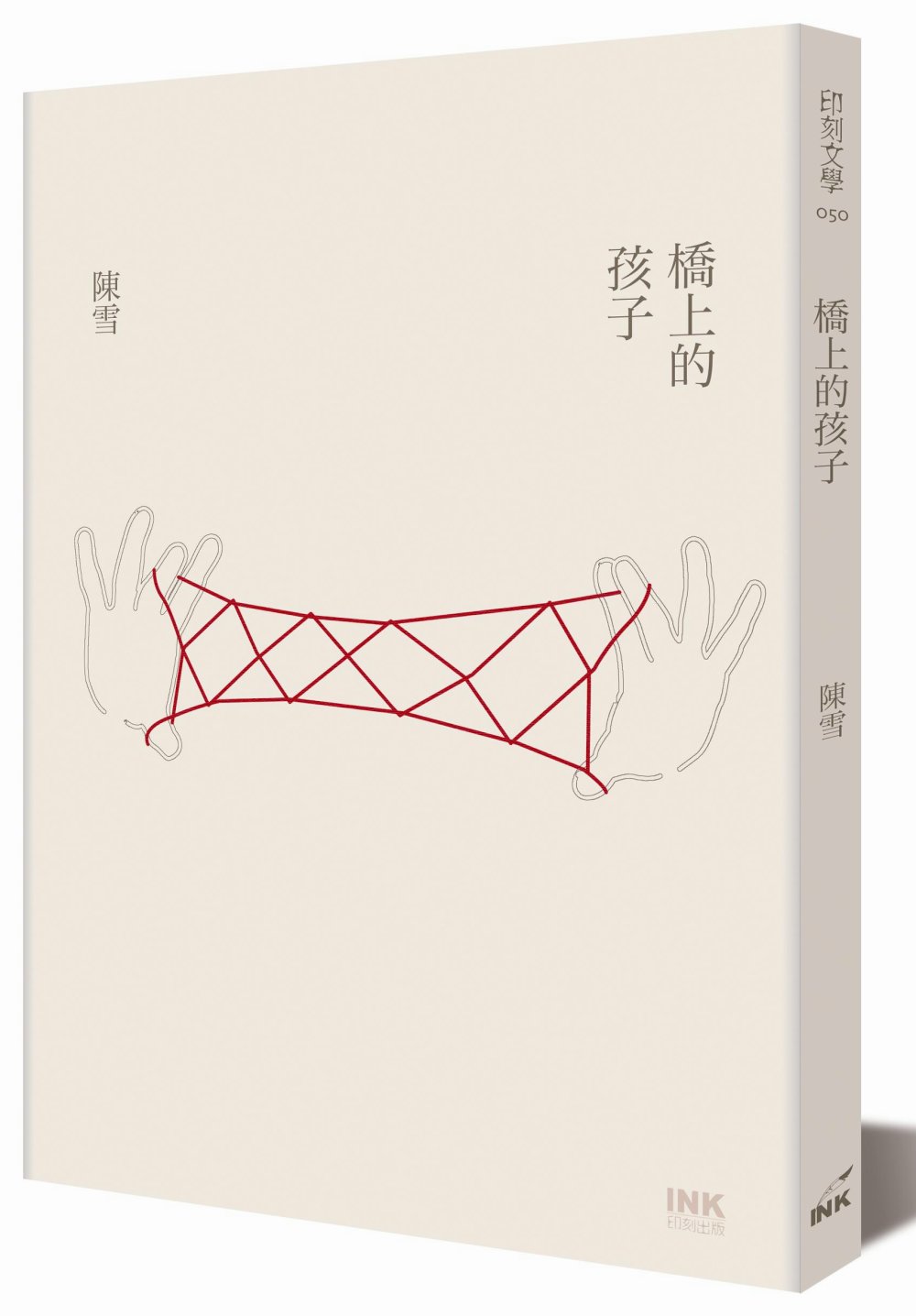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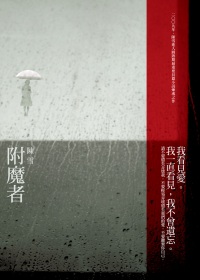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