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娼妓,俗稱「妓女」,或正名為「性工作者」。這些詞語各有其存在的道理,我看情況輪流使用。
妓女在台灣文學中扮演吃重角色。例如,黃春明的〈看海的日子〉以「妓女做母親」為故事主軸。妓女這種角色好方便,因為它為小說帶來幾種利於說故事的好梗(但也是老梗)。其一,貴與賤的辯證。妓女一般被認為是極賤的身分,這個身分足以戲劇性地放大行善或人性的光輝。母親這個被神聖化的身分一旦由妓女兼任,故事也就顯得特別有戲(母親之聖性與妓女之卑賤,之間存有吸引讀者目光的衝突)。阮玲玉的名片《神女》,將從娼的母親詮釋為神女(妓女)兼女神,就是這種老梗的典範之一。老實說,我甚至認為利用這種老梗的眾多文學和電影,與其重視了妓女,不如說重視了貴賤之間的好戲──它們以呈現妓女之名,行議論貴賤之實。
妓女帶來的好梗之二,是性與愛的辯證。性愛分離 vs 性愛合一,在文學和社會新聞中都是老生常談,但作者讀者樂此不疲。妓女被想像成只性不愛(在此性賤而愛貴)的性愛分離者,如果妓女一但動情就傻了,但也就是脫賤入貴(就人格而言,而不是就金錢收益而言)的契機。
性與愛的辯證並非是「二元」的,而是「三角」的:金錢交易為性與愛添加了變數。一般認為性要收錢而愛不沾錢,也因此從娼而不收錢(意味妓女將性看成愛)就是高貴甚至崇高的,愛人而竟然收錢則是羞恥卑劣的。愛情故事(這是文學之大宗)只要有錢進場,就成了通俗劇。
寫妓女的好梗之三,是娼妓存在於家庭之外。在家庭(包括同志家庭)之中發生的性(配偶之間的性,含同志配偶)大抵上是被尊重的,而發生在家庭之外的宿娼被視為不道德甚或非法的。於是妓女代表了悖德受詛的愛。
妓女的好梗還有好一些,但我在此再列出第四種就好:妓女是一種身分(identity),而且是一種大致上被認為越早卸下越好的身分。台灣人是一種身分,但當台灣人的目的通常不是為了在來日不當台灣人;相較之下,當妓女的目的幾乎都是為了在來日「從良」「洗手」,不再當妓女。性工作者的性工作可以被詮釋為一種輕描淡寫隨時不幹的工作,像是在便利商店工作,彷佛不會在人生履歷表留下太嚴重戳記。(我在這裡是指文學中的妓女,跟現實生活中血汗勞動的性工作者不同。)這種似乎可以剝下來丟到腦後的身分,予人「重新開啟新生活」的美好妄想(但妄想往往落空)。
因為妓女在文本敘事中具有多種能耐,台灣文學長期利用了妓女:許多描寫妓女的文本與其說在再現妓女,不如說是藉著妓女這個平台(platform)討論貴與賤、性與愛與錢、不被禮法制度接受的情感,以及不/可以倒帶重來的人生。
在各國的同志次文化與同志文學中,娼妓跟同志也是牽連的。許多人為了要去除同志的污名,於是刻意將同志打造成正大光明的形象,剔除同志跟娼妓等等社會邊緣人的瓜葛,以求被主流社會接受;然而,這種粉飾太平的作法是削足適履的:被削的足是同志,被削去的部分是娼妓,而履是主流社會。同志與娼妓,以及各種人(不限於同志)跟娼妓,都有可供細談的多種關係,在此我僅針對台灣同志文學來談。
有些同志自嘲是妓女,或是挪用性工作者的某些術語:紅牌、酒女、大班、下海、從良、釣凱子等等。這些說法都是將娼妓種種視為隱喻,利用娼妓來指涉同志,一如利用玫瑰花來象徵愛情。這種聲東擊西的策略,未必是作者本人有心的設計,反而往往是來自讀者隨心發展的常規。
白先勇的同志文學成就,除了《孽子》之外,他的短篇小說集《台北人》最為耀眼。然而《台北人》其實只收錄了兩篇明顯展現同性戀的小說:〈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和〈孤戀花〉。前者除了聚焦在男同志聚集的台北新公園為主要場景,也提及「小么兒」游晃的三水街──從小說上下文來看,這批「小么兒」是類似流鶯的少男;後者主要人物是中國和台灣的酒家女,她們為了錢而取悅男人,卻也享受同性取暖。這兩篇小說都證實了同志跟娼妓的緣份匪淺。不過吊詭的是,長久以來,這本小說集裡頭最為讀者們(含同志讀者)津津樂道的兩篇小說,卻未必是〈滿天裡〉和〈孤戀花〉,而是〈永遠的尹雪艷〉和〈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尹〉〈金〉兩篇小說只突顯了性工作者,並沒有提及同性戀。然而,據我主觀猜想,〈尹〉〈金〉兩篇小說帶給台灣同志文化的影響力可能遠勝過〈滿〉〈孤〉兩篇小說。
具有某種身分認同的讀者未必只能在同一種身分認同的文學人物中獲得共鳴。許多具有強烈台灣本土意識的前輩作家,其實是在閱讀歐美文學(而非中國,或日本,或台灣的文學)中獲得啟發與力量。同志讀者在《台北人》中特別看重的角色,未必是小說集中的同志,卻可能是書中的煙花女。妓女看盡性愛剝離的境遇,可能把同志的心情說得更清楚。〈尹〉〈金〉不是同志文學文本。但是讀者(含同志,非同志讀者)往往可以在非同志文學文本中獲得貼近同志的啟發。我不禁聯想,在台灣同志的公眾歷史中,張愛玲其人其作舉足輕重,但她影響讀者的作品並不是同志文本(後來面世的〈同學少年都不賤〉固然也可以算是同志文本,但這一篇其實並沒有參與台灣同志公眾史)。談同志文學,並非只能鎖定具體展現同性戀人證物證的文本──難道還要活在另一座衣櫃裡嗎?──而要讓閱讀的欲望解放流動到各種文本上。
〈尹〉〈金〉 兩位主人翁相同之處,都是因為性事而被視為卑賤,但她們都力圖整頓自己,在俗世面前保持尊貴。但尹金二人也提供了兩種典範,讓同志各自認領。尹堅持性愛分離,而且拿錢不手軟;她保留性工作者的身分,並無意洗手。金則心軟承認性愛的接合;她蛻去性工作者的身分,以為身分就像衣服一樣穿脫。聽說卸下同性戀身分改當異性戀的人形同「走出埃及」,那麼尹形同「留在敘利亞」而金「走出敘利亞」。
在邱妙津的短篇小說集《鬼的狂歡》中,名作〈柏拉圖之髮〉就建立在賣淫的基礎上。如果沒有性產業,文中兩名女子還沒有認識的機會。如果沒有假借買春的名義,這兩名女子還找不到膩在一起的藉口。
故事是這樣的:一位男性金主為了幫助熟女小說家尋找寫愛情小說的題材,便出資讓熟女去認識阻街女郎。熟女扮成男人,開著金主的凱迪拉克去找妓女──這裡的凱迪拉克換成積架也不損象徵意義,因為它僅僅代表了富有男人的霸與俗。她在眾多阻街女郎之中看中一名少女,便跟少女「簽約」,藉此「花錢買一次模擬愛情的男人經驗」。從此熟女帶少女回家同居。這篇小說固然陳述了「同性戀(熟女和少女之間)vs 異性戀(少女與眾恩客之間)」,但這個對比其實「寄居」(像寄居蟹那樣)在另一個對比中:「沒有金錢涉入的愛 vs 金錢交易的性」。少女跟不愛的男人們頻頻上床,與其說是因為她有異性戀的身分,不如說她有妓女的身分;少女不跟熟女上床,與其說是她沒有同性戀的身分,不如說她寧可用性來(跟男人)賺錢。不要怪異性戀至上,要怪就怪金錢至上。小說中強烈的性偏好焦慮,轉嫁到金錢上面去了。性交易化為勉強遮掩同性戀的面紗:如果熟女跟少女的恩愛曝光了,她們兩人都可以宣稱自己不是同性戀,而「只是」買春者和賣春者罷了。
在陳雪的成名作《惡女書》中,最有名的短篇是〈尋找天使遺失的翅膀〉。台灣同志文學選集的英文譯本《Angelwings》(天使翅膀),就採用了陳雪小說的意象。台灣的讀者可在books com tw 找到此書,北美的讀者可在amazon找書,自用送禮兩相宜──事實上我在美國在台灣都採用這本小說集當教材。在〈天使〉中,主人翁女孩跟她母親的愛恨情仇是全文觀點,而主人翁遺失母親的主因就是母親從事性工作去了。母親給主人翁「不明確的愛」,理由是她把錢放在愛的前面;而母親的「阿凡達」(avatar,或稱化身)阿蘇,卻寧可甩開口袋塞滿鈔票的男人們,讓主人翁搭她的積架(等於邱妙津所寫的凱迪拉克)(應是賣淫收入所購得),讓她跟著名建築師(讀作:有錢有勢的男人)玩兩女一男的 3P。性產業讓天使失去了翅膀,卻也找到了翅膀。〈柏拉圖〉〈天使〉提出不同的問題:前者在問「是不是,能不能」,而後者在問「失去還是得到」。
吳繼文的《世紀末少年愛讀本》取法於清朝陳森的章回小說《品花寶鑒》,形同在當代台灣重新想像大清國,堪稱台灣文學與同志文學中的奇葩。這兩部小說各有千秋,值得細談。在此我只想點出:兩部奇書主要是藉著呈現少男性工作者和他們的恩客來呈現男男愛欲(但「主要」之外還有「次要」;「次要」的部分尤其精彩,並且在《品花》之中尤多──那就屬於《中國同志文學史》了)。也就是說,男男恩愛被人質問時,他們可以推託兩人只是「主客關係」(那年代也無「同性戀」「同志」等等概念),可以託稱兩人結合只是為了賺錢(如果這兩位是比較低階的角色),也可以宣稱兩人結合只是為了青春之美而心生青春崇拜之情,而不涉及性也不計較錢。古人不懂同性戀,但他們懂同性之間可以買賣。
吳繼文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天河撩亂》也是驚世之作。書中主人翁時澄在1970年代離家到台北補習重考大學,卻心浮氣躁,在電影院第一次看了《魂斷威尼斯》(此片是OKAPI老朋友了),驚覺電影院內男男觀眾趁黑互相手淫的生態。一回在中華商場(欲見舊址實況請看蔡明亮導演的《青少年哪吒》)漢口街偶遇日本男子搭訕,他們去林森北路聽歌,跟日本人回他的旅店,上了床,拿了錢。從此,他開始忍不住常去中山北路和林森北路之間的巷子勾引日本觀光客,跟他們上床收錢。有人一次給他一百美金,可供他三個月的生活。有人拿出很粗的電動按摩棒硬塞時澄,結果不歡而散。他賣淫一個月,被朋友發現;面對朋友的逼問,他沒說他在搞同性戀,也沒說他在賣淫(或據他本人定義,是「出賣身體外加廉讓靈魂」),而說:「沒什麼,就是玩玩。」
時澄是愛性的男同性戀者嗎?或許吧。但他將自己的身分解讀為愛錢的賣淫者。而被朋友質問時,他又將很沉重的身分(賣淫者)說成很輕鬆的行為:「沒什麼,就是玩。」
身分A變成身分B又變成行為C。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有些同志說起自己的往事,會說:「當年愛玩嘛。」這是說當年貪愛做愛?還是說當年賣淫?語言的曖昧,就是同志進可攻退可守的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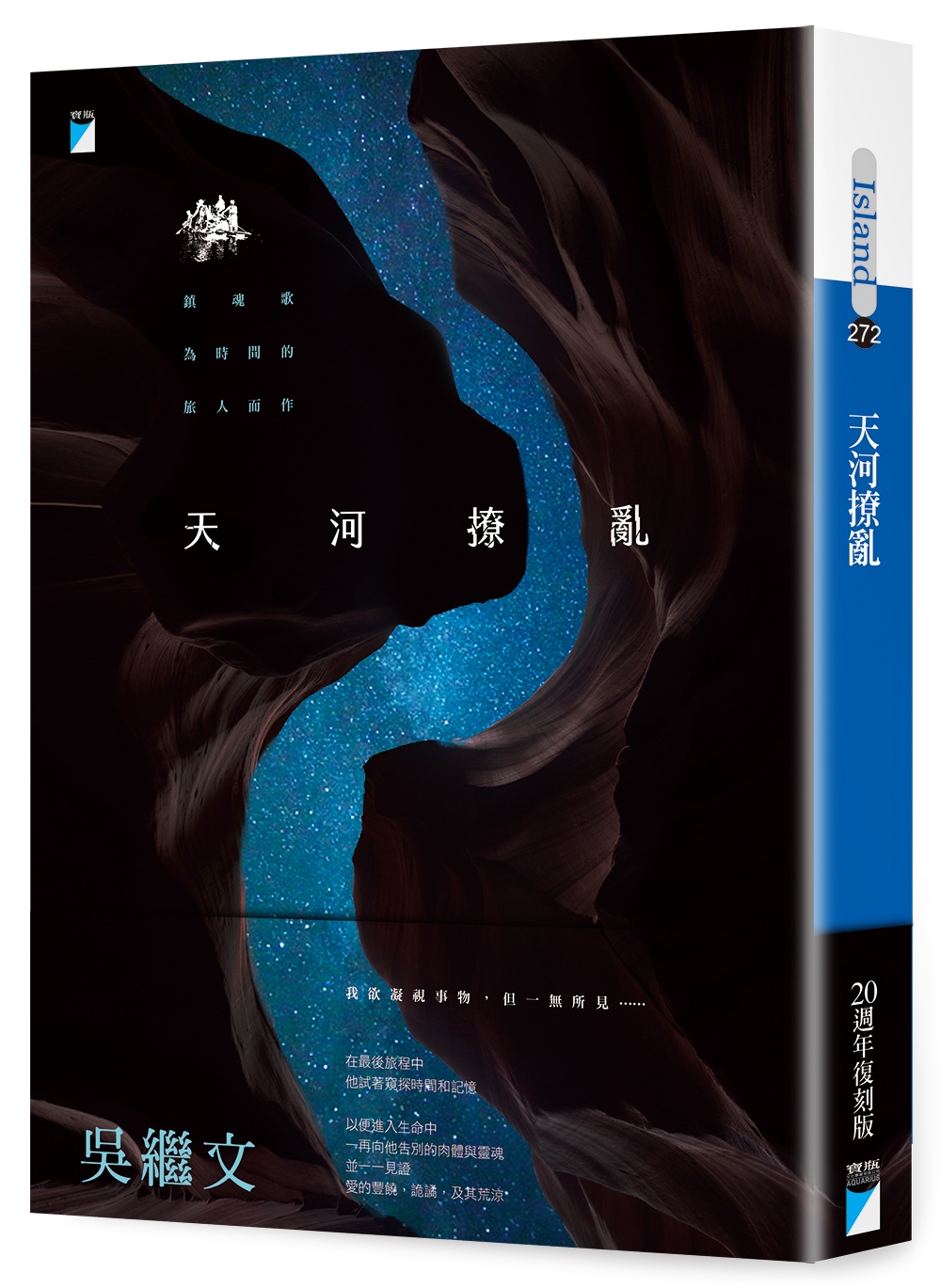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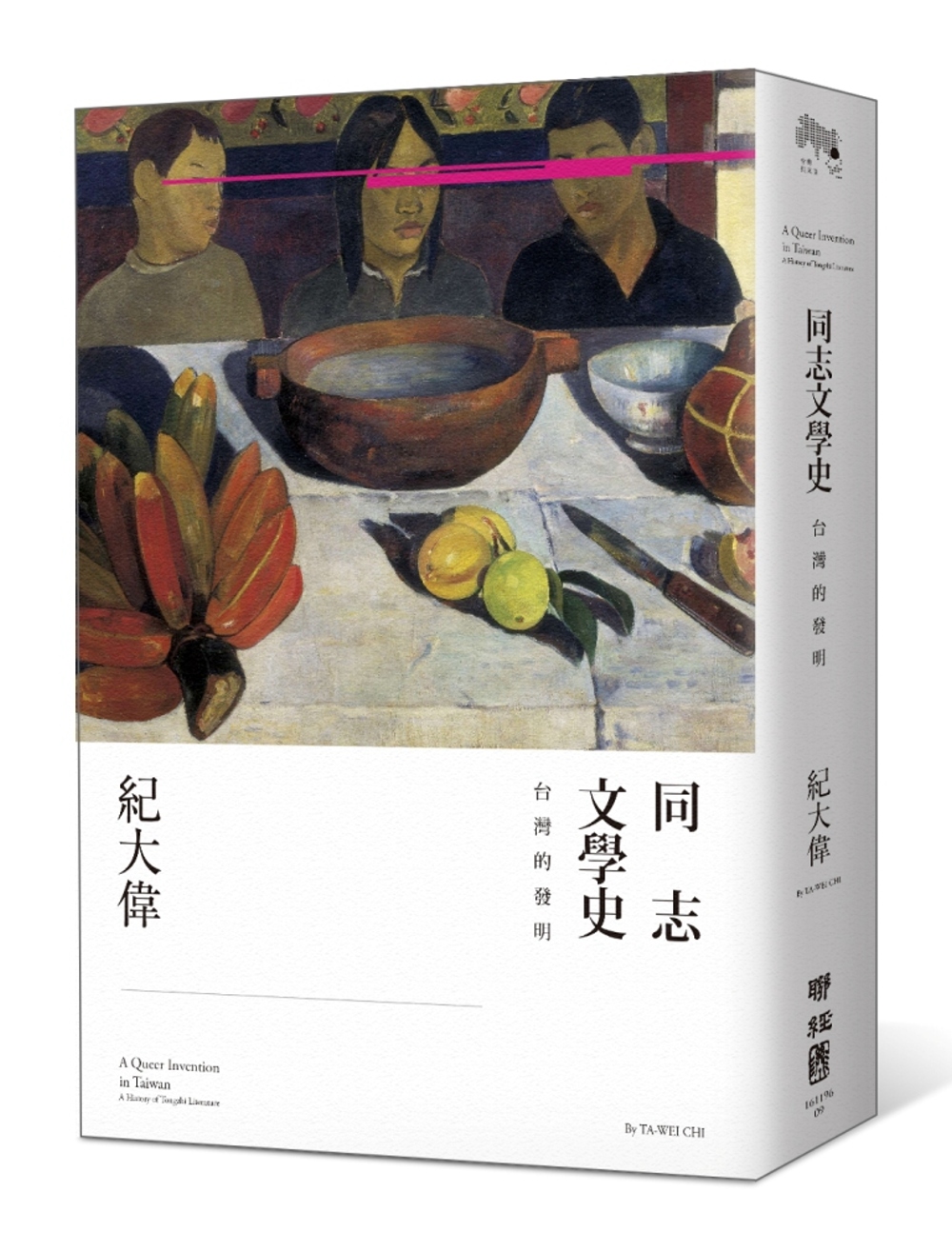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