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什麼才會讓讀者甘願進入這本書?像是,其中一篇〈貓派〉(即書名由來)發表後得到三百萬人次的轉發,作者一舉成名天下知,還得到了超過三千萬台幣的預付版稅?還是說得驚悚一點,若《一代宗師》的台詞是「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那作者克莉絲汀.魯潘妮安(Kristen Roupenian)要說服你的可能是:「每段愛情,都是劫後餘生。」
沒錯,打從那句「以分手不分屍為前提來交往」的台詞浮上檯面,結束一段感情,不是每個人都能「全身而退」的。世人紛紛發出純真的疑問,為什麼會這樣呢?在魯潘妮安的筆觸下,愛情本來就很危險,而且愛情(被我們搞得)越來越危險,我們一心往愛情死去,真正沒戲唱了,又滿臉納悶自己是怎麼死的。《貓派》12個故事告訴你,人是怎麼邁向深淵,又如何逃過一劫。最棒的是,她的文字好讀極了,絕對不是那種你雄心萬丈地買來,讀了幾頁,再次睜開眼睛發現自己睡死了的那種「經典」。
先從代表作〈貓派〉說起。
「到底是誰先撩誰的,瑪歌和羅伯特的答案可能不太一樣。」(這句話有個更通俗的版本,我們的父母都認為:是他先追我的。)瑪歌在影城的販賣部打工,她習慣跟客人搭幾句話,道理很簡單:這對小費有幫助。第二次,羅伯特提出要求,瑪歌給了自己的電話。兩人開始傳訊息。後來,兩人在販賣部之外的地方碰面,羅伯特買了一些小東西給瑪歌,瑪歌以為最後要來個吻,誰知羅伯特吻了她的額,瑪歌很樂,她回家,跟父母說自己在談戀愛。兩人下一次見面時,進度往前,他們要去看電影。在車上,羅伯特很安靜,瑪歌閃過一個念頭:她可能會被帶到任何地方去先姦後殺⋯⋯。羅伯特沒殺她,但他們之後的約會不太順利,反覆冷場、尷尬,感覺羅伯特有點受傷,瑪歌想照顧他,沒想到很快地瑪歌變成那出糗的人,瑪歌不知所措,哭了,換羅伯特很樂。瑪歌慢慢懂了,「她開始覺得更了解他了——他非常敏感,非常容易受傷——這讓她覺得離他更近了,也更有力量,因為一旦知道怎麼傷害他,她也就知道如何撫慰他。」瑪歌終於跟羅伯特回家,但羅伯特一連串笨拙的反應,瑪歌冷了,不過瑪歌很有禮貌,決定幹下去,「她認為自己拿不出必要的機智和委婉。她不是害怕他會逼自己做她不願意的事情,而是在她為了促成這件事做了那麼多動作後,又堅持他們現在停下來,會顯得她有公主病,很任性,就像是去餐廳點了東西,等食物送上桌,又改變心意要退回去一樣。」
兩人開始做愛。
後續的描述超精彩,容我在此保留,去說另一個「大同小異」的故事,朋友A在交友軟體內收到一堆屌照,她甚至沒開口,那些屌照便如雪片般飛來,A花了一段時光,想明白了,「原來那些人以為屌照會讓我興奮,天,他們為什麼不問問我呢?」瑪歌跟羅伯特的性愛,差不多也是這樣一回事。羅伯特做了許多跟發屌照一般解high的行為,瑪歌忍耐,理由同上,她不想被認為有公主病,也可能瑪歌始終沒鬆懈心防,何況她在羅伯特的房子裡,先姦後殺,不是不可能。
從〈貓派〉這篇小說,你很難不驚覺到作者控制議題走向的能力,她一方面暗示讀者「這些男人可能危險又噁爛」,一方面又讓她筆下的女主角對這分危險升起一股「與性興奮有關、但有悖常情的恥辱感」。類似的情感亦可見於〈看著妳的遊戲,女孩〉,少女潔西卡與一位髒兮兮又模樣齷齪的男人打過幾次照面,男人借出莫名其妙的錄音帶,要求潔西卡在12點時於公園交還。潔西卡沒去,之後鎮上發生少女遭人綁架的案件。警方費了一點心思才釐清這案件與潔西卡口中的「查爾斯」無關。很多年後,已為人母的潔西卡,立於窗前,「凝視著外面浩瀚、可怕、光芒刺穿的夜晚,發現自己好奇著查爾斯是否還在公園等待她的到來。」理智上,「查爾斯」可能不是壞人,但他先前的言行舉止也不像善類,為什麼潔西卡依然升起一思憧憬?答案並不難猜,即使對方的儀態令人作噁,他的等待或喜愛,仍不失為一種對自身存在的崇高讚美。可以在幻想中無數次放一個人鴿子所帶來的權力感,是潔西卡越年長,越不想錯過的精髓。〈鏡子、桶子與老舊的大腿骨〉和〈火柴盒症〉則以魔幻的敘事,帶出「女人的感受不容小覷,有時那是你在愛情裡最重要的保命符」。作者真的很敢寫。
我最喜歡的故事是〈一個好人〉。
故事的框架很庸俗也很前衛,關於花花公子泰德的「上半生」。青春期的泰德超土,是個魯蛇,他深愛安娜,但安娜迷戀前男友足球運動員馬可,泰德跟一個魯妹瑞秋走得很近,不知怎麼地還做了。安娜弄了一堆噁爛的事跡來挽回馬克,一堆人懷疑馬克還因此聲請了保護令。泰德打從心底唾棄、憎惡瑞秋,又受不了誘惑,一再搞她,一再幻想著安娜。簡言之,這是一個「我愛你,你愛她,她又愛他」的復古格局。但,作者的嗜血風格,讓這篇好看得要命!因為她反對淒美,專攻這種格局裡每個人內心的張牙舞爪與「朕不給,你不能搶」的小氣巴拉。
弔詭的是,我們並不難從泰德、安娜與瑞秋的身上,憶起自己在感情裡也曾多麼醜陋。承認吧,誰不曾壓抑過打電話騷擾某一位前任的慾望,或明明也沒喜歡誰,但又無意拒絕他一再端上的好意(為什麼要拒絕呢);或是,深諳對方把自己當備胎,但仍渴望有所進展的心機。我們如同《寄生上流》裡的司機金基澤,明明熟稔自己的位置,又會不自禁地在難得愉快的場景下,做出踰矩的提問,有時我們沒有意圖,身上的氣息或瞬間尷尬的表情,即出賣了我們。
我由衷佩服作者魯潘妮安那樣放膽地描寫在異性戀的框架下,一切的套路是如此地乏善可陳,非分之想因而代替我們鋌而走險,越來越「勃大精深」。我們都被「先認真的人就輸了」、「曖昧比直來直往更高級」這些話給潛規則了,搭建出一套華而不實的對談邏輯,聊到天長地久,卻發現我們一點兒也不了解對方。這是社群媒體時代所豢養出的社交障礙,我們看似更擅長(也更喜歡)與自己腦補與幻想出來的阿凡達相處。作家精準地勾勒出這些蒼涼、病態與蠢。最讓人驚艷的是她並不輕易讓人感受到誰對誰錯,她只是以一種無所謂的中性姿態點出了「這就是我們」。
甚至,更進一步說,#Metoo以後,討論風起雲湧,核心議題隱約浮現:「與慾望有關的意願,能不涉及權力支配嗎?」這是個艱困的議題,論述的舉動,即可能被視為挑釁。我很驚喜在必然的磋商與試探中,文學再一次地填補了這真空。如同〈死亡願望〉,作者透過女孩賈桂琳的要求,驟然飆起高音:「我希望你同意尊重我的意願,做我要求你做的事情,因為這對我真的很重要。我想要我們一起去洗澡⋯⋯然後,過一段時間——這很重要——在我沒有預料的時候,我希望你用最大的力量狠狠打我的臉。打了我之後,等我摔倒了,我希望你踢我的肚子,然後我們就可以做愛了。」
《貓派》12個故事,如貓踩紅線,姿態輕靈,反覆調度你的恐懼。她越是重申「你知道你需要這個」,讀者越惶恐不解,我、真的、這樣想嗎?我需要書中所指的這些怪物嗎?我也震懾作者反覆拆解、挖掘再挖掘一個沒有多少作家有能耐處理好的問題:「過於渴望被愛是否可以視為一項缺陷」。這份飢渴,時常讓我們這秒鐘甘於受暴,下一秒鐘又成為真兇。
我們慢慢意識模糊,是愛情枯萎了所以我們動手?還是我們先凋零了愛情才對我們飽以老拳?我想起泰德的台詞,「好泰德底下有一個壞泰德,沒錯,但是在那下面有一個真正是好的泰德,但從來沒有人見到他,他這一輩子都沒有人見到那個他。在一切的底下,我只是那個只想要被愛的孩子,但我試了又試,試了又試,還是不知道怎麼讓那件事發生。」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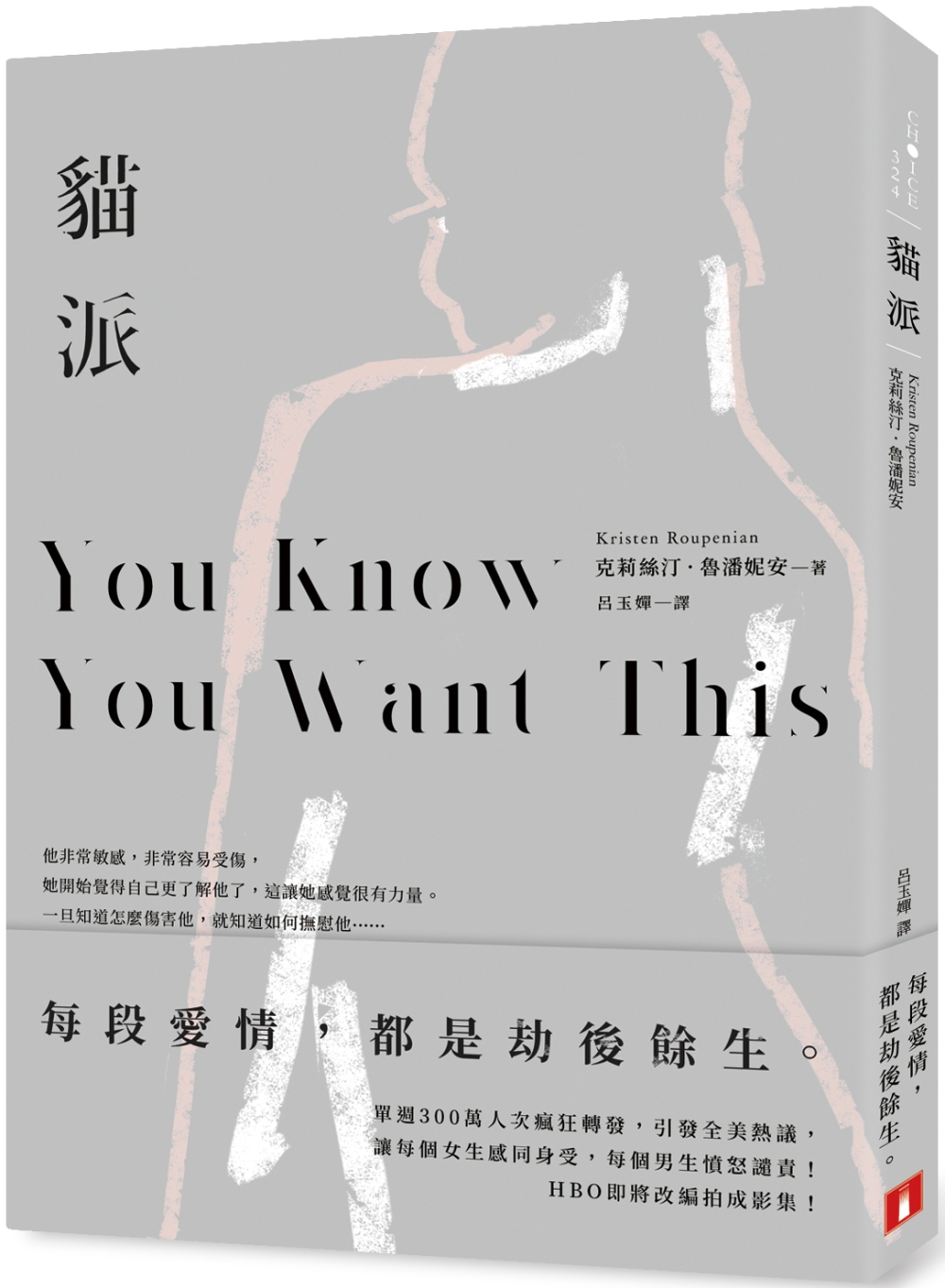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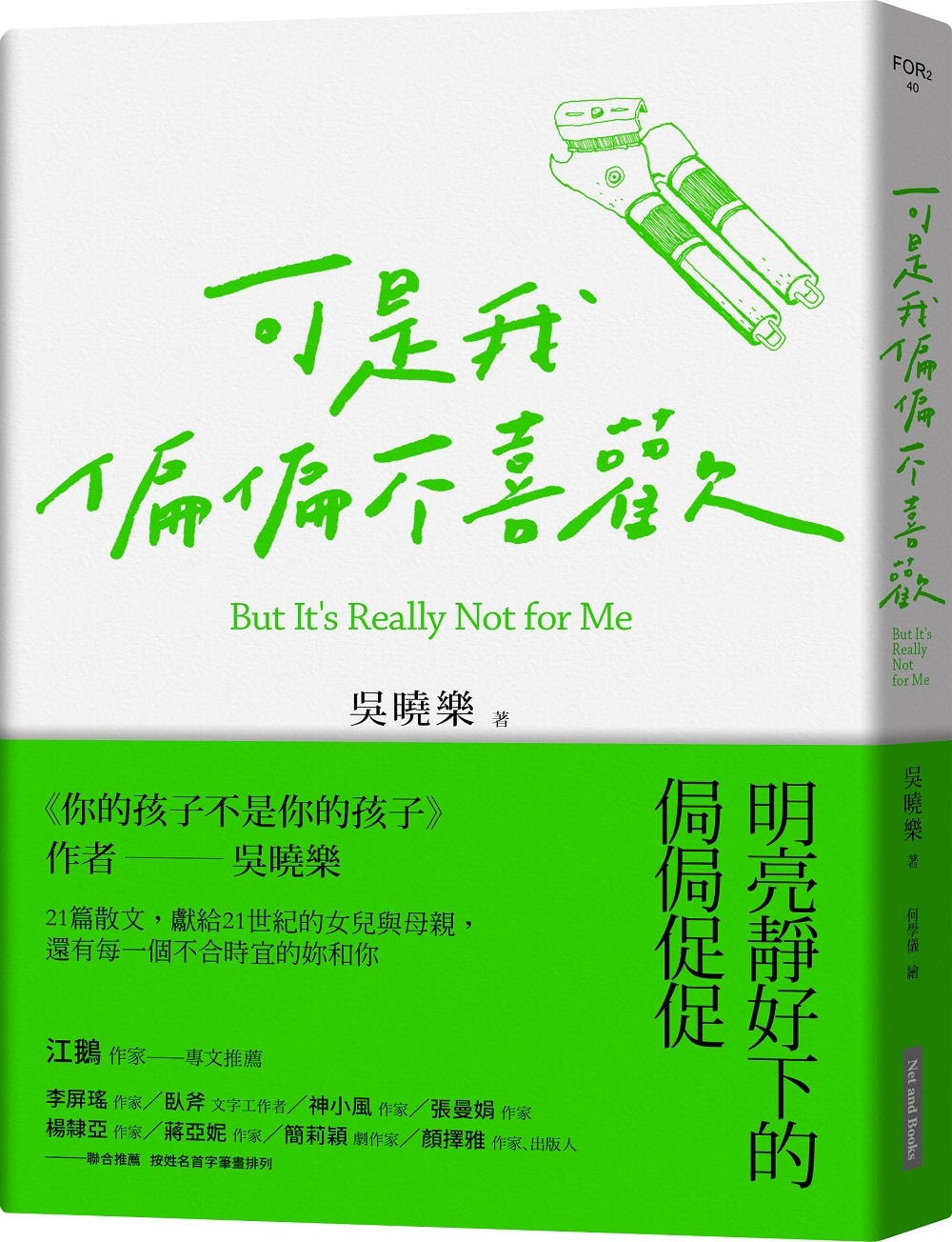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