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花了大半年編輯《每日讀詩詞:唐詩鑑賞辭典》,然後無縫接軌編輯《每日讀詩詞:唐宋詞鑑賞辭典》,同樣的詩人,筆下卻有不同的面貌,乍看之下不免大驚:您發生了什麼事?
轉性的是人,還是作品?
例如,晚唐詩人溫庭筠的詩,其名句「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過陳琳墓〉),就是一個典型的才識俱高而不得志的文人。但這位最早大量寫詞的唐人,在詞中滿是閨婦、思婦、怨婦,寫不盡的寶函鈿雀香腮雪,畫羅翡翠金鷓鴣。著實令人起疑,這是女性服飾的業配文嗎?
再來看和溫庭筠齊名的韋莊,這人不得了,「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一首〈秦婦吟〉寫盡黃巢之亂時的慘狀。他會寫什麼樣的詞呢?一樣是閨婦、思婦、怨婦,春欲暮、花不語,出蘭房、別檀郎。
不理國難與仕途,只要做自己
雖然理智上知道,詞一開始是在飲宴場合給歌妓唱的,有些詞甚至是文人即席寫的,本來也不需要登大雅之堂。在溫柔鄉那卡西的場合,當然是唱〈孤女的願望〉或〈粉紅色的腰帶〉,難不成唱〈梅花〉或是〈中華民國頌〉?但是看的詞愈多,愈覺得案情不單純。不可能的,如果單純只是娛樂用途,何必耗費那麼多的筆墨力氣精雕細琢(或是粉雕玉琢)?從詩到詞的轉變,這些文人想要表達的到底是什麼?
讓我們接著看看以溫、韋為代表的五代花間詞人們,一時亡國一時慘,一直亡國一直慘,但是放著國仇家恨不寫,一樣只關心薄妝桃臉、豔情多,愁眉黛綠、郎不歸?
知名的亡國之君李後主,亡國前寫的詩詞都是燦爛沉醉的流金歲月,「臨風誰更飄香屑,醉拍欄杆情味切」(〈玉樓春〉),亡國後只能追恨那欄杆啊,「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虞美人*〉),他始終表現自己的真實心情,OK,很好懂。他是當時少數在詞中清楚直接表達自己想法的作者,或許身為國君,不須隱藏自己的想法吧?
*註:據宋人王銍《默記》記載,這首〈虞美人〉是李後主的絕命詞。他亡國之後被軟禁,這一年的七夕生日時,不僅找歌妓唱了「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而且還唱得很大聲。宋太宗聽說之後大怒,就派人送毒藥去給李後主。劇終。
等到大宋開國,第一個以詞聞名的文人,正是寫「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雨霖鈴〉)的柳永。但是啊,詞既然是飲宴場合給歌妓唱的,你以詞聞名,不就是每天在青樓酒館的意思嗎?身為一個士子讀書人,這樣可以嗎?當然不可以,據說柳永曾寫「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鶴衝天〉),後來他考進士時,宋仁宗看到他的名字就說:「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然後他就落榜了。柳永這人也很妙,他原名三變,聽到之後乖乖遵旨,這可是皇上要我去淺斟低唱的(嘆),所以自稱是「奉旨填詞柳三變」。(可參考宋人吳曾的《能改齋漫錄》和嚴有翼《藝苑雌黃》)
古代讀書人唯一出路是科舉考試,他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後來他改了名字,終於在近50歲時才考上進士,但是一生潦倒,死後葬在仙掌路,淸王士禎嘆息:「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為弔柳屯田?」(〈真州絕句〉)寫了曉風殘月的柳永,死後只有歌妓年年到墳前憑弔。
沒有一個讀書人會刻意拿自己的前途開玩笑,但柳永偏偏又寫了大量的詞,這中間的反差,應該就是他持續寫詞的原因吧?或許,詞中隱藏了許多沒有直接說出來、卻又不能說出口的話,因此他才一首一首寫下去?
隱藏在詞裡的個人心事
直到讀了晏殊的〈破陣子〉,我才覺得自己有點懂詞了:
燕子來時新社,梨花落後清明。池上碧苔三四點,葉底黃鸝一兩聲,日長飛絮輕。
巧笑東鄰女伴,採桑徑裡逢迎。疑怪昨宵春夢好,原是今朝鬥草贏,笑從雙臉生。
這首詞乍看很單純,在一個燕子飛來的春天,清明節時良辰美景當前,雖然梨花已落,但有碧苔、黃鸝、飛絮,聲色俱佳。幾個採桑女互相調笑,笑得這麼開心,並不是因為昨晚做了春夢,而是因為今早鬥草(比賽看誰撿到最奇特的草)贏了。
晏殊這位太平宰相,真是好閒情逸致,寫了一首這麼清新的詞,念起來都心情愉快了。但是等等,再念一次,「池上碧苔三四點,葉底黃鸝一兩聲」,這兩句話好耳熟,是不是很像杜甫〈蜀相〉寫的「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當時能當到宰相,絕對是飽讀詩書的,這不可能是巧合,是不是晏殊在這個春光明媚的場合,突然想起了杜甫,或是突然想起了宰相諸葛亮,所以才寫下這兩句?
再往下「東鄰女伴」,就算真的是住在東鄰的女生吧,會特別拈出「東鄰」,一定也想到了戰國楚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吧?晏殊是要說這位採桑女跟宋玉東鄰的女伴一樣美貌,「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還是要說自己如秦章華大夫,見到美女仍沒有逾越禮義界線?接著「笑從雙臉生」,這分明是拿這位採桑女類比王昌齡「芙蓉向臉兩邊開」(〈采蓮曲二首〉其二)的採蓮女嘛。
寫一首詞,心思這樣千迴百轉。他的骨子裡還是那個傳統文人,還是宋玉、王昌齡、杜甫,只是有些心情不適合直接說出來,然後我突然就懂了,何謂「詞之妙,莫妙於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清劉熙載《藝概.詞概》),沒說出口的,才是他真正想說的,不是不說,只是借用別的事情來說。或許有點隱晦,但杜甫〈蜀相〉中的「兩朝開濟老臣心」,應該常常縈繞在他的心頭吧?所以在這個春光嫵媚的日子,看著青春正盛的採桑少女,才會寫出這首詞。
這時覺得,有人將這幾位少女的笑容,以這樣的方式留下來,真是太好了。這不是逞弄筆墨而已,葉底黃鸝、東鄰女、鬥草、雙臉,修辭就是他與世界相處的方式。這麼一想,溫庭筠等花間詞人,是否因心中有不能明言的哀傷,只能寄託於「裁花剪葉,鏤玉雕瓊」(歐陽炯〈花間集序〉語)的華麗詞藻呢?

詞是與世界相處的方式
再回頭看柳永,再讀一次〈鶴衝天〉: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他說「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又豈是不在意浮名?這正是杜甫的「何用浮榮絆此身」(〈曲江二首〉其一),那是知道自己永遠得不到上流權貴的賞識,只能苦中作樂,買醉佯狂。只是他不能明說,「非不言也,寄言也」,雖然自認是不受重用的「遺賢」,是有「卿相」之才的「才子詞人」,但他假裝只喜歡留連煙花巷陌、偎紅倚翠,甚至說這是平生暢事。
但這樣的心情為什麼不能寫詩,而要寫詞呢?因為當時的文人,對於「詩」已經有根深柢固的概念,從《詩經》以來,就是「詩者,志之所之也。」(〈詩大序〉),詩是要言「志」,這些幽微隱約的心情,怎麼能用詩來寫呢?所以,詩正正經經的,那是工作用的帳號,詞才是私人哀居帳號,或許其中傳達的是更真實的心情吧。
不過凡事必有例外。「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這是屬於柳永的纏綿,「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則是蘇東坡的曠遠。據說蘇東坡曾問幕僚,他的詞和柳永相較之下如何?幕僚說:「柳郎中詞宜十七八女孩兒,按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明楊慎《詞品》引宋俞文豹《吹劍錄》)
蘇東坡也是一生屢遭貶謫,仕途不順,但是紅牙板和鐵板、十七八女孩兒和關西大漢的差異,就是蘇、柳與世界相處的方式不同*。
*註:蘇東坡這位當時的搖滾巨星,非常在意柳永這位鄉村歌手。另有一次他寫了〈江城子.密州出獵〉這首狂氣四溢的詞,「老夫聊發少年狂」。得意之餘,忍不住寫信跟朋友說:「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算是文學史上少數留名的「呵呵」。
生命應該浪費在修辭上
不只是柳永,蘇軾處處與人不同。另一個有名的例子是「蘇門四學士」之一的秦觀,某天進城去見蘇軾,蘇軾問他最近寫了什麼詞?
秦觀:「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
蘇軾:「十三字只說得一個人騎馬樓前過。」
(清王弈清《歷代詞話》引宋曾慥《高齋詞話》)
秦觀因為有細膩的觀察力,他眼中的世界是飽滿豐富的,他不僅看見車馬馳過,還看見香車寶馬,而且是「繡轂雕鞍」的車馬。但是蘇軾只關心:發生了什麼事?你咬文嚼字的,不就是「一個人騎馬樓前過」嗎?
兩人眼中的世界如此不同,就算同樣是寫〈鵲橋仙〉牛郎織女,秦觀說得深情款款:「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蘇軾呢,他說相聚分別,最好是像在緱山成仙的王子喬,時間到了揮揮手,該走就走,「不學痴牛騃女」。
我曾經以為,各種寫作方法或是修辭技巧,只是創作者為了標新立異,或是與別人、前人區隔而採用的方法,實在不需要深入研究,雕琢文字只是雕蟲小技。韓愈就說了:「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調張籍〉),不要浪費時間在經營自己的詞句啊!李賀也說:「尋章摘句老雕蟲」(〈南園十三首〉其六),在經營章句之間逐漸老去,多麼可悲。
不過為了發現這些詞如此動人的祕密,我才了解,原來各種寫作方法,不只是一種文人的技巧,根本就是詩人思考與觀看世界的方式。這麼一想,豁然開朗,原來當我們掌握了多少種寫作與修辭方法,就掌握了多少種與世界相處的方式,也就有多少種感動的可能。
【每日讀詩詞】唐詩 / 唐宋詞 系列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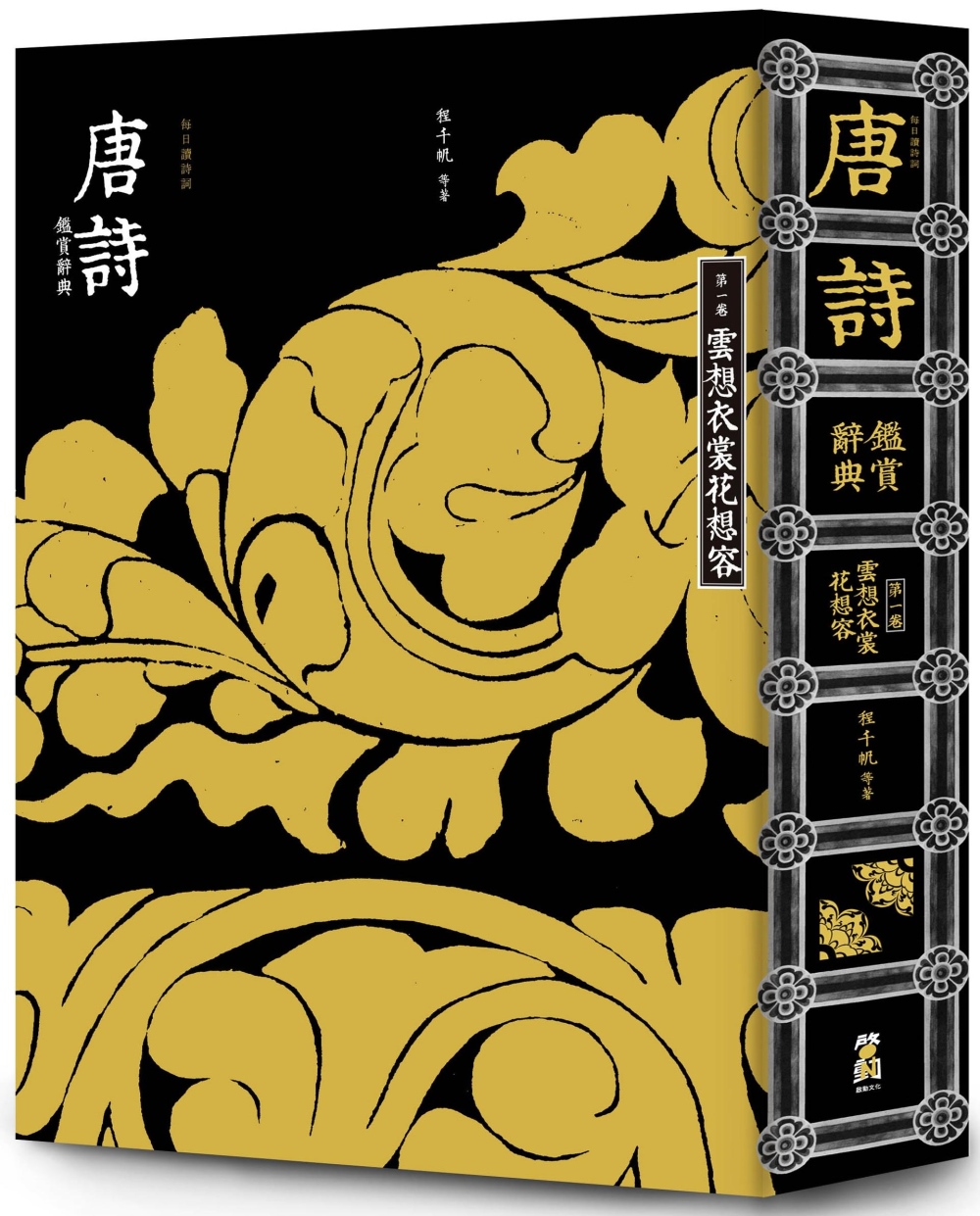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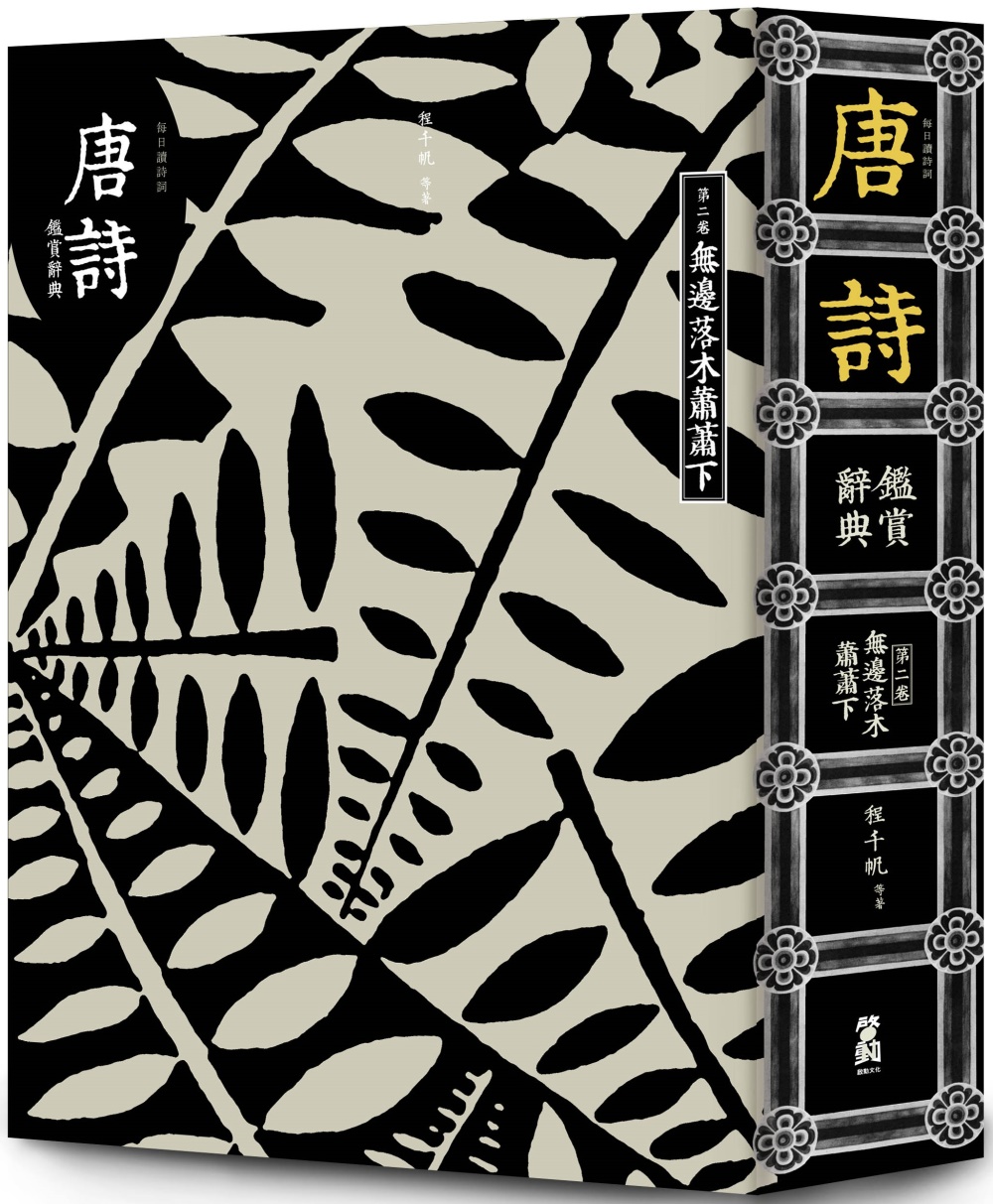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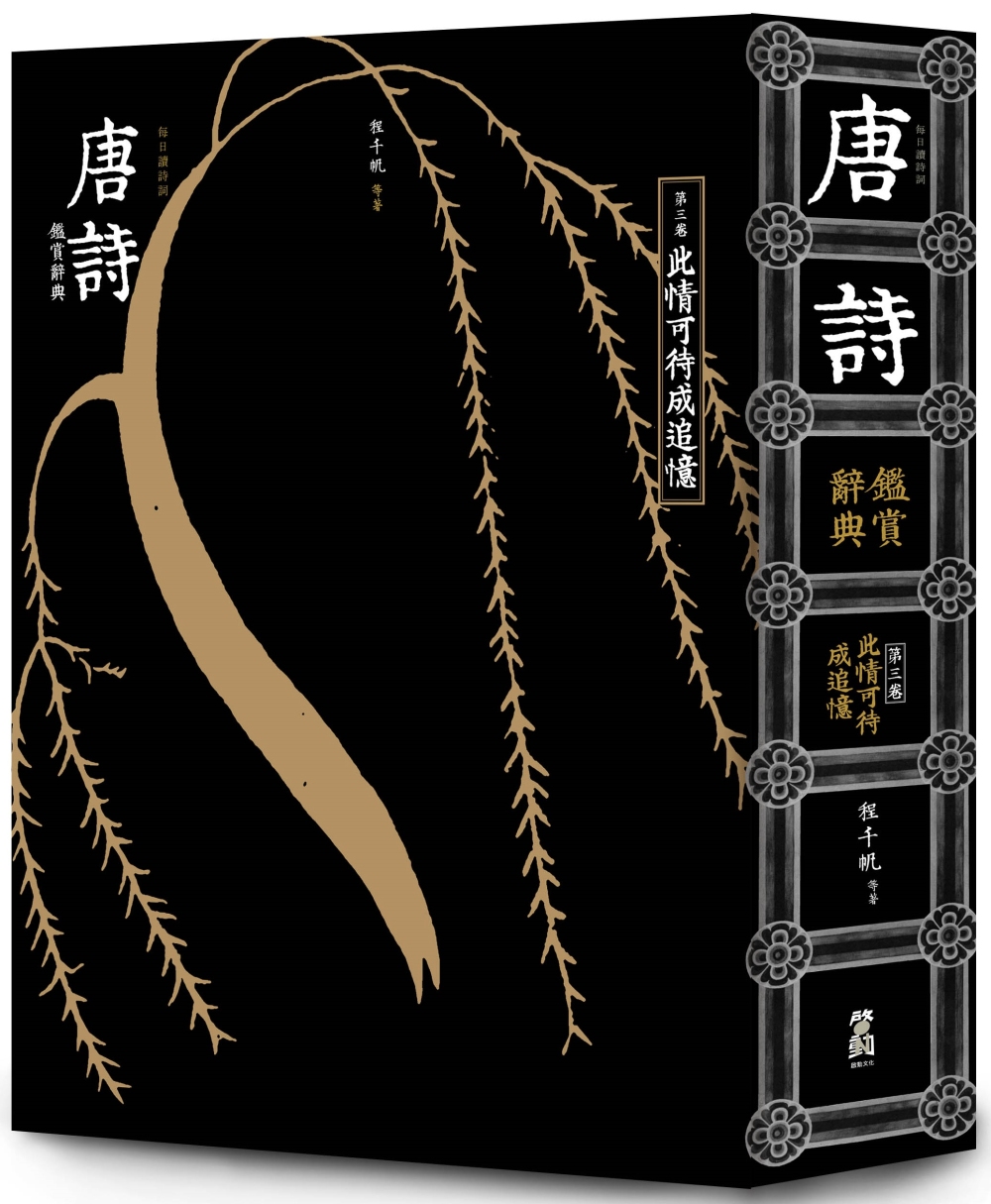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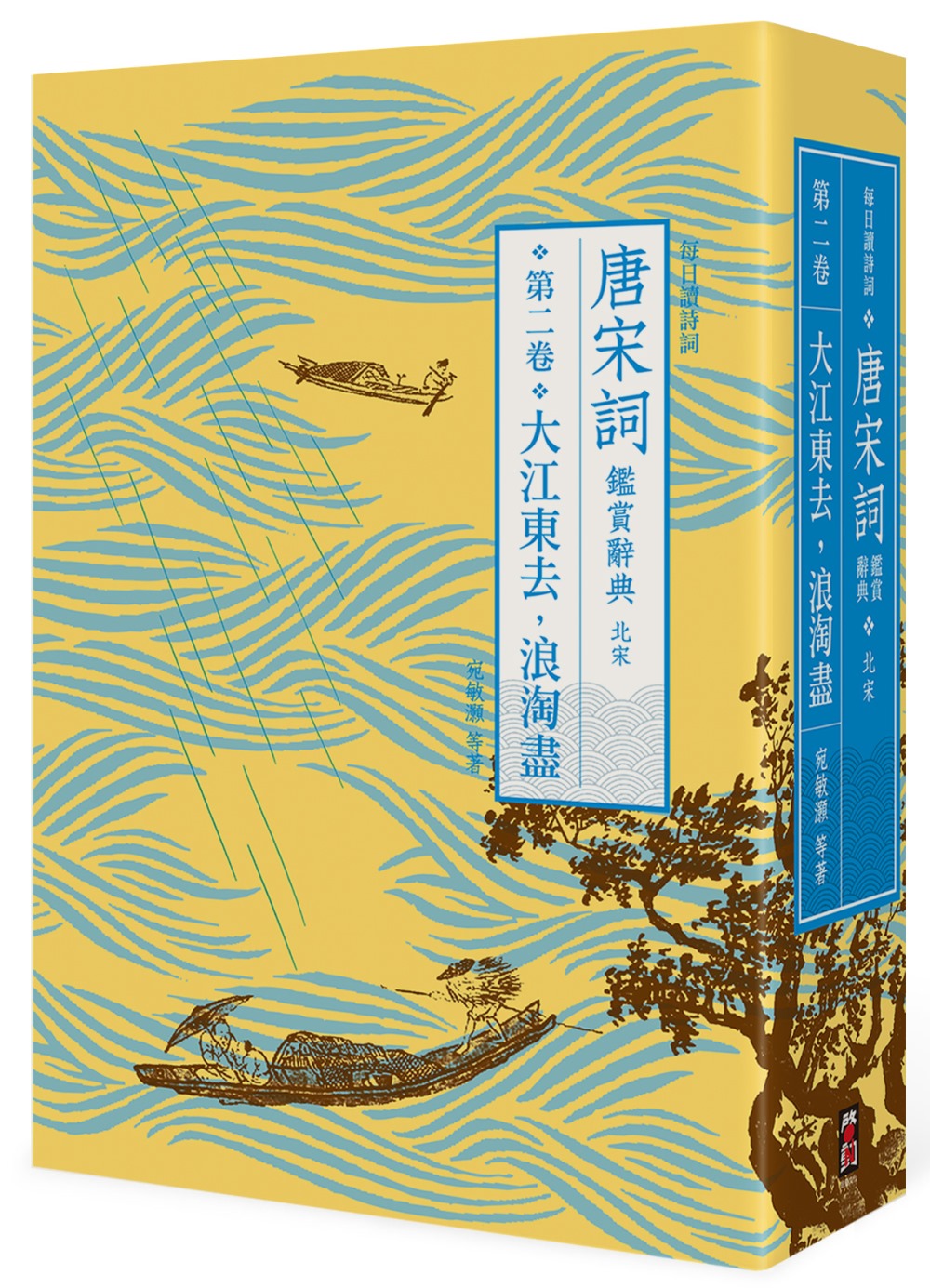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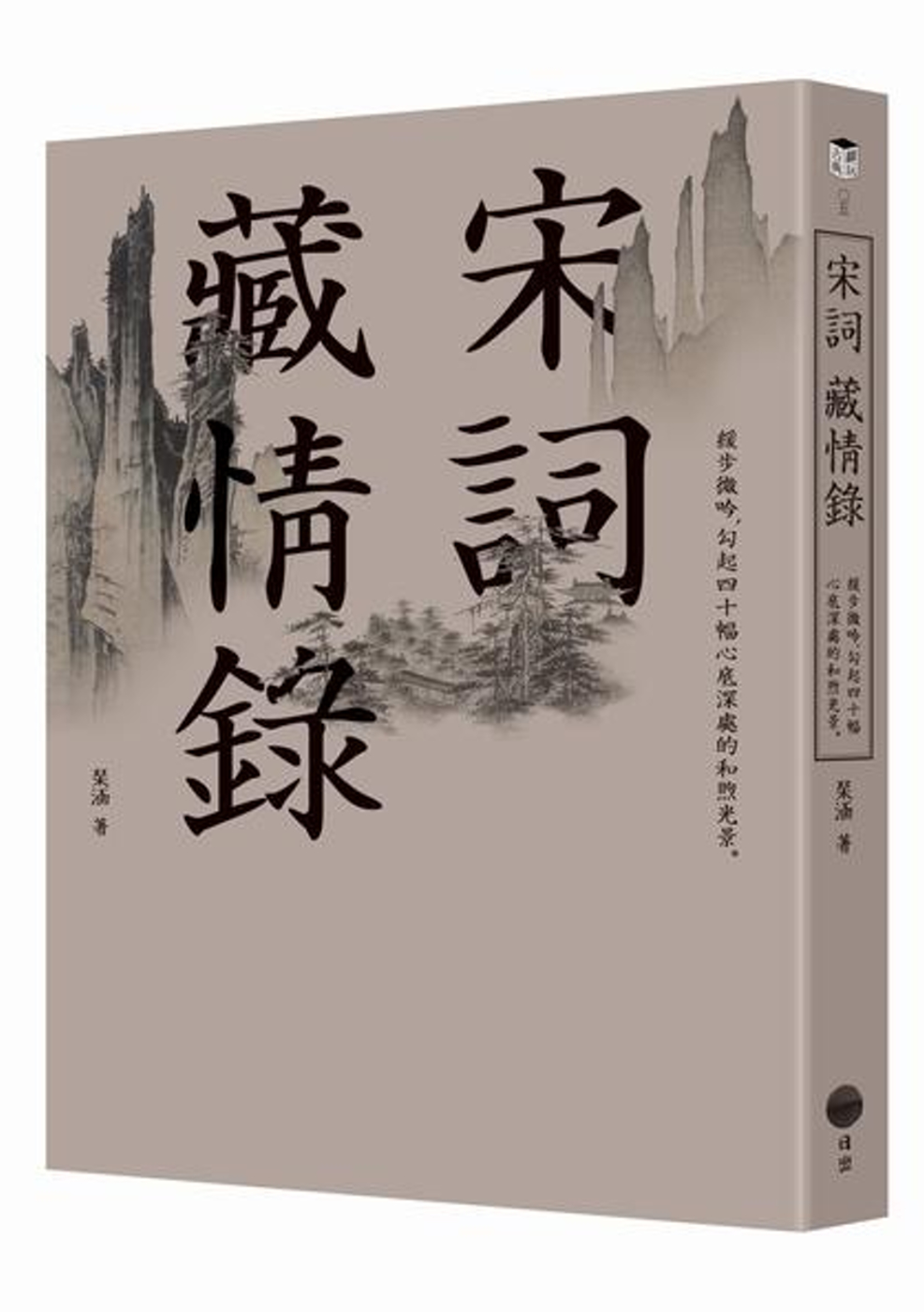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