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間一切事物有用沒用,大抵人類說了算。
植物通常有用,只是有用到最後形同沒用,例如路旁的行道樹。
既然殊途同歸,
不如一起閱讀植物(和我們)如何沒用——
搬進新家不到一個月,新室友也跟著搬進客房。為了室友進駐哪個空間妥當,我可算計了好一段時間。起初我盤算讓他待客廳就好,一大片透光窗戶旁的角落,夾在窗外的山景和我的工作桌之間。雖然空間不大,但視野極佳——想像日光和微風從窗外斜斜映射,室友的纖細身姿便在我眼前影影綽綽、款擺搖蕩……我忍不住吞了一口口水。
可惜算盤打太錯。這面迎東北的窗,除了夏天透早六、七點有極偏的曙光,就沒有任何光照效果了。即使有風,也只能享受半套。這麼一來,室友的美根本無從展現,偏偏「美」是我需要他當室友的唯一理由。
看來只有下午三、四點會西曬的客房容得下室友了。雖然也想過讓他和我共享閨房,但無論日照風吹濕度,我房間都不夠理想……終於安排底定的那天午後,從花市迎回新室友,目睹他在客房窗邊微微仰著臉,迎接三點半第一道西曬光,細長葉片似動非動、在牆上翻映層層疊疊的光影,我靠在他的影子中閉上眼:是了,這就是我一見鍾情的瞬間。心愛的黃椰子。
在我墜入情網之前,黃椰子在我眼中根本常見到視如不見。去哪個辦公大樓開會,他就待在電梯旁或茶水間,診所轉角或銀行入口也總有一個他站在白盆裡垂頭默默。就是,椰子嘛,台灣到處都有,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一點都不稀奇,直到我遇見台北市立美術館地下中庭的那一棵。

Photo by Matthew Cabret on Unsplash
那是一個集體創作計畫。在北美館閉館整修期間,一群劇場創作者和北美館不直接經手藝術的工作者們一起做一個作品。我合作的對象是總務組負責植栽維護的Y。我還記得,當Y第一次帶我走進北美館地下中庭,那個我以往完全忽略的空間,她如何興高采烈地和我介紹裡頭植物:福木、竹、蘭嶼羅漢松(以上種在這裡都不怎麼合適,她打算申請換一批適地耐陰的景觀植物)、波士頓蕨、電信蘭、黃椰子……
站在兩公尺高的黃椰子下,Y要我抬頭看,上方偶然射入的日光穿過葉束,在我們臉上投出細緻的光影。我閉起眼睛,依稀看見綠色悠光,手指一樣對著我的臉來回輕輕拂動。那是我變成老祖母後也會記得和孫女轉述的瞬間。
通常我們學習辨識植物的過程是這樣:你去到一個地方,見到一株植物,接著你設法弄到他的名字,然後上網查資料。這跟墜入情網很像,你遇見一個人、感覺非常強烈、打聽對方是誰、然後盡可能情蒐他的一切。不過,關於黃椰子,或許該說所有的植物,第一階段的蒐索總是難以令我滿意。
「散葉葵,又名黃椰子,學名Dypsis lutescens。棕櫚科馬島棕屬下的一個種。生長高度可達6至12米……為叢生灌木,莖有分節,葉片聚生於支幹頂端。羽狀複葉長約2至3米…… 花長於葉鞘底下,為圓椎花序……花為黃色,細小,旋生於小穗軸上,雌雄異花,有3片花瓣及3片萼片,雄蕊6個……果實外表光滑,橙黃色,乾枯則呈黑紫色……」
就像一個老實偵探日夜跟蹤後回報的資料,對方朝九晚五出門必先踏左腳吃飯把肉留最後,但比起這些,我更想知道:他從哪裡來?他想去哪裡?他不為人知的祕密為何隱藏?他在遇到我之前,曾經歷哪些波濤洶湧的遭遇?是,是,我知道,把植物擬人化是科學求知真理的大忌,但,和一棵讓我crush的黃椰子建立關係,獲取他客觀表相外的其他故事經驗,成了栽種他、和他日夜相處以外的迫切必須。
所以我到植物園去。那裡有我所知最多的棕櫚科植物,不只遍布整個植物園,甚至自成一區:黃椰子、大王椰子、亞歷山大椰子、酒瓶椰子、棍棒椰子、孔雀椰子、岩海棗、銀海棗、羅比親王海棗、蒲葵……這是一群移民至此超過百年的棕櫚大族,並且每棵樹無論來時是一粒種子或一株小苗,通通登記在案。他們的來歷,被這個以研究植物為目標的機構記錄地清清楚楚。
「黃椰子是在何時引入台灣呢?雖然記錄顯示1898年初次引入,1905年自新加坡又引入,但真正的年代很難確認……1915年《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林業試驗場植物目錄》出現Areca sp.不明的椰子類植物,推測可能是黃椰子栽種於臺北苗圃的正式記錄,或許較為可信的引入年代,應是1910-1915年之間……」
結果,植物學者李瑞宗在《沉默的花樹:臺灣的外來景觀植物》考察到的黃椰子移民紀錄,仍是蒙昧一團的不確定。相較於孔雀椰子和羅比親王海棗都是1922年由當時主管植物園的金平亮三從南洋引入、酒瓶椰子在1904年從夏威夷引入後先落腳於恆春的林業試驗支所,還有其他不計其數來自熱帶的豆科與棕櫚科植物,卻都在初抵台灣時留下他們的移動與來歷,黃椰子的登陸台灣,簡直就像《鐵達尼號》裡李奧納多扮演的流浪畫師,差別在於:黃椰子最後安然上岸,且在1970年代前後被園藝市場哄抬成明星,繁殖了一代代大樓門口和電梯旁的景觀植栽。
黃椰子起源何處?「棕櫚科馬屬」揭露答案,他是馬達加斯加的原生種植物。據說,島嶼是物種多樣性最高的地方,也就是,一個島比一片大陸更能孕育多元的物種、構成更複雜的生態。但是,正當黃椰子在我們的辦公大樓和庭園造景排排站,賜予我們細緻優雅的美麗時,馬達加斯加島上的野生黃椰子,數量稀少到已瀕臨危險。
原因可以從樹形同樣不高、原生地同為島嶼、瀕危程度是「極危險」的酒瓶椰子(Hyophorbe lagenicaulis)身上發掘。英國邱園(Kew Gardens)的園藝師卡洛斯.馬格達勒納(Carlos Magdalena),長期參與搶救模里西斯島瀕危植物的任務,他在《植物彌賽亞》中提到,酒瓶椰子曾遍布模里西斯,但目前它們的分佈範圍極度受限,野生酒瓶椰子一度剩下不到十株。為什麼呢?
李瑞宗《沉默的花樹》提供我們另一塊拼圖。70年代,一名台灣的園藝商人張碁祥發現酒瓶椰子有非常大的外銷需求,想方設法聯繫上模里西斯的僑民協助,最後「私下向植物園掃地的工友購買。因為種子實在很多,每天都可以掃一堆,官方管道不能私下出售,就走另途,亦可絕處逢生。掃地的工友還以為這些種子要拿去做中藥,不知別有他用。」
酒瓶椰子在台灣園藝界一度價格飆升到有專門偷取的竊賊集團。事業一度瀕危的張碁祥,靠酒瓶椰子翻身,多年後受訪,他說,「相隔地球那麼遠的這批酒瓶椰子,我有說不出的感謝。」不過,這批因過度摘採幾乎滅絕的椰子,大概不太可能接收或感應到他的謝意。
所以,在得知我的新室友其實有著相仿身世後,我該怎麼看待我們的關係呢?我對他的慾望,促成遙遠島嶼上人們的摘取和大量繁殖。當人類繁殖的馴化品種在全球蔓延,野生族群則瀕臨滅絕,它們身上隱藏的某些獨一無二的遺傳因子,也將在地球上永遠失落。我不確定這個失落將對地球帶來何種損失,但我也無法解釋,為什麼得知有族群滅絕會讓我的心微微抽痛。
在我思索著這一切艱難的生命倫理問題時,我的貓跳上高台,端詳了我婀娜美麗的室友好一會後,往他身上狠狠咬下一大口葉片。
NEW!! 專欄【沒用的植物】每月更新。
01_首先,你要有個沒用的陽台
02_植物仙姑養成術
03_植物仙姑大對決
延伸閱讀



![沉默的花樹:台灣的外來景觀植物[軟精裝]](https://www.books.com.tw/img/001/056/62/001056623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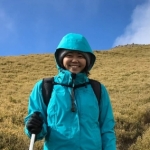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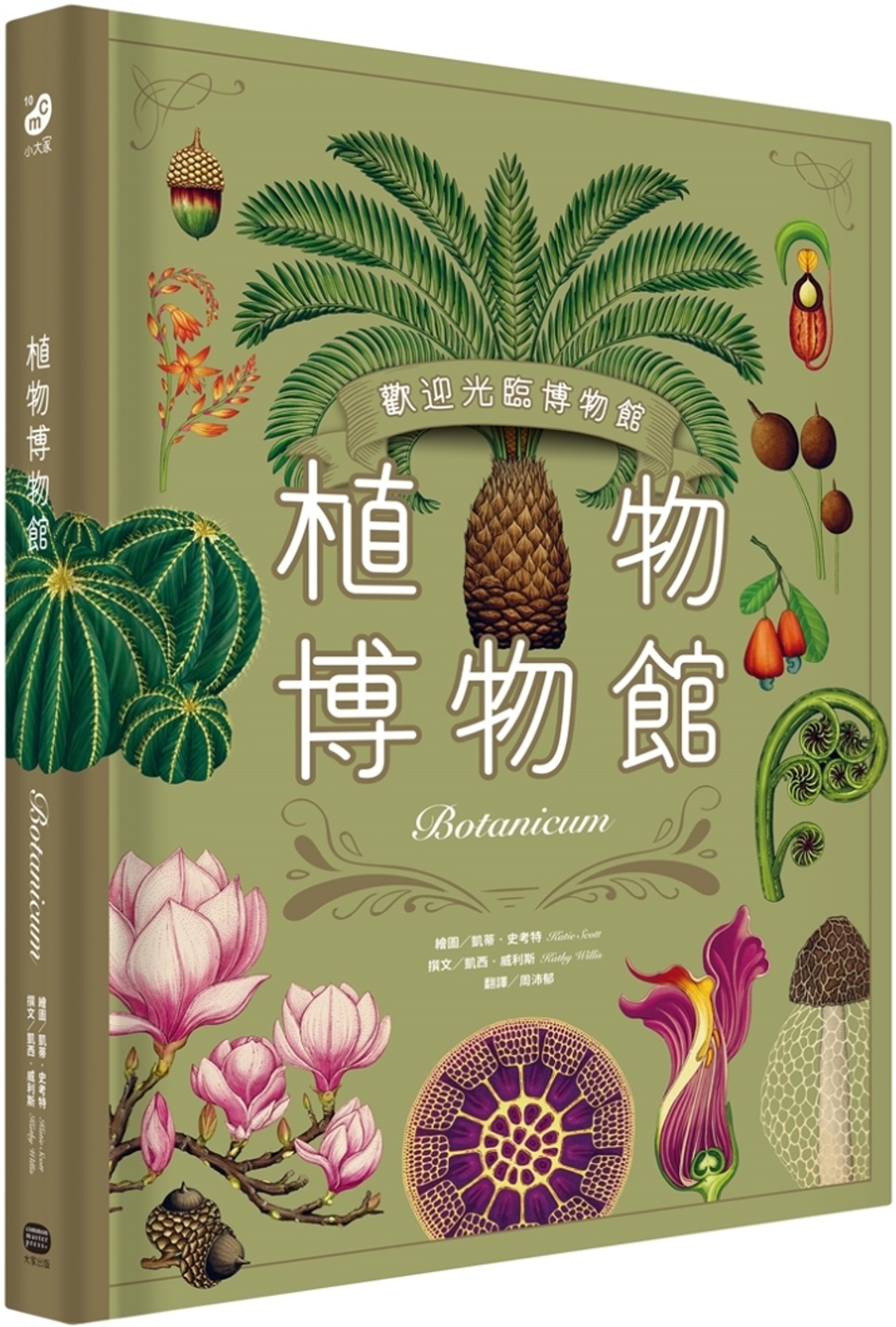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