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默思.奧茲是我非常鍾愛的小說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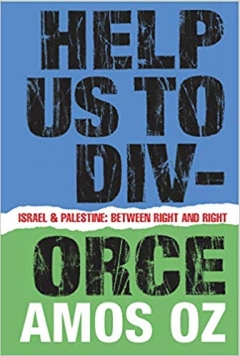 《助我們離婚!》書影
《助我們離婚!》書影
陳柏言在《地下室的黑豹》作品解析中,曾將呂赫若的〈玉蘭花〉與其中段落加以對照,讓我大有同感,稱快不已。不過,在認識奧茲的文學作品之前,我最早讀到的是他的政論小書《助我們離婚!》(2004),這本書的副標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現在的兩個國家」。身為以色列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奧茲卻挺身支持巴勒斯坦的國家主權。他認為,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都是歐洲殖民主義的受害者,兩方不是善惡之爭,而是「兩者都對」。奧茲不是唯一有此勇氣者,但他的立場鮮明,言辭犀利,對某些歐洲盛行的廉價表態,他的批判也很尖銳。他的出席,往往意味著巴勒斯坦的權益在場。這是我們在認識他是「以色列國寶作家」時,也必須了解他的「以色列立場」是多麼地非典型。
他的政治散文扼要明快,令我相當意外,說理文字也可具有如斯美感,而一開始讀他的小說,我就感到相見恨晚──我十分同意《朋友之間》推薦序作者葉佳怡對他短篇小說造詣的喜愛,以今年為例,我大約讀了十來本的中外短篇小說集,在偶然的瞬間,我試圖將它們放在一起思考,不禁感嘆道:奧茲真可以說是個短篇小說之王啊。

艾默思.奧茲(Amos Oz),1939年生於耶路撒冷(當時以色列尚未建國),出身書香之家,父母皆有大學學位,通曉多國語言,受歐洲文化薰陶甚深。(圖片來源 / wiki)
我們有許多不同理由來讀《朋友之間》:對短篇小說的技巧有興趣、是奧茲的忠實讀者,此外,還有一個很大的誘因:那就是書中的友情主題與大名鼎鼎的基布茲。
任何曾經翻開大學程度社會學的讀者,大概都聽過基布茲。最有印象的,恐怕就是它在育兒與社會組織上的特殊性,在討論親屬關係與性吸引力的相關研究中,它也經常被引用。而如今有一本文學大師為基布茲作畫的小說,相信會令不少人文學科的研究者,雙眼一亮。
 以色列的基布茲(Kibbutz)公社,過去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現在則從事工業和高科技產業。(圖片來源 / wiki)
以色列的基布茲(Kibbutz)公社,過去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現在則從事工業和高科技產業。(圖片來源 / wiki)
友情與基布茲息息相關,因為公社或說任何類公社的組成,都帶有弱化親緣、尋求平等以及堅守原則等人造色彩──一方面,這樣的小社會對抗批判的是眾人較熟悉的主流社會,另方面,這類實驗與實踐的存在,總是探問人在組織與團結這個向度上的創造力,可以走得多遠、會有什麼困難。若問是什麼可以連結這樣的社群,友愛就是無法忽略的理想與經驗。
《納尼亞傳奇》作者C.S.Lewis對友愛做過精闢的分析:「友情是各種愛中最『不自然』的一種:它最不本能、最不動物性……」;但朋友群也有可能犯與騎士階級類似的毛病,「在一群真正的好朋友之間……每個人都會覺得其他朋友比自己優秀……問題是……對朋友的謙卑很容易就會引申出對外人的驕傲。」以政治性而言,「擁有真正朋友的人都較難被駕馭或支配:好的統治者會發現他們很難被糾正,壞的統治者會發現他們很難被腐化。」友情並不簡單──它不僅僅是同伴之誼。奧茲選擇以「友情」主題切入基布茲,可以說是匠心獨具。
〈挪威國王〉中的茲維是所有死者的好朋友──他不斷對生者報死訊,從安哥拉大屠殺到挪威國王之死都使他絮叨。茲維來自波蘭,最惡名昭彰的集中營奧許維茲就是在波蘭,而非德國。他像極了惡意反猶的人會醜化的猶太人之影:總是拿大屠殺對人喋喋不休。但在基布茲,他的強迫症可是拿猶太人開刀啊!而且他唯一沒提的,就是死去的猶太人。因為在基布茲,誰會不知道呢?猶太人介於可說與不可說的沉重背景,就在這令人啼笑皆非的偏執易感開場中,揭開序幕。
〈兩個女人〉中,芭瑞從奧絲娜身邊帶走了鮑茲,但又想爭取奧絲娜的友情,令我們不禁疑問,如果芭瑞與鮑茲的情愛結合那麼重要,芭瑞遂其所願之後,難以療癒的孤獨,究竟又意謂什麼?〈朋友之間〉中,大衛.達甘會上場。他50多歲,是出現最多次的一個人物,尖酸的羅尼會說:「……基布茲的人若是需要妻子,就站在大衛.達甘家的台階下等一陣子,便會有女人像煙蒂那樣被扔出來。」小說裡我們並沒有看到大衛以特別下流或犯法的方式「換女人」,看來他就是「誘惑有方、拋棄有術」。除了拿來說笑,基布茲裡的人,覺得他們政治權威的「快情慾」(借用「快時尚」這個表達)有問題,但也說不出問題在哪;結果是,納胡的女兒和大衛同居了──眾人都覺得,這是大衛同時欺負了納胡和他的女兒。
大衛侃侃而談他和納胡的友情,而納胡找不到清楚的理由把女兒帶回──納胡並非否認女兒的愛情,但有什麼在語言之外的東西,使他還是嘗試反對他們──儘管這使他很落下風。我以為性規範其實是這個故事的障眼法,真正被批評也被贖出的是納胡。不是因為他保護女兒的想法太落伍,而是他終於發現友情的夢幻是如何窄化了他的認知。女兒告訴他,自己在大衛身邊過得很好時,納胡終於飆出了一句「這怎麼可能?」
與其說是不相信女兒,不如說是道出了他對「朋友」大衛的真實評價,而這才使得納胡本人更加真實不虛──納胡沒有外化他心中的暴力,但我們可以感受到這話對他本人來說多麼有殺傷力,不是源於他不能帶回女兒,而是抖落幻覺後的空虛失重:因為,對朋友的幻覺,就是我們對自己的幻覺。
〈父親〉和〈戴爾阿吉隆〉分別是新來者莫沙伊與長在者約塔姆的故事。大衛也都扮演了關鍵角色。在〈父親〉中,他忠告莫沙伊不可讓父親對他的影響大過基布茲,茲維問莫沙伊城裡有什麼是基布茲沒有的?莫沙伊答道,「城裡有怪人」──顯示莫沙伊分辨出基布茲的安穩,仍是以犧牲某種多樣性為代價。
〈戴爾阿吉隆〉中,約塔姆在義大利的舅舅,也是基布茲的叛逃者,要出資讓約塔姆去義大利上大學,約塔姆的母親積極運作,希望眾人通過決議放行,這一篇對於基布茲的經濟與教育原則有很細膩的描述,也會使我們大開眼界。然而重要的轉折是,約塔姆反對母親,因為他對基布茲有深厚的認同,但同時,他也對大衛說出,響應對猶太人的號召已經讓他窒息。這裡我們就看到基布茲的文化積累、危機以及大衛的手腕,他對年輕人特有的理解與寬容。不過,這是因為大衛通情達理?還是基布茲有青年流失的危機?也許兩者皆是。奧茲洗練的筆法,既描繪出大衛攻心為上的人性感召,還拋出一個讓我們想像「大衛年輕時代」的殘影:對啊,這個斬釘截鐵的人也不是生來就為建基布茲的,他一定也有過掙扎與徬徨。
〈在夜晚〉與〈世界語〉兩篇,在另一個向度上互有呼應:經常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妮娜,被現任書記約夫視為最可靠的政治接班人,這種惺惺相惜不太外顯,或許是知己最高尚的型態;鞋匠馬丁對物質的輕簡苦行與對思考的熱忱,強烈地令人憶起史賓諾莎──他和奧絲娜之間的友情,是小說中非常光輝的一頁。他們生在基布茲,但卻是仍保有某種距離的自主邊緣者或叛逆者──基布茲也得歸功於他們的自發性或離心性,而不是只有占住權威的老師大衛。在這些動人故事中,奧茲也勾勒基布茲中,壓抑女性與某些男人去性化與幼齡化的現象。〈小男孩〉中被其他小孩霸凌的歐弟,粉碎了該地純真無辜的形象,而父親羅尼失控毆打的不是霸凌者,而是某個溫和小孩,更暴露了基布茲人對於自衛,深藏著惡夢似的恐懼。誰是小男孩?大概不只是歐弟。
邪教、派系、政治共同體、以公社名不以公社名的自發性組織、甚至我們出生的家庭,各自運作的方式,偶爾驚人地相近又相似,其間差異,常常「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朋友之間》走進的,絕不單單只是基布茲這個小宇宙;讓我們能從另一個星球看我們的所在,我們的所在,真的那麼理所當然嗎?這,更是《朋友之間》帶來的珍貴反思視野。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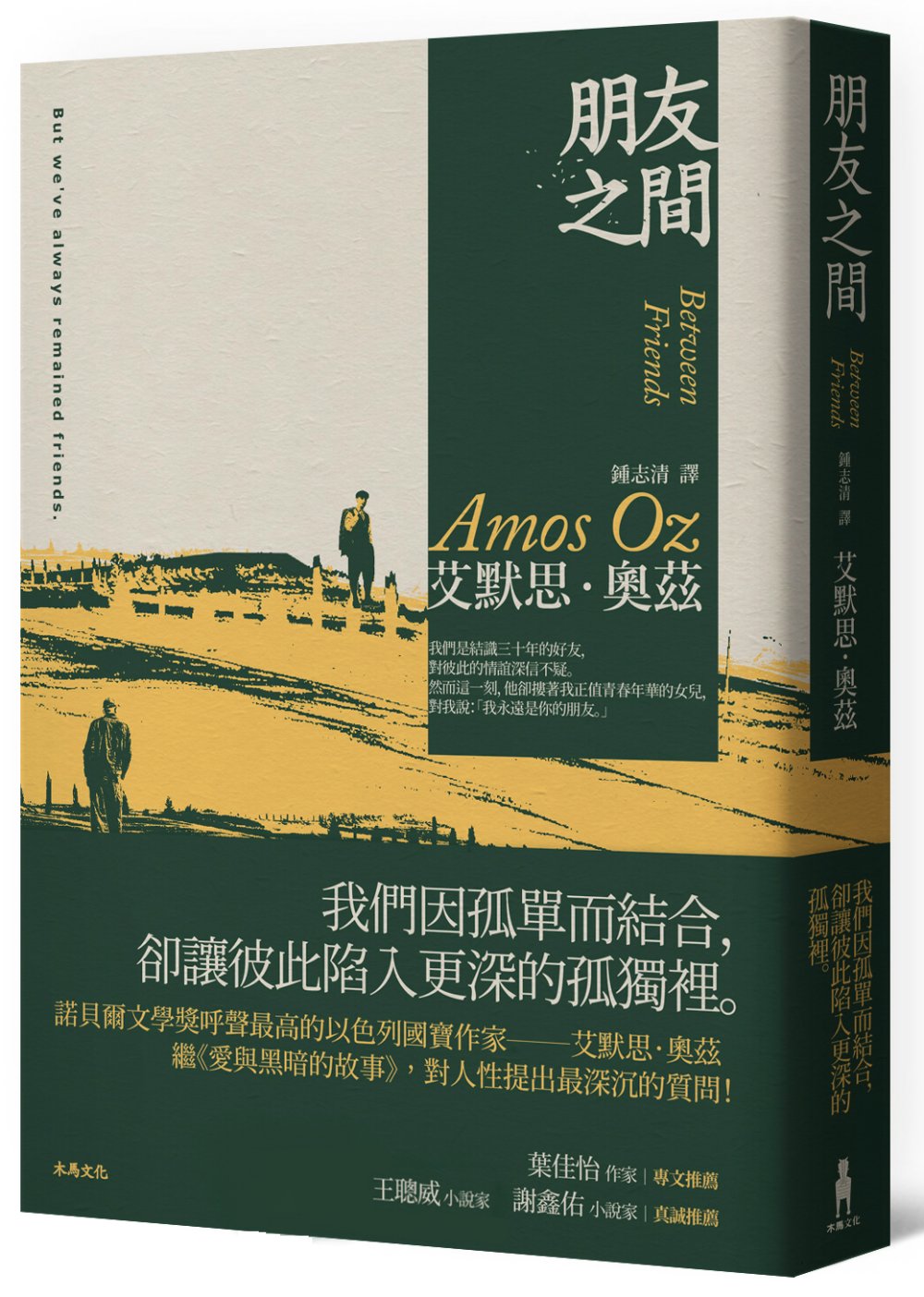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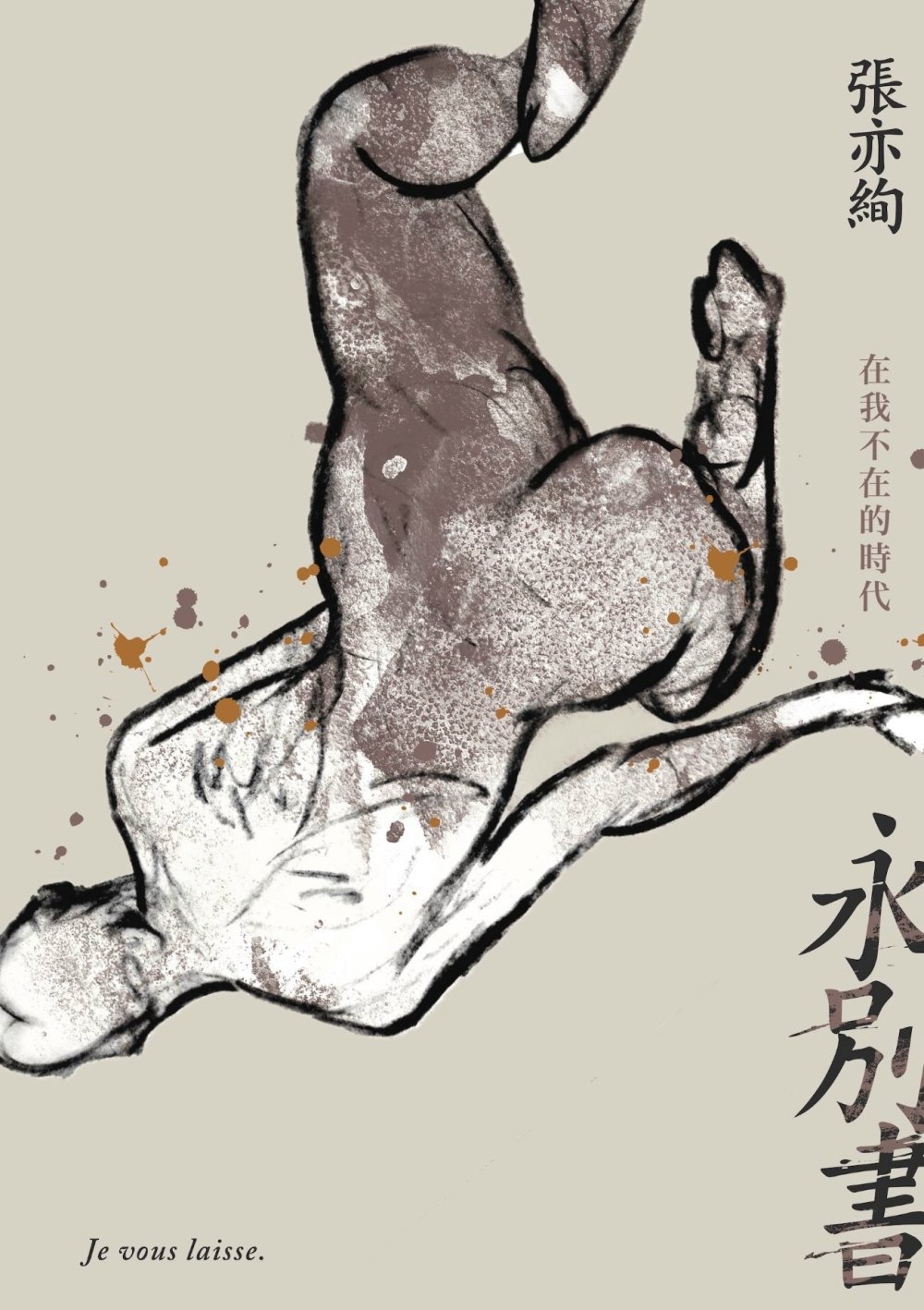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