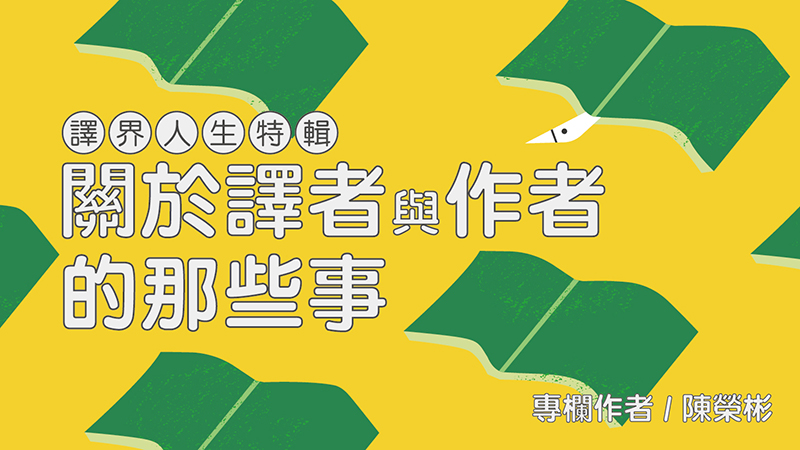
從凌叔華到王禎和的自譯
回顧現代華語文學的歷史,能夠將自己的作品翻譯成英文的作家,真的有如鳳毛麟角。比較知名的例子包括凌叔華在英國青年Julian Bell(他的阿姨是大名鼎鼎的小說家Virginia Woolf)的幫助下,把自己的小說《無聊》等作品英譯後刊登在專門英譯推介中國文藝作品的上海雜誌Tien Hsia Monthly(取「天下為公」之義,贊助者為孫文之子孫科),還有蕭乾就讀燕京大學新聞系期間就曾參與翻譯系上老師Edgar Snow主編的現代中國小說選集Living China(裡面收錄一篇他自己的作品〈皈依〉),就此踏上往後幾十年的自譯創作旅程。更有名且有趣的例子是張愛玲,她也是自己《赤地之戀》、《秧歌》、《金鎖記》等作品的譯者,而且她曾說過:「要提高英文和中文的寫作能力,有一個很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一篇習作由中文譯成英文,再由英文譯成中文。這樣反覆多次,儘量避免重複的詞句。如果你常做這種練習,一定能使你的中文英文都有很大的進步。」
 凌叔華是最早翻譯自己作品的現代華語小說家之一,她的合譯者Julian Bell有一位大名鼎鼎的阿姨,即英國小說家Virginia Woolf。
凌叔華是最早翻譯自己作品的現代華語小說家之一,她的合譯者Julian Bell有一位大名鼎鼎的阿姨,即英國小說家Virginia Woolf。
 張愛玲翻譯了自己的小說作品《秧歌》等。但她那獨特的張腔很難用英文表現出來。
張愛玲翻譯了自己的小說作品《秧歌》等。但她那獨特的張腔很難用英文表現出來。
 張愛玲的The Fall of the Pagoda與The Book of Change兩本小說並無自譯的中文版,譯本係由臺灣譯者趙丕慧操刀,讀來頗有張腔。
張愛玲的The Fall of the Pagoda與The Book of Change兩本小說並無自譯的中文版,譯本係由臺灣譯者趙丕慧操刀,讀來頗有張腔。
換言之,在張愛玲看來,翻譯與創作是不可分的,翻譯甚至是精進創作的方法。她的自譯也與人生際遇息息相關:1952年離開中國後她必須自謀生路,往後十幾年間為了在美國文壇覓得一席之地而開始成為中英雙語作家,操刀自己作品的中譯英或英譯中,而且像The Fall of the Pagoda 與The Book of Change 等作品甚至只有英文版(後來才由臺灣知名譯者趙丕慧譯為《雷峰塔》與《易經》)。
但她獨特的「張腔」移植到英文環境之後失去了原有的活力與情調,這是個不爭的事實。所以劉紹銘教授在評論張愛玲自譯《金鎖記》時才會說她的英文是“bookish English”,是自己苦修來的,因此才會把男人「拚命地在外頭玩」翻譯成“play so hard outside”(讀起來比較像「打球打得(或玩遊戲玩得)很認真」),而不是“fool around so much outside”(意思是「在外頭卯起來鬼混」)。
另外一個例子是知名小說家王禎和自譯短篇小說〈嫁妝一牛車〉。他自臺大外文系期間就開始持續創作不輟,小說向來以夾雜國語、台語、英語、日語著稱,且充滿各種滑稽、幽默元素,就算是描寫台灣社會底層小人物的悲慘人生,讀者讀來往往是笑中帶淚。但有些幽默元素若轉換成另一種語言,往往就失去了原有的笑點。舉例說來,〈嫁妝一牛車〉裡面形容女主角放屁「平平仄仄,仄平平得不可收拾」,把「平仄」這兩個嚴肅古雅的字跟放屁這個不雅的身體現象連結在一起,形成某種反差造成的幽默感,令人會心一笑。不過等到他把這句話自譯成英文後變成“her stomach started to cannon one after another, consistently and rhythmically”,則是可以回譯為「她的肚子開始放炮,一發接一發,呈現一種持續不斷的韻律感」。雖然用「放炮」來暗指放屁也挺幽默,但“consistently and rhythmically”完全失去了原文中「平仄」二字的神韻。
譯者白先勇
由張愛玲、王禎和的例子看來,作家就算英文程度再怎樣高深,畢竟並非英語母語人士,再加上帶有作家獨特標記的中文風格,在翻譯成英文後不見得能夠完美轉換,作家翻譯自己的作品往往不是點指成金的保證。就連白先勇這種長期在美國大學教書(UC Santa Barbara)的作家,英語已經成為他較常用的語言,但根據他在某次訪談中透露,短篇小說“Hong Kong 1960”是他唯一一篇用英文創作的作品(後來也由他自己譯成〈香港:一九六〇〉,於1964年刊登在《現代文學》上)。另外,他還曾把自己的短篇小說〈謫仙記〉譯成“Li Tung: A Chinese Girl in New York”,收錄在短篇小說集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中國二十世紀短篇小說》,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但翻譯後曾由該書編者夏志清修改過。白先勇甚至曾形容用英文創作「就好像左手寫字」,因為英文畢竟並非他的母語,用於創作,有說不出的彆扭。但透過稍後我將舉出來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他的作品之所以很難翻譯,跟張愛玲、王禎和一樣,也是因為風格強烈。小說中他使用的是某種融合古典文學與中國各地方言的特別文字,而且字裡行間往往含藏各種文化、歷史元素,這對任何譯者都是一大挑戰。
 白先勇的《臺北人》、《孽子》與《紐約客》等代表作都受到中國古典文學與各地方言的雙重影響,對想要翻譯這些作品的人來講都是一大挑戰。
白先勇的《臺北人》、《孽子》與《紐約客》等代表作都受到中國古典文學與各地方言的雙重影響,對想要翻譯這些作品的人來講都是一大挑戰。
戰力爆表的隊友:喬志高與Patia Yasin
但白先勇畢竟還是把自己的短篇小說經典《臺北人》翻譯成英文,但翻譯與出版過程頗經一番波折,要先從白先勇的臺大外文系學長劉紹銘教授說起。劉教授任教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但因為他是印第安納大學比較文學博士,與該校關係向來密切,後來印大出版社於1970年代末期籌辦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叢書,便是由他與羅郁正(專長為古典中國文學)與李歐梵(李為白先勇大學同學)兩位教授擔任編輯委員,其中劉、李兩人在臺大外文系期間與白先勇共同創辦《現代文學》雜誌,是相交數十年的好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臺北人》就被翻譯成Wandering in a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 Tales of Taipei Characters(書名採用其中一篇故事〈遊園驚夢〉),於1982年出版,跟陳若曦的《尹縣長》、黃春明的短篇小說集《溺死一隻老貓》、蕭紅的《生死場》與《呼蘭河傳》,還有錢鍾書的《圍城》同樣入選該叢書中,成為現代華語文學中具有相當代表性的作品。後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在重新出版《臺北人》中英對照本時,則是把英文書名改成比較簡單的Taipei People。
 《臺北人》英譯本能由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他臺大外文系的學長劉紹銘教授(前排中一)與同學李歐梵教授(後排中)可說功不可沒,他們三人也都是《現代文學》雜誌的編委會成員。
《臺北人》英譯本能由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他臺大外文系的學長劉紹銘教授(前排中一)與同學李歐梵教授(後排中)可說功不可沒,他們三人也都是《現代文學》雜誌的編委會成員。
《臺北人》的英譯計畫其實從1970年代中期就已啟動,雖然白先勇找到了兩位戰力爆表的隊友,但還是磨了五年才完工。他的「翻譯團隊」有負責潤稿的英文編輯喬志高(原名高克毅),與合譯者Patia Yasin(漢名葉佩霞,原姓Rosenberg,是美國重量級藝評家Harold Rosenberg之女)。但凡熟悉F. Scott Fitzgerald經典小說The Great Gatsby 的讀者,對於喬志高這個名字自然不陌生,因為他就是最有名中譯本《大亨小傳》的譯者,中英文造詣即便連白先勇也佩服不已。
至於Patia Yasin則是白先勇於UC Santa Barbara的同事,有衛斯理安大學的民族音樂學博士學位,精通英、法、義大利文(譯完《臺北人》後又去學了波斯文、土耳其文)。喬志高的翻譯、編輯經驗豐富,也是美國俗語、成語專家,而Patia Yasin則是英語母語人士,且熟悉樂理(《臺北人》裡有不少崑曲等中國音樂元素)。白先勇曾說,要不是有這兩位隊友,他也不敢接下英譯自己小說的艱難任務。
 與白先勇合譯《臺北人》的Patia Yasin是民族音樂學博士,精通義、法、波斯、土耳其文,是多才多藝的譯者,可惜已於2017年病逝,享壽74歲。
與白先勇合譯《臺北人》的Patia Yasin是民族音樂學博士,精通義、法、波斯、土耳其文,是多才多藝的譯者,可惜已於2017年病逝,享壽74歲。
 喬志高的翻譯作品《大亨小傳》堪稱The Great Gatsby所有譯本中成就最高者。
喬志高的翻譯作品《大亨小傳》堪稱The Great Gatsby所有譯本中成就最高者。
「歸化」與「異化」之間
據白、葉兩位合譯者所言,他們在翻譯時總想找出「le mot juste」(最恰當的字眼),而不只是把中文直譯成英文。例如〈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女主角原名金兆麗,如果只是音譯就無法把她的個性凸顯出來,於是喬志高幫忙想出Jolie 這個名字,它在法文裡有活潑歡快的含意,真是再恰當不過了。同樣的,金大班任職的臺北舞廳「夜巴黎」則是被譯為Nuits de Paris,而非直譯成Nights in Paris,不但與Jolie 這個法文名字前後呼應,對於英文讀者來講也能呈顯出一種異國情調。〈遊園驚夢〉裡女主角錢夫人之妹月月紅,則是在喬志高的建議下譯為Red-red Rose,典出英國詩人伯恩斯(Robert Burns)經典詩句:“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
另外,〈思舊賦〉裡面兩位年邁女僕順恩嫂、羅伯娘講話口氣頗具地方色彩,因此白、葉兩位譯者決定用美國南方方言來翻譯她們講的話,例如把「不中用」譯成“I ain't no use no more”。至於〈梁父吟〉裡面的輓聯對句「出師未捷身先死。 中原父老望旌旗」則是以古英文的句構、用詞翻譯成“That thou shouldst have died ere victory did crown thine expedition!/Still do the homeland fathers and elders all long for the sight of thy banners”,強化了莊嚴肅穆的感覺。有時候白先勇在對話裡面使用的佛教概念,則是會被偷偷轉化成基督宗教的用語,例如「普渡眾生」被改寫成“redeem poor souls”(可以回譯成「救贖可憐的靈魂」),「成了正果」則變成“attain salvation”(意思是「獲得救贖」)。
從翻譯研究的角度看來,雖然這個翻譯團隊為了讓譯文能夠貼近西方讀者的理解而做了很多轉化、改寫,較接近所謂的「歸化」(domestication)翻譯策略,但在希望能傳達某些中國文化、歷史資訊的地方,有時候他們也會選擇用音譯的,像是「副官」、「師娘」、「旗袍」、「大哥」等等稱謂或專有名詞,然後在每一篇譯文最後面附上詳細註解——而這則是保留異國文化、歷史元素的「異化」(foreignization)翻譯策略。《臺北人》英譯本可說是一本介於「歸化」與「異化」之間翻譯名作,經過白先勇與葉、喬兩人精雕細琢,不斷推敲後,將翻譯藝術的成就推向高峰。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分別由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臺北人》英譯本。
分別由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臺北人》英譯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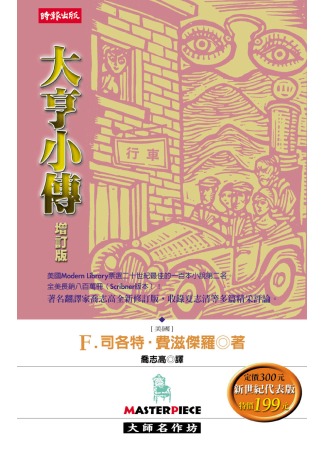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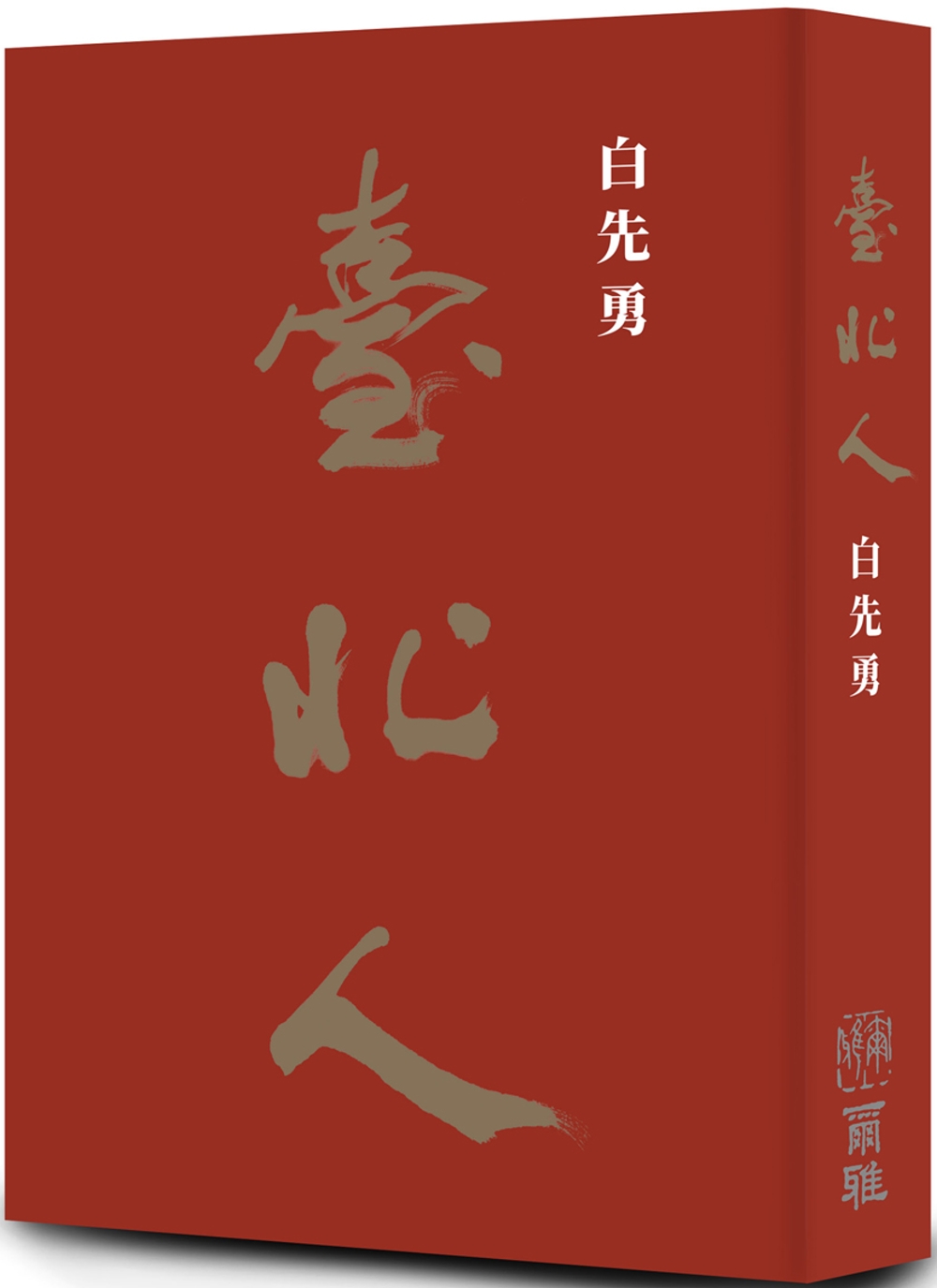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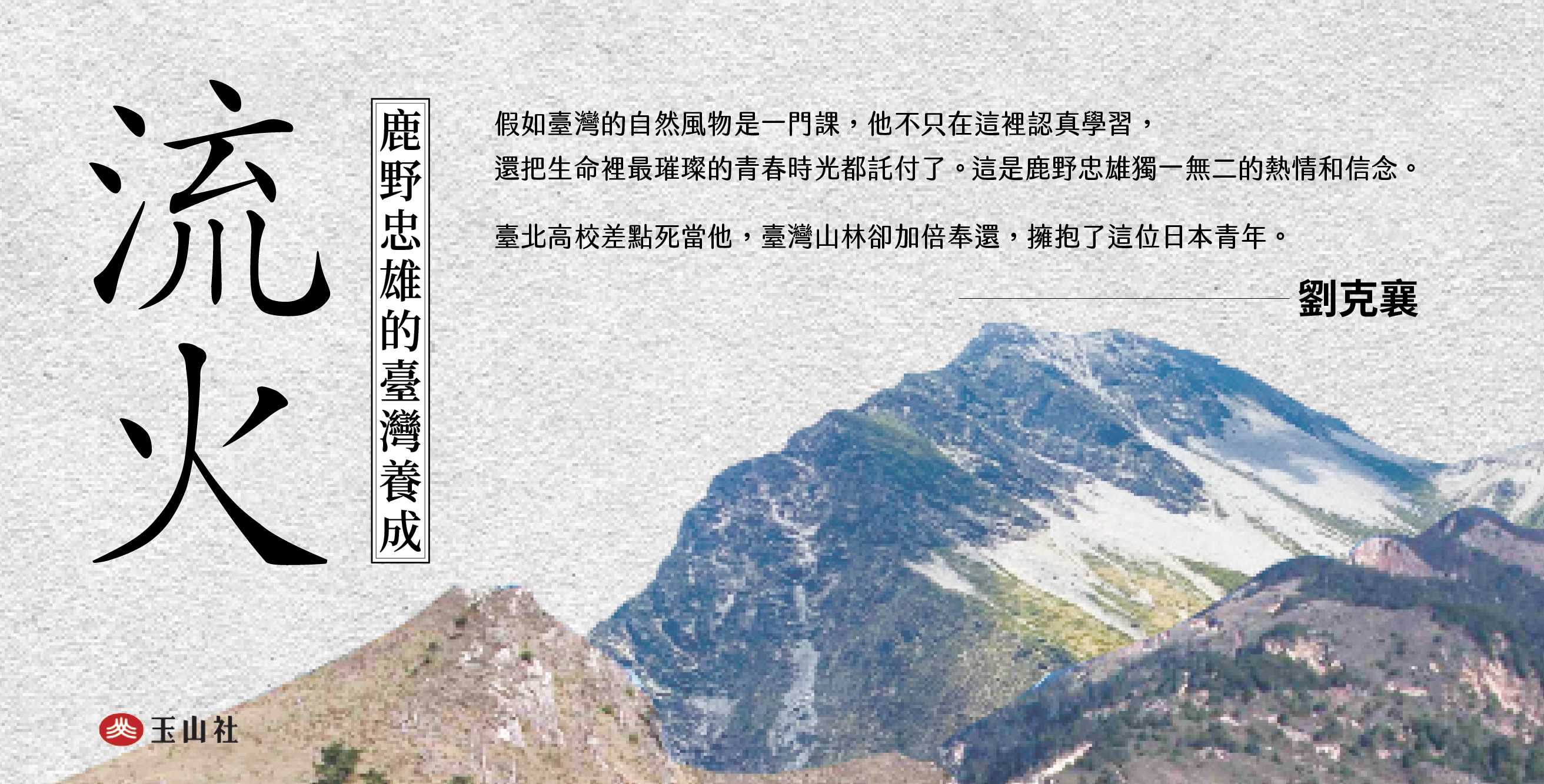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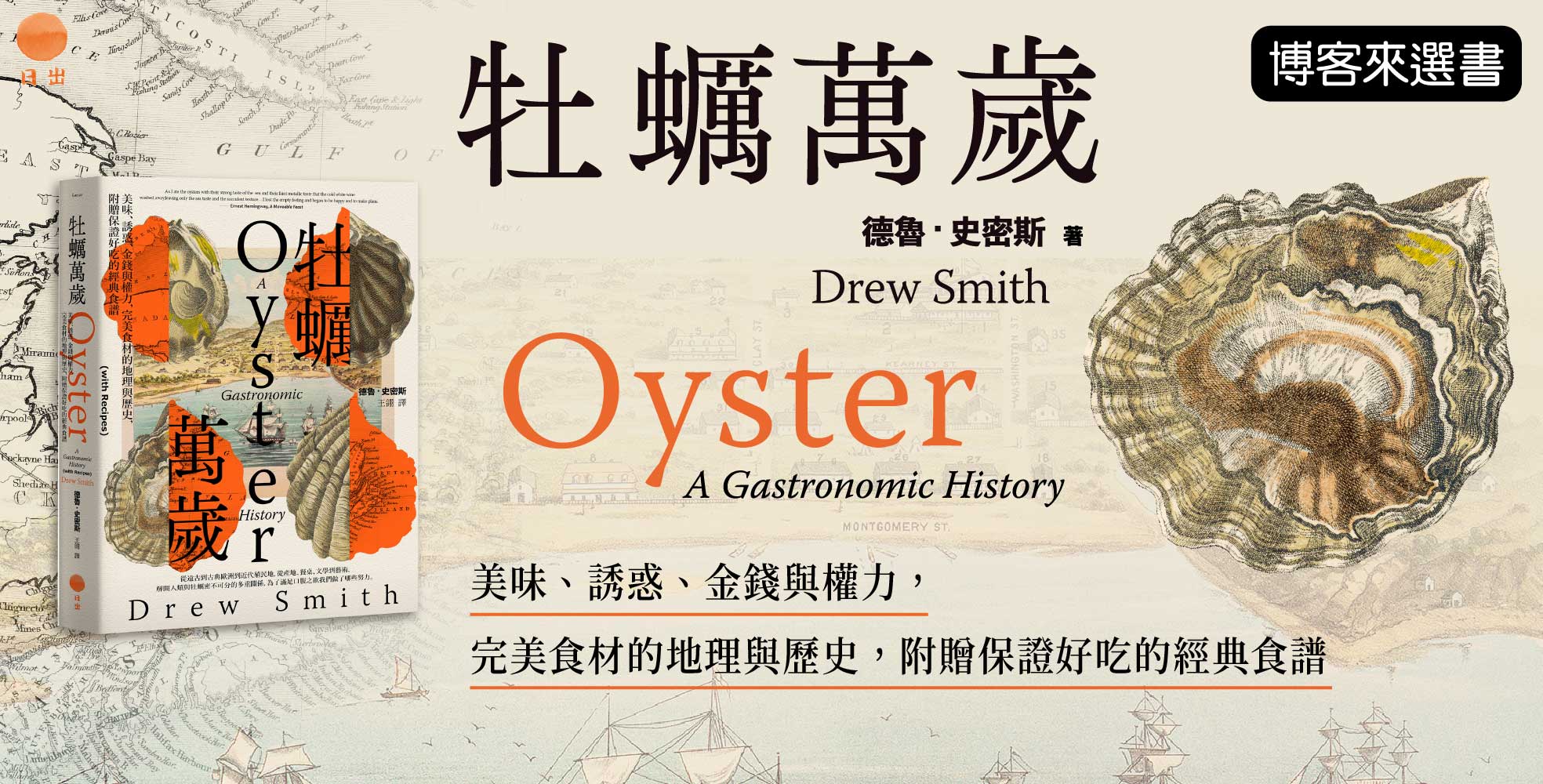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