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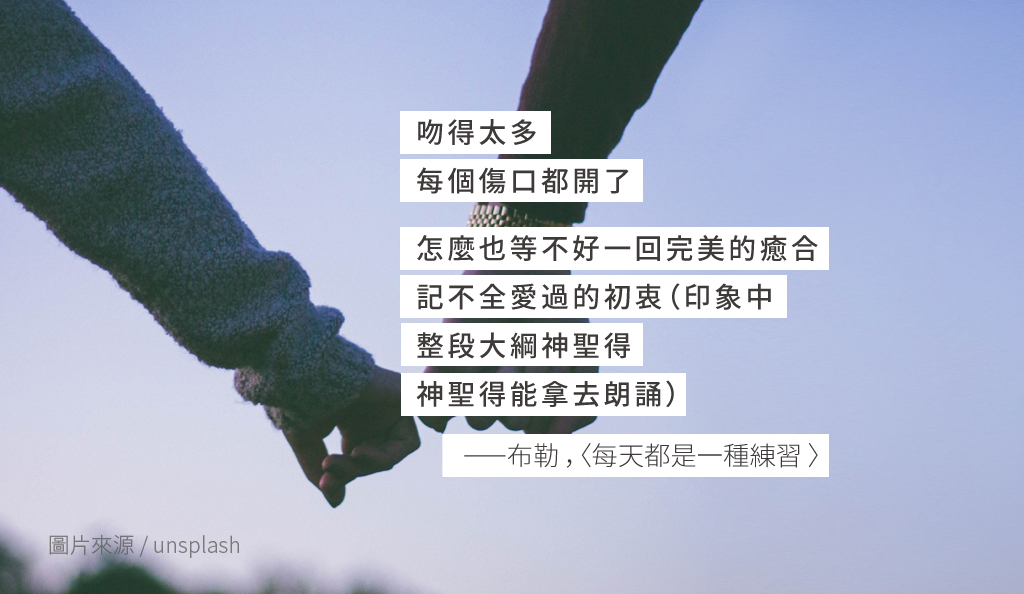
為什麼大家都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性別。
小學的時候好像每個人都很清楚自己喜歡誰,隔壁的王同學,喜歡我們班花,兩人走在路上牽小手,體育課偷偷把名字刻在校園角落的樹上,畫一個情人傘。小學的時候好像沒有人會說王小明和李小明是班對,就算兩個人每天抱抱也一樣,但只要王小明和李美麗座位被排在一起,兩人就會被說「班對」、「親親」。
那種猜測班對的純純之愛好像是某種本能,小時候的愛,似乎總更是懷抱暴力的本能,而正如布勒於〈無愛演化生活〉中所寫:「災難來時總難以預見/那些突如其來的手/愛是直覺/而直覺難免缺乏準確/準確的愛命中不了什麼/而我曾經那麼那麼/只依賴本能生活」,雖然談愛,而我更想指出的是,愛、性別、性向──無一能倖免直覺,而直覺並不總是準確。
曾經我的直覺是世界上只有異性戀,只有男性與女性,我不可能愛上每種性別。但誠如上述,直覺並不總是準確。
現在出櫃似乎更加自然了些,但出櫃都是非異性戀在出的,好像是非異性戀們總會先以為自己是異性戀,而在某一天忽然體悟到自己的不同因此走出衣櫃。但衣櫃究竟是誰建造的,是誰讓我們必須躲進去的呢?為什麼異性戀沒有那個衣櫃?
廁所或者床頭櫃也好啊,為什麼都沒有。為什麼異性戀不用從某個空間走出來?
我很好奇異性戀究竟是什麼時候知道自己是異性戀的。
是在健教課本上嗎?還是看到自己的父母做愛,或者是偷翻到別人的A片,網路上偷偷瀏覽的H漫,或者是對巷的檳榔西施對你拋了媚眼。還是如〈得不到〉中所寫:「每日/每日思念海浪/即使我/一生/都棲息在/海邊」,是某種索求不得,愛妹愛弟愛不到,而體悟到自己是異性戀的?就像是異男忘一樣。究竟異性戀是什麼時候,知道自己就真的是異性戀的?總有些異性戀喜歡說同性戀是後天造成的,那異性戀呢?而布勒在〈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致吾友葉青〉中說:「我的同性戀是天生的,毫無疑問」,那異性戀也是天生的嗎?
最早登陸的走獸,會知道自己從前是屬海的嗎?
這恐怕不是真正的議題吧,究竟是先天後天捏造虛構的,那些都無法抵消所愛非人之痛,所求不得之苦——而在非異性戀族群中,最常出現的恐怖故事,或許就是被迫全裸了。從前學校有過一個向同性告白失敗,且被他告白對象昭告天下的同學,我從未見過他,不知道他究竟是誰,但我記憶中總有某個模糊的輪廓,我總是覺得當時的他一定像是布勒〈霧中風景一〉中所寫那般,那麼孤獨:「不怕。//內心的真實需要一把手電筒/讓不懂得轉彎的光照亮迂迴的/心之暗面/我目光亦步亦趨跟著燒/如此這般,彷彿依舊是直行的路途/就這麼在夜裡蜿蜒開來//兩旁的樹都在暗裡哭了」。
所以,究竟為什麼異性戀不用出櫃,而非異性戀的出櫃,甚至可能時間點都不是自己能夠決定的呢?就像電影《親愛的初戀》中,男主角賽門被同學在網路上公開出櫃(小說中也是一樣的情節)。究竟為什麼是我們,要擔負這種,可能的毀敗呢?
倖存過後的我們。在沒有準備好,就被迫出櫃現身的人啊,最後究竟長成什麼樣子?在〈霧中風景二〉中的景象輕易就讓能讓我心碎:「大霧散去/你是唯一的倖存者/沒有來時亦無去路/唯你在曠野之中/長久佇立/的影子」。
最早登陸的走獸,有後悔自己不小心離開了海嗎?
後悔慢慢被愛變成賤貨,沒有來時亦無去路。
-
〈每天都是一種練習〉
出自布勒詩集《致那些我深愛過的賤貨們》
吻得太多
每個傷口都開了
怎麼也等不好一回完美的癒合
記不全愛過的初衷(印象中
整段大綱神聖得
神聖得能拿去朗誦)
淡紅的痂還那麼新鮮
誘拐食指從裡面再吸吮
一點點甜
(只要一點點 就好甜好甜)
每個傷口都開始咯咯笑
淚水也還燦亮一如既往
映照十一月的晨光
明天後天
大後天
我們都還同樣靦腆
微笑
說早
晚上手牽手
一起睡覺
延伸閱讀
1.【書評】湖南蟲:沒有詩也沒有關係?──讀鯨向海《每天都在膨脹》
2.【詩人╱私人.讀詩】潘柏霖:為什麼我們不能擁抱呢──讀孫梓評《你不在那兒》
3.【詩人╱私人.讀詩】波戈拉:無所不在的我,與偽裝的他者──讀零雨《膚色的時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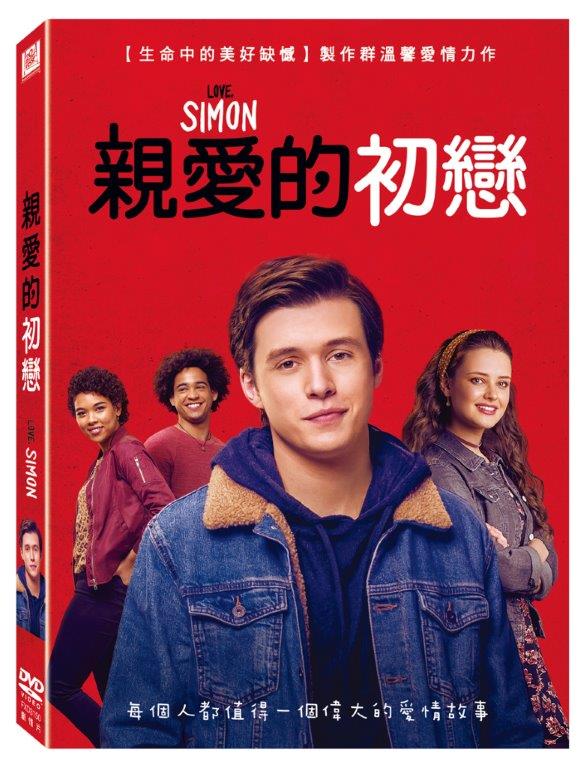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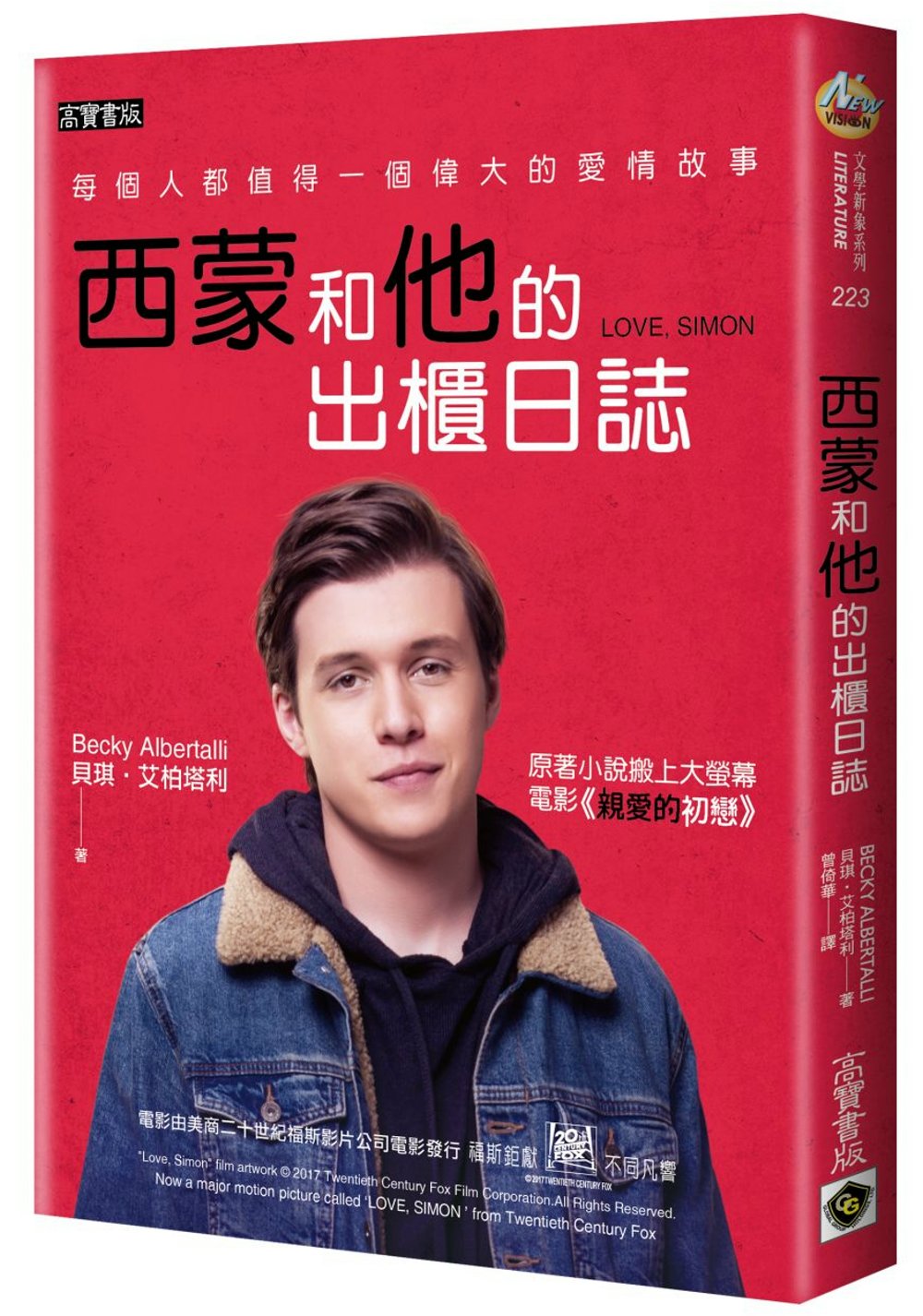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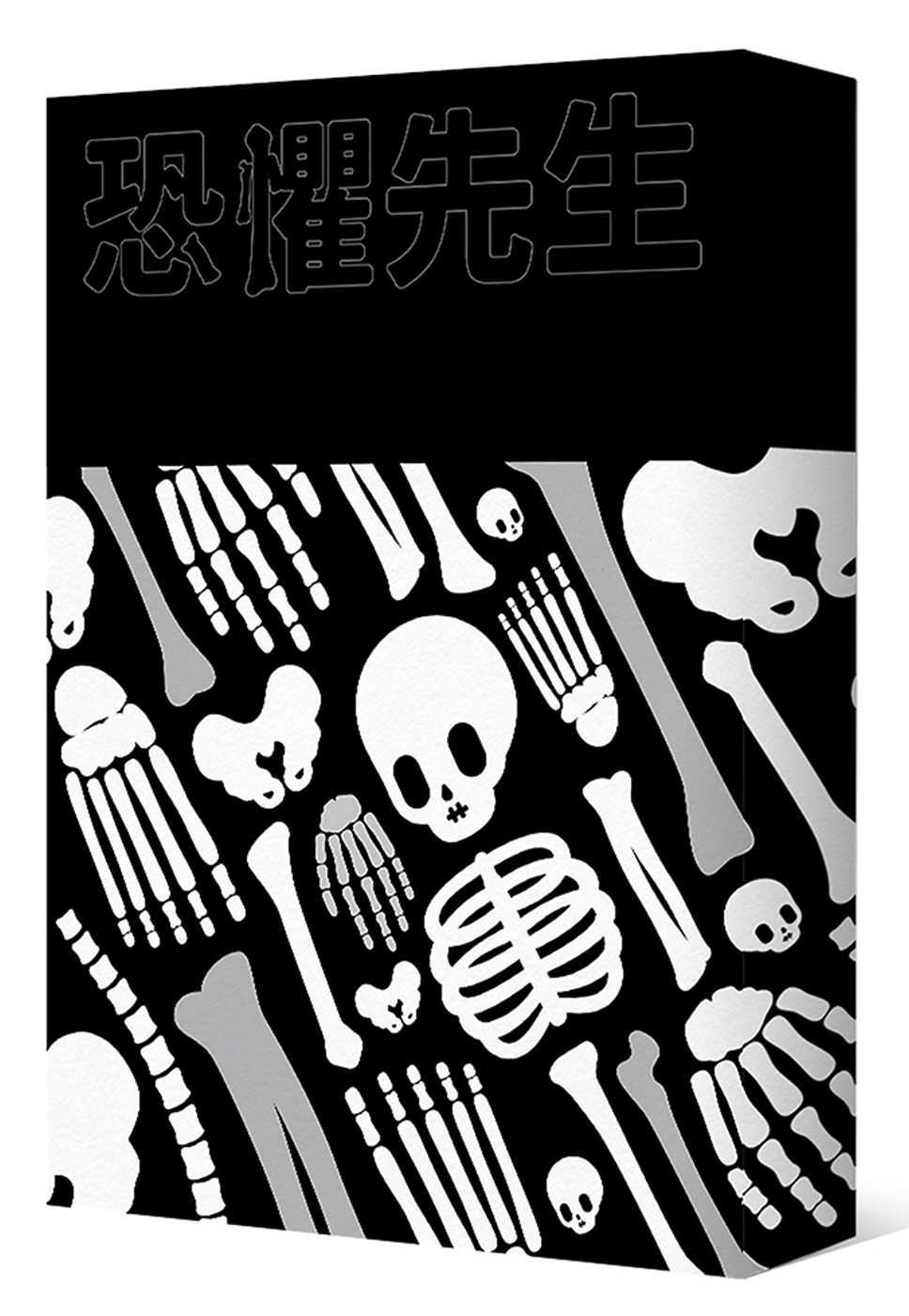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