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是金英夏(1968-)首部長篇小說作品(圖/漫遊者文化提供 © Munhakdongne)
「每個人都有破壞自己的權利,而且只有行使這種權利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人。」
韓國文學評論家柳浦善曾用這句話來說明小說《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的敘事核心,話中的一些張狂與危險,讓人想起光著頭、眼神銳利看著你的法國哲學家傅柯。
而坐在我們對面的金英夏卻直白地說,「與其說是生命政治,我倒認為是個人生命的權利究竟歸屬於誰的問題。」金英夏曾在媒體上公開說:自己的人生是一連串的上癮所組成,18歲開始的菸癮、20幾歲的遊戲上癮、飆車、紙牌與酒精,他花了好大的力氣才學會控制。也許是這樣的經驗,讓他為自己一連串上癮的人生,理出了國家政府對菸酒的管制,比起毒品卻相對寬鬆的矛盾,進而探問自己的身體、健康與生命的掌控權,應該屬於誰?
他舉例,像是西歐世界過去會重刑處罰自殺未遂者,或是儒教社會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任意毀損身體就被視為不孝的倫理。而我們拜訪的當下,韓國社會團體正在為廢除50年代成立的「反墮胎法」請願,金英夏說,「至今許多國家仍不接受女性有墮胎權利,這也是以『女性的身體是屬於社會的』思考點出發。但我堅信,個人身體的權利,基本上是屬於個人的。」
原來,在南韓知識型綜藝節目《懂也沒用的神祕雜學詞典》中,被視為時尚指標、看起來總是慢條斯理、溫文儒雅的金英夏,也有如此基進的姿態。
《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是金英夏最早享譽國際的成名作,書名來自法國女作家莎岡某次吸毒被捕後,對審查法官說的話:「只要不傷害到其他人,我相信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金英夏便用「個人有權利破壞自己身體」的激烈主張,描寫一種死亡的極端方式,以對國家、社會、父母所代表的權威提出反抗。「我讀大學的時候,社會正在進行打倒獨裁政權的革命,年輕人被強烈的氛圍籠罩,人類的暴力衝動有時是向著別人,有時也會失去方向用來對付自己。年輕人很容易在過度的自我陶醉和自我厭惡中擺盪,這種搖擺,很容易以『自我破壞』的衝動來表現。」回望那段寫作時期,他坦承,「我只是感受到強烈的憤怒而已。」隨著歲月經過,當他重讀20多歲時寫的這本小說,才發現當時自己是處於何種情況,「就像其他作家一樣,我們其實不知道自己現在在寫什麽,寫完了以後,要過了許久才會揭曉。」
 (圖/漫遊者文化提供 © Munhakdongne)
(圖/漫遊者文化提供 © Munhakdongne)
不懂壓縮美學的人,最終都不會知道生活的祕密
《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中,主角的職業是一位「自殺嚮導」,同時也是在完成每次委託工作後,會把委託者的故事「再創作」的作家。他欣賞畫家大衛(Jacques-Louis David)冷靜地把馬拉死亡的緊張感,凝結在至死也握著的鵝毛筆上,也喜歡閱讀旅遊指南和歷史書籍,因為二者都冷靜地把城市或歷史複雜的事實和生命,壓縮成幾行簡單的文字。金英夏解釋,「『壓縮的美學』是小說主角所主張的,他從事勸別人提早結束生命的工作,並將這份工作包裝成一種美學,這暗示著他相信『自己是神』的誇大妄想性格。」
 大衛的《馬拉之死》(La Mort de Marat)是法國大革命時代最著名的畫作之一。描繪法國革命家、記者尚-保羅·馬拉遭刺、死在浴缸的場景。(圖片來源 / wiki)
大衛的《馬拉之死》(La Mort de Marat)是法國大革命時代最著名的畫作之一。描繪法國革命家、記者尚-保羅·馬拉遭刺、死在浴缸的場景。(圖片來源 / wiki)
 《光之帝國》韓文版封面,漫遊者文化2019年出版
《光之帝國》韓文版封面,漫遊者文化2019年出版
小說中提及多幅西洋經典畫作,這些畫有何隱喻?金英夏說,他是在結束一趟40天的歐洲自助旅行後開始寫這本小說,「我認為,在視自殺為罪惡的歐洲基督教文化中,畫出在宗教故事裡登場的死亡主題,是對當時『以生産為美德』的社會做出迂迴的抵抗,因此我將『美麗地畫出死亡』的作品放在小說開端。」而小說的篇章名,他就以大衛的油畫《馬拉之死》、克林姆的《朱迪絲》、德拉克洛瓦的《薩達那帕勒斯之死》構成;他另一本描述北韓間諜潛伏南韓20年後突然接到「返北」命令的《光之帝國》,更直接與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的畫作《The Empire of Light》同名,加深了小說主角的生命痕跡被抹除,又突如其來被置換的超現實感。

左:克林姆的《朱迪絲》;右上:德拉克洛瓦的《薩達那帕勒斯之死》:右下:馬格利特的畫作《光之帝國》(圖片來源 / wiki)
金英夏說他喜愛傳統的美術作品,也關注現代藝術。他提到,現在被稱為古典主義的作品,例如安格爾或大衛的作品當初在發表當時,給予世界極大的衝擊,所以直到現在還被留存下來。「所有創作都有類似的層面,新的作品就是藝術家對以前存在過的作品的回答,這種回答大致以反抗的樣貌呈現。如同否定父母世代的遺產,子孫才會有所成長一樣,藝術也是這樣。在這個意義上,和製作完成度極高的作品相較,我更喜歡『與過去有強烈衝突』的藝術家和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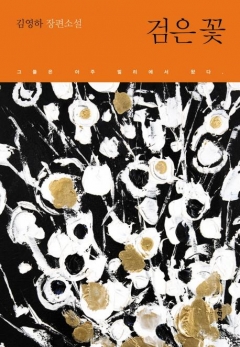 《黑色花》韓文版封面
《黑色花》韓文版封面
也許就是這種既延續卻又與之對抗拉扯的性格,讓金英夏的小說讀來也像是一種解壓縮的過程,偶有一些東西遺失或變形,比如,他喜歡在已知的史實裡安排一些更動,「韓半島就是非常特殊的區域,歷經王朝、殖民地、内戰、分斷的歷程,隨著南、北韓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理念對立,目前仍未停止敵對狀態,」金英夏認為,在這個過程中發生的悲劇,不只含有悲傷和惋惜,還呈現了對人類内在生命的反諷——人們必須活在愚蠢、錯誤的環境中,有時還經歷了許多可笑的事。「《黑色花》裡,身分被降為移民勞工的王族如此,《光之帝國》中突然被派到南韓、卻被北韓遺忘的間諜也是如此,我喜歡這種反諷,因此韓半島的歷史是很好的背景。我會先構思身處在這種有趣狀況中的人物,然後開始寫小說。例如《殺人者的記憶法》中,『罹患老年痴呆症的年老連續殺人犯』即屬此類。」
文學不能改變世界,但能承續個人心裡的過去和現在,達成和解
年輕時的金英夏深受馬克思主義吸引,大學時期正逢韓國民主化運動的高潮。問積極投身過學生運動的他,這段經歷是否影響了創作?「80年代許多韓國大學生因為對現實感到絕望,所以從外部尋找解決方案。因為相信美國默許並支援獨裁者,所以反美和反資本主義的思想受到歡迎,當時馬克思主義、毛主義、金日成主義等思想對韓國大學生非常具有吸引力。這些大學生參與了韓國的民主化運動,結果就是導致獨裁政權瓦解,獲得了總統直選的權力,並且誕生了以新憲法為基礎的第六共和國。」隨著民主化的進行,反資本主義、反美思想也逐漸在大學和社會中失去力量。金英夏坦承,他自己是對「個人」的關心多過於對社會和體制,才走上作家一途,「我想藉由作品訴說那個時代的故事。我認為文學雖然不能改變世界,但能扮演承續個人心裡的過去和現在的功能。大部分人都對於自己激越的年輕歲月都加以隱藏、擱置,但文學能再次召喚那些過去,經由讓現在的讀者閱讀,他們得以跟過去和解。這種方式能幫助讀者接受過去,而這種過程也發生在作家自己身上。」
一般將金英夏視為韓國當代文壇的一條分界,在他之前的韓國文學,多以農村為背景,主人公是從農村到首爾的知識分子,或是以韓戰及其後的民主化運動為主要事件的小說。與過去的體裁相比,金英夏確實發表了一些看似怪異的作品,「我的小說大多是以都市為背景,描述當代年輕人經歷的問題,有時用幻想的技巧來表現,因此當時的文壇覺得我的風格十分陌生。但現在,大多數讀者都在都市長大,和我使用同樣書寫方式的作家也成為主流了。」
小說《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自1996年出版至今,改版再刷幾十次,金英夏曾在書中自白,原本虛擬的「自殺嚮導」工作,在20世紀末的日本因為成了真正的職業而引發討論,雖然幾次想改寫,但比起成熟老練的筆法,他選擇坦然面對年輕時寫下的粗糙與挑釁,「這才是這本書的樣貌。」
 (圖/漫遊者文化提供 © Munhakdongne)
(圖/漫遊者文化提供 © Munhakdongne)
在衛星代替神靈俯視的世界,我依然在寫作
20幾年後再看自己的小說,金英夏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26歲寫這本小說時,完全沒想到會被介紹到外國,可是在出版兩年後被翻譯為法語,後來也有英語和德語等外語版本。」他曾在小說中開玩笑似地寫道:「小說家沒有作品被翻譯成英文出版,幾乎等同無所事事的人。」他的作品已被譯介到十多個國家,問起作品被廣泛翻譯有何感想?他說,「塞萬提斯以前說過,作品在作家生前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是非常光榮的事,但我認為,被翻譯的作品終究是該語言的文化資產。小說雖然是我寫的,但透過譯者和編輯之手,才得以被他國的讀者接受,在這個過程中,誕生了非常不同的文化内容。在這個意義上,我不認為被翻譯的作品完全只是我的小說,所以我幾乎不干預作品的翻譯。我相信作家的真正成就並非被翻譯的語言數量,而是母語讀者們的深刻理解和熱愛。」
最後問金英夏有沒有來過台灣,他出乎意料地關心起台灣出版社是否和韓國一樣集中在首都?我們還摸不清楚問題的用意,他就說,「對第一次接觸我作品的台灣讀者來說,因為台韓在歷史、地緣上有多處共同點,加上年輕世代也有類似的文化傾向,因此我相信,對於我小說的接受程度應該不難。」
20幾年過去,「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這句話仍帶點挑釁,金英夏選擇誠實面對這些傷疤,就是人生經歷的一部分,然後用書寫向自己過去的怒氣和解,也難怪他最後如此建議有志成為作家的人:「雖然應該要深入了解前輩作家和作品,但你如果不用自己的方式表現『真實』是不行的。唯有用自己的方式,正直地寫下屬於自己世代、自己的故事,才是正確的道路。」
延伸閱讀
1.【特稿】崔末順:抒情破壞與當代感性──韓國「新世代文學先行者」金英夏及其小說
2.【書評】石芳瑜:要麼創作,要麼殺人──金英夏《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的暴烈與頹廢
3.【專訪】為了寫出最幽暗的恐懼,她在半夜的山裡走了一年──專訪南韓作家丁柚井
4.【書評】廖梅璇:披覆著暴力輻射塵迎向花開──讀韓江小說《少年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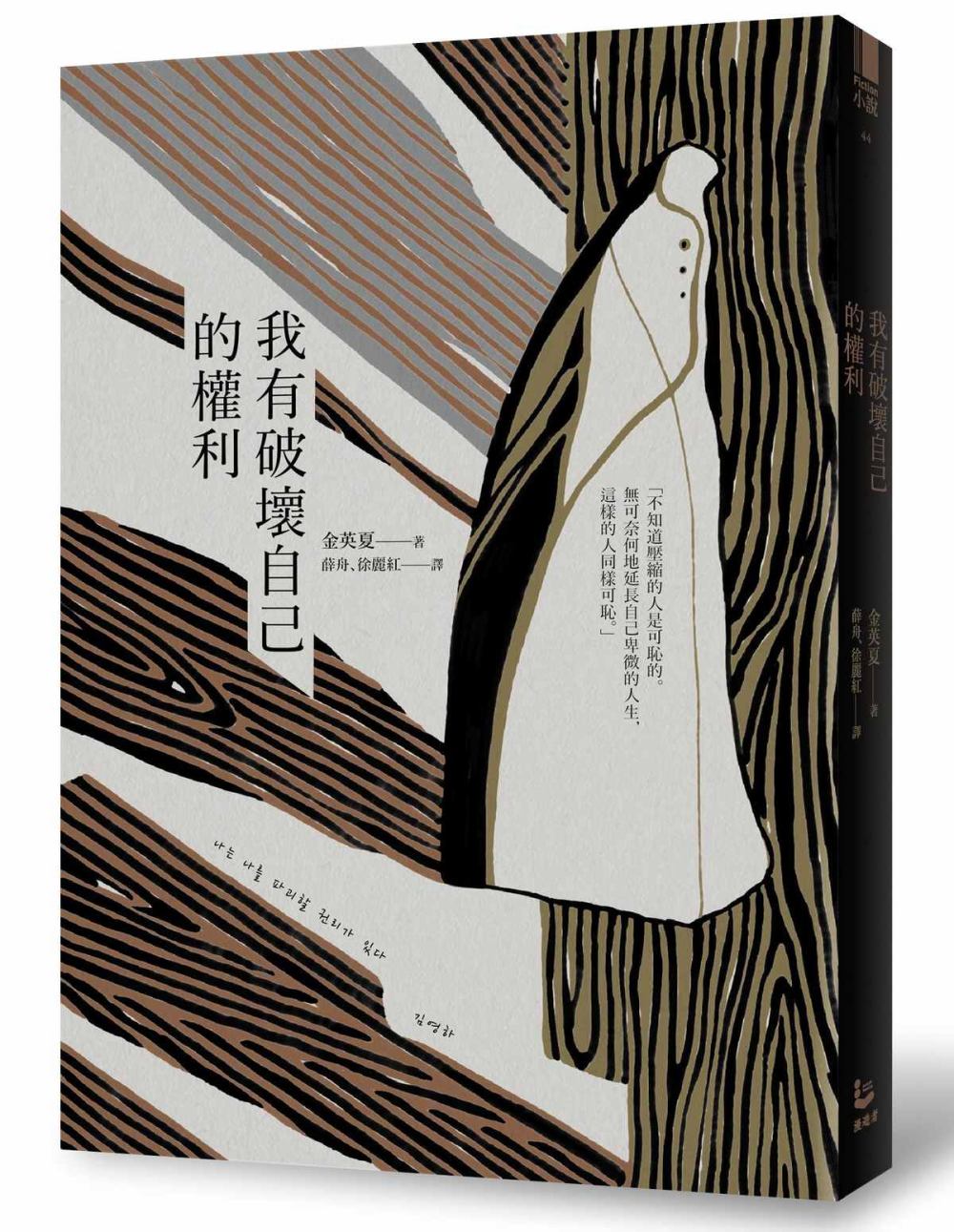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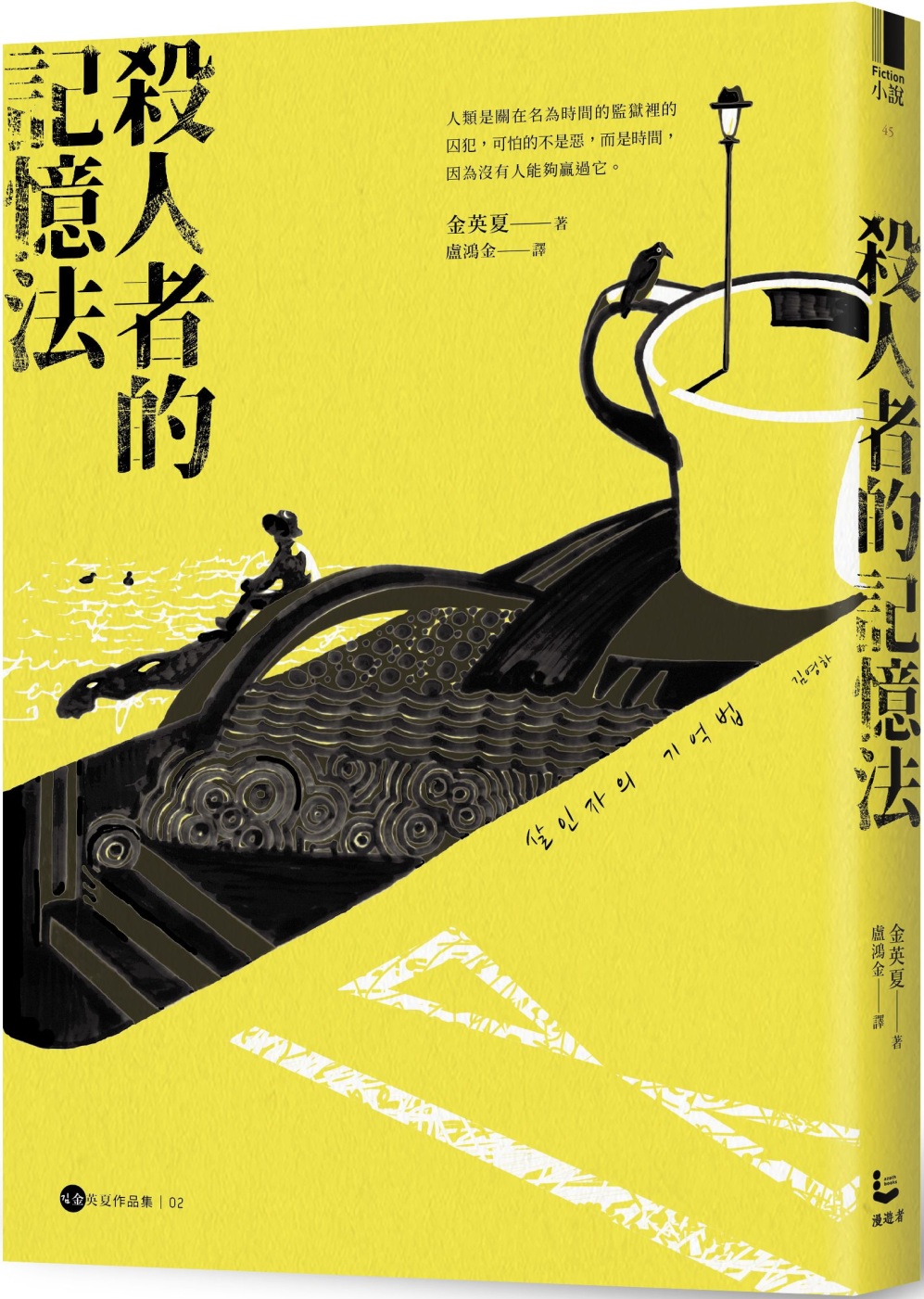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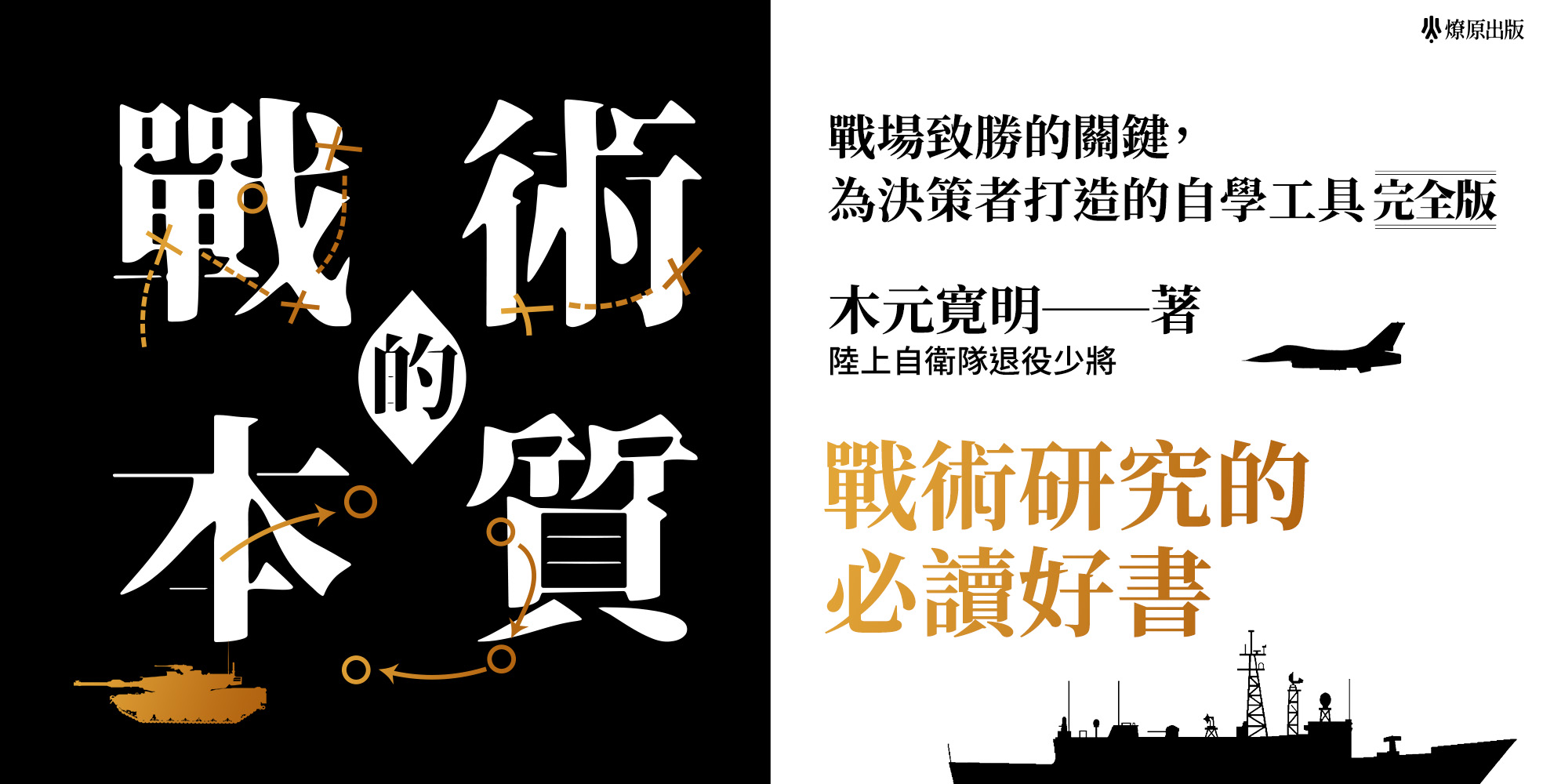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