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電影、電視、網遊等不同敘事媒介挑戰人們過去的感知習慣,許多小說家跋涉險路,窮盡各種能夠描述的情狀,企圖奪回被新媒介占據的領域,或許為了文字久遠輝煌的傳統,或許也為了丈量,丈量文字能鑽探生命地層多深。
《生命的測量》作者朱利安.拔恩斯(Julian Barnes),與英國文學史前輩約翰生博士(Samuel Johnson)一樣,既是作家,也是辭典編纂者,善於追究字源,給出例句,清晰明白界定字詞今生前世,如一把不出錯的鋼尺,適於用來測度人的理性範疇。然而當生命中的不測降臨,溫度計水銀亂竄,指南針失準,人類失去度量世界與自己的能力,語言忽地靜默,所有辭典字彙在悲傷前啞口無言。
本書是拔恩斯繼小說《回憶的餘燼》後,雜糅多種體裁再度書寫傷逝。在第一章〈高度之罪〉,作者鎖定19、20世紀之交,三個分別搭乘熱氣球旅行的真實人物,英國軍官伯納比上校(Fred Burnaby)、法國女演員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和法國攝影師納達爾(Nadar),採用報導文學紀實風格,由一百多年前熱氣球與攝影術的發展,論述人類面對現代化的激情與惶惑。第二章〈平平實實〉,想像力一反標題字面涵義縱馳,以真實人物為基底,織造伯納比與莎拉的無果戀情,從雲端意念陡降至現實人生,虛實相接不露針腳,足見小說家手藝高妙。到了第三章〈深度的迷失〉,作者剝除之前的象徵與隱喻,以散文文體直述與他結褵30年的髮妻驟逝後,被遺留於人世的傷慟。

朱利安‧拔恩斯畢業自牛津大學現代語文學系後,曾參與《牛津大辭典》編纂工作(圖片來源 / thecultureconcept)
談到書寫的技藝,技與藝總是相提並論,小說家畢生修煉的技藝便是以文字模擬世間種種狀態,遣詞造句擬真到了極致,便仿似成為實相。然而仿似終究是仿似,當死亡降臨,縱有一身技藝也無法讓愛人起死回生,人生便來到了失語時刻。「傷慟會改造時間,改造它的長度,它的結構,它的功能。」拔恩斯如此形容失去摯愛的劇變。傷慟意味著日常世界從此分為喪妻前和喪妻後,對於人事物的判斷開始動搖,朋友安慰的話語聽來別有用意,親人會在意想不到的時候刺痛你,生活中每件事物都移形換位,人與世界的相對距離一夕扭曲崩解,這是意義的強震。
愛有多深,死亡造成的地形塌陷就有多深,文字就有多難以沉墜觸碰痛苦,但埋在深處的情感,才是成就藝術的核心。創作宛如製作燈籠,一步步折紮骨架,糊貼棉紙,彩繪鏤刻,最後總要在燈座中心點亮火光,那是創作者的精神,是自我對世界的認知與情感,有了火燈籠才會發亮,但倘若火焰熾烈到燒毀一切,就什麼也沒了。
什麼也沒了。愛與傷逝的憂鬱何其相似,兩者都創造光影縱深,造就藝術,但光燄一旦閃燃會吞噬所有,徒留精神上的廢墟。拔恩斯比喻這困境彷彿置身熱氣球籃,陷入重重雲層,失去方向感。他不得不拋出45米長絲線上的小降落傘,握著氣閥繩,測速,定位,試著安全著陸,療傷,在虛惘與痛苦中倖存下來。

納達爾(1820-1910)是第一個進行空中攝影的人。(圖片來源 / wiki)
然而愛人的死亡是一種現實的減法,兩雙眼睛剩下一雙,人要如何在枯瘠的事實外存活?創作者總是夢想著憑藉藝術,或許能夠向上帝打個商量,讓所愛的她/他回來。拔恩斯自承:「作家相信自己的文字所創造的模式,並希望也堅信這些模式能加總成為想法、成為故事、成為事實。這向來是他們的救贖之道,無論有無傷慟。」但他顯然很清楚,兩千多年前關於奧菲斯(Orpheus)的希臘神話已經道出藝術的無能為力:樂手奧菲斯用演奏感動了冥王,冥王承諾讓他死去的妻子重生,只要他帶著她走出地府前,絕不回頭看她。可是為愛深入地府的人怎麼能夠不回頭?奧菲斯失妻後,被象徵非理性的酒神女信徒殘殺棄屍。藝術無法贖回死亡,愛到喪失了理性,結局就是殉葬。那麼,寫作對傷慟到底能產生什麼作用?
將兩樣從未結合過的事物結合在一起,有時世界就此改變,當納達爾結合攝影術與熱氣球,拍下第一張空拍照之際,便悄然改變了人類的視野。攝影如羅蘭巴特所言,證明被攝物曾在某一刻存在,並在觀看的當下透露那一刻已然逝去,因而成為現代的悼亡之術;而熱氣球飛行的高度,使攝影者抽離當下現實凝視地形與建物,企圖留存此刻的遺跡。拔恩斯在本書描述納達爾一再實驗如何讓空拍的影像顯影,顯見熱氣球與攝影的結合,暗喻著人類試圖抽離強烈情感,回顧確認災殤現場的掙扎。
這是生命的弔詭之處,愛需要追悼,而完美的追悼需要技藝。在巨大的憂傷中,拔恩斯以驚人的寫作技巧,剪裁貼縫歷史細節與遠颺的想像,再造愛的遺跡。儘管內在火苗熊熊燃燒,他仍折彎竹篾,紮起骨架,包圍起熱烈的痛楚,宛如保護脆弱的自我。愛是熱氣球,在空中不確定地飄搖,技藝卻讓人得以接近記憶裡的真實,盡可能重現逝去的風景,然後像伯納比般拉扯氣閥繩,拋出鉤錨,將熱氣球籃固定在陸地。傷逝者或許餘生都會隱隱作痛,但在行走現世孤旅時,總有一盞燈照明前方路途,像頻頻回首的奧菲斯,每次回首便再度感受到失妻的痛苦,體認死亡的不可逆,過程本身卻成為一種療傷,一種回歸現實的試煉。
因而《生命的測量》,是一位極度理性,精準拿捏技巧的作家,對傷慟的多方探究。由於理性,拔恩斯認知到意識底層哀痛的深度有多麼難以追索;由於精準,他詳盡測繪出悲傷的地形走勢,從迷茫,麻木,追悔,刺痛,到挽回的渴望,記憶的延續與消退。正因他如此清晰明白地界定痛苦的疆域,並留下文字無法觸及的空白,療傷成為可能。在技藝與精神結合的光源下,他支撐著自己繼續寫下去。
如此理性節制地書寫死亡,卻寫得如此動人很少見,正如純粹的愛與技藝,從來都很珍稀。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1.【書評】蘇絢慧:關於生命的退場,我們所知道的實在太少──讀《在我告別之前》
2.【鹹水傳書機】一個年輕醫師的人生最後一哩路──《當呼吸化為空氣》
3.【專訪】願失去的痛苦,不再孤獨──林書宇電影《百日告別》
4.【專訪】《旋轉門》蘇偉貞:生活元素單純以後,才可以裝進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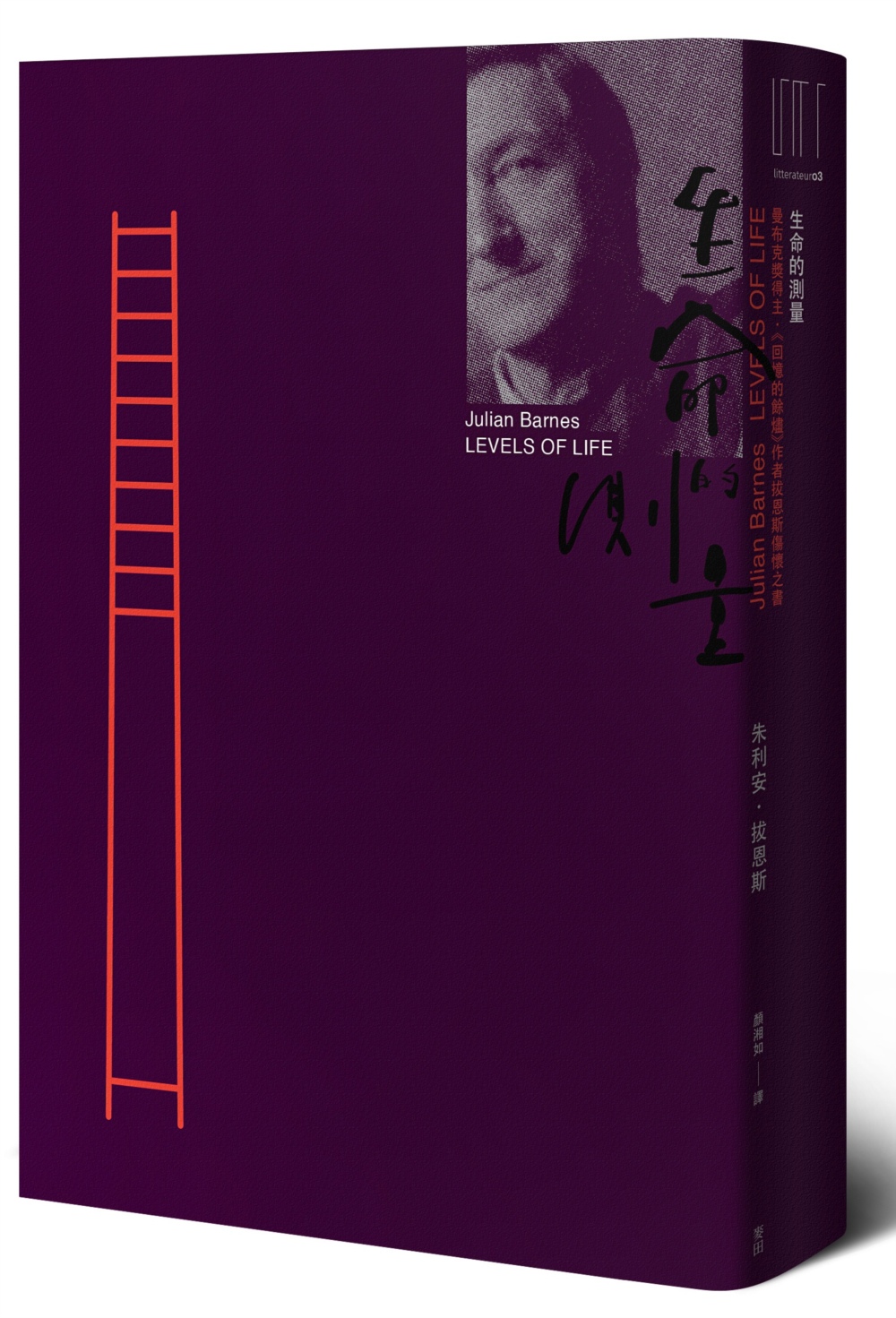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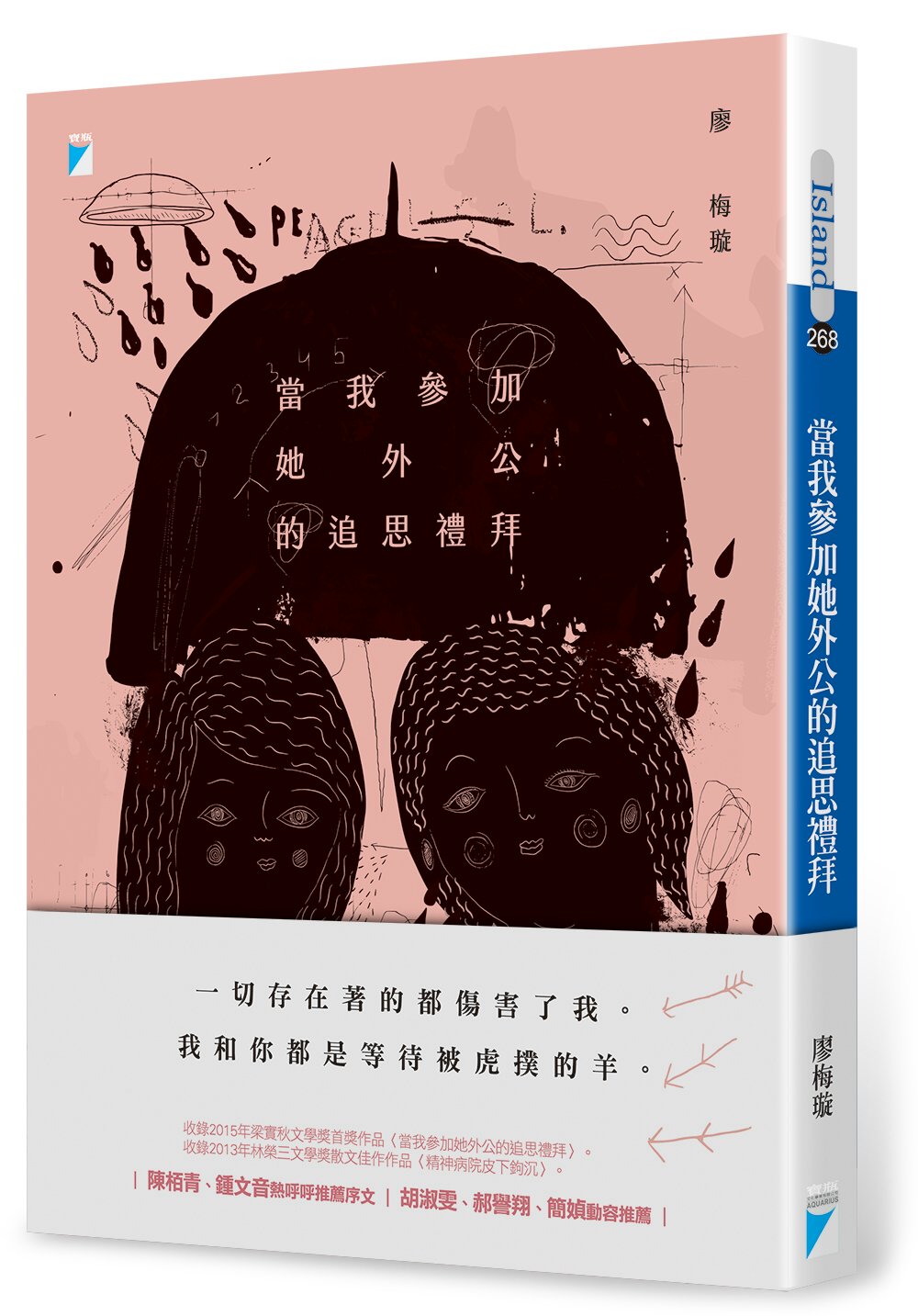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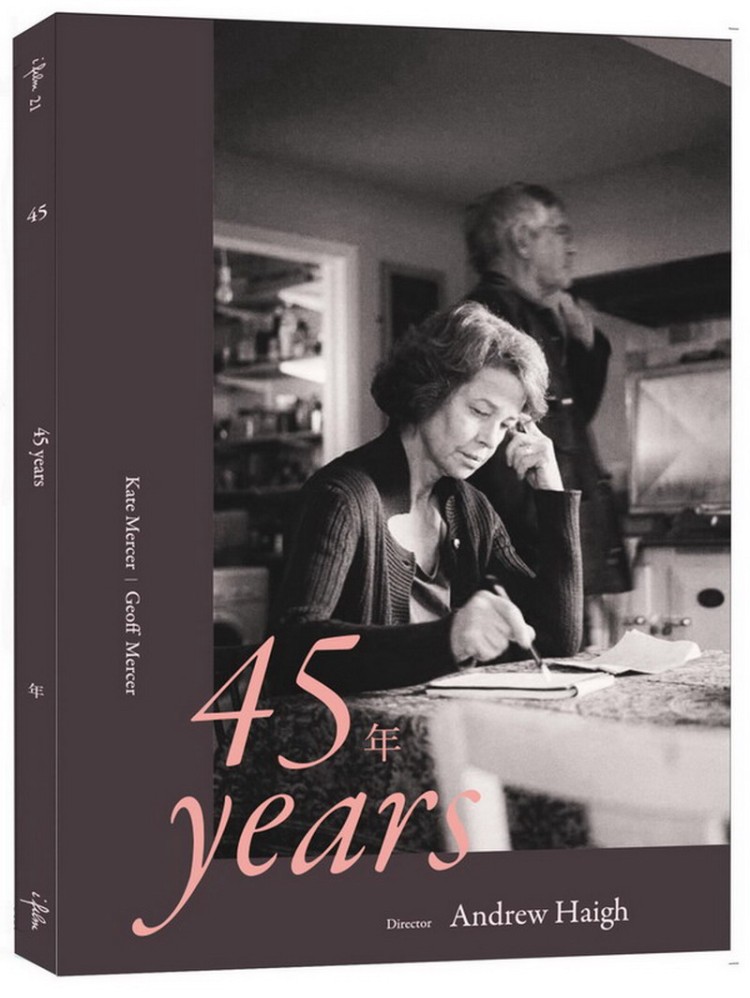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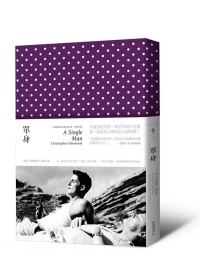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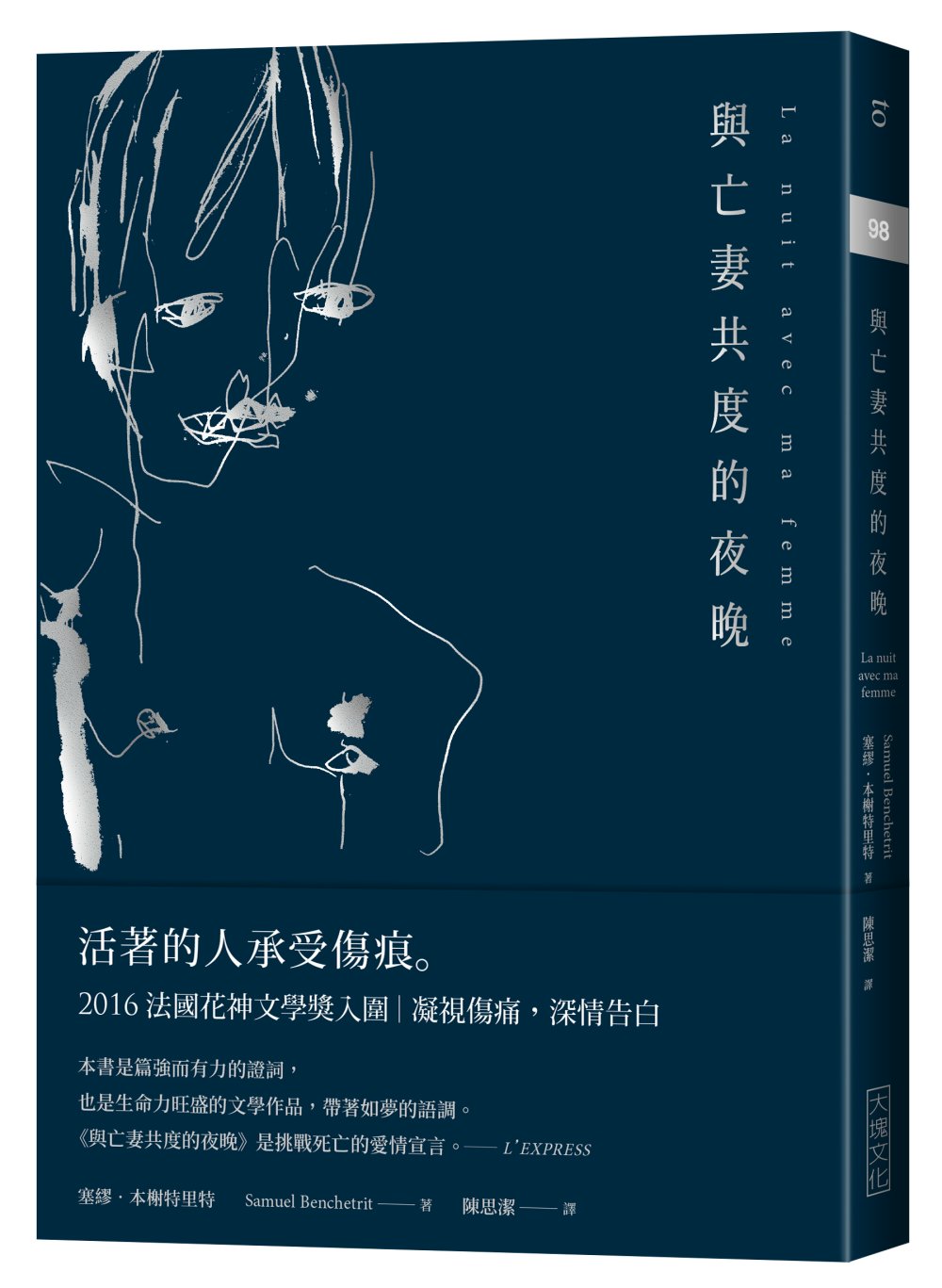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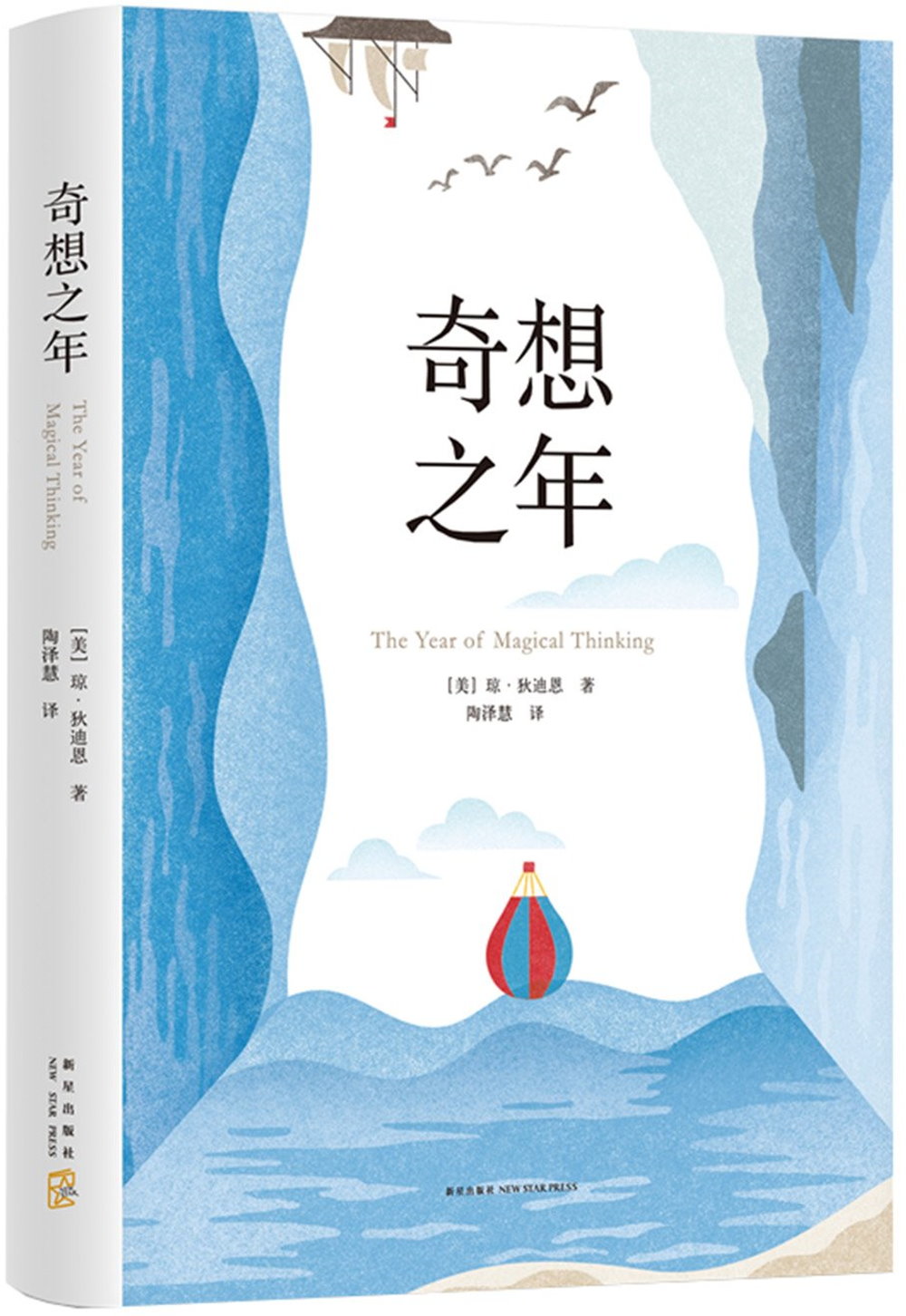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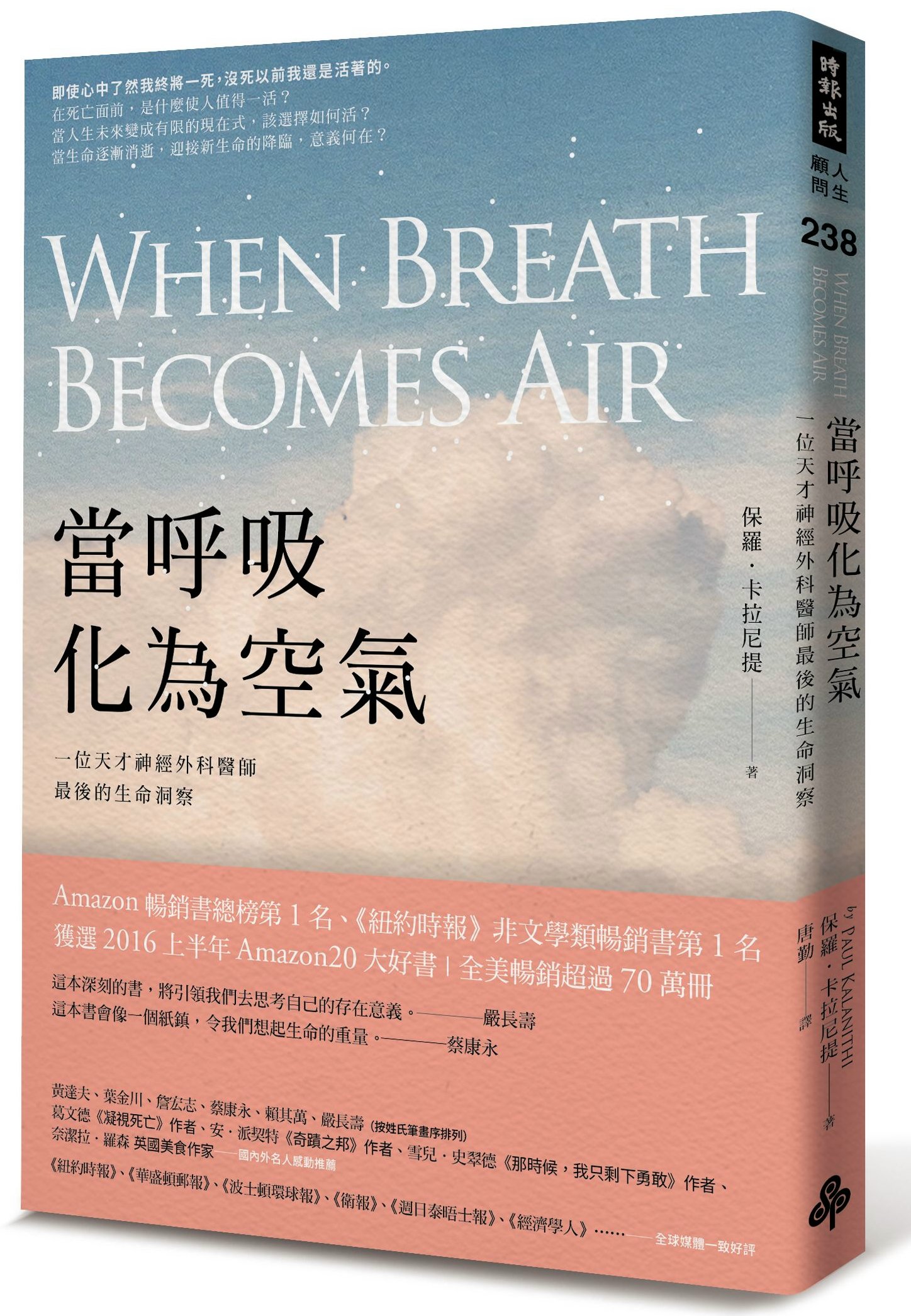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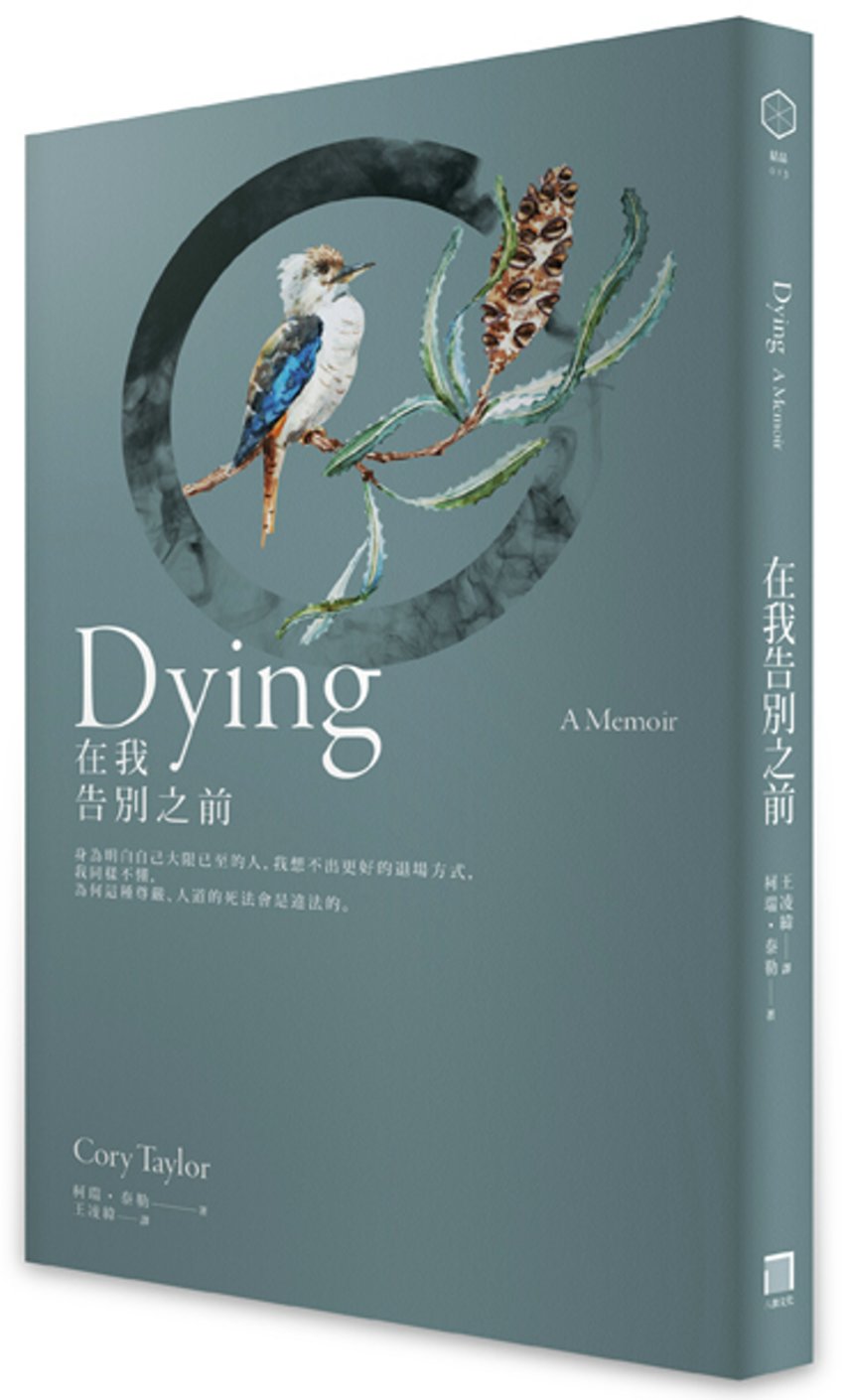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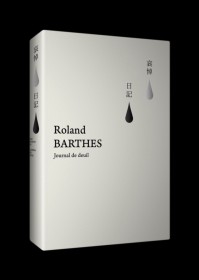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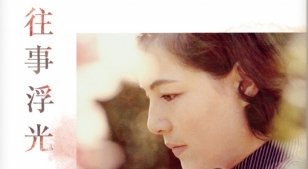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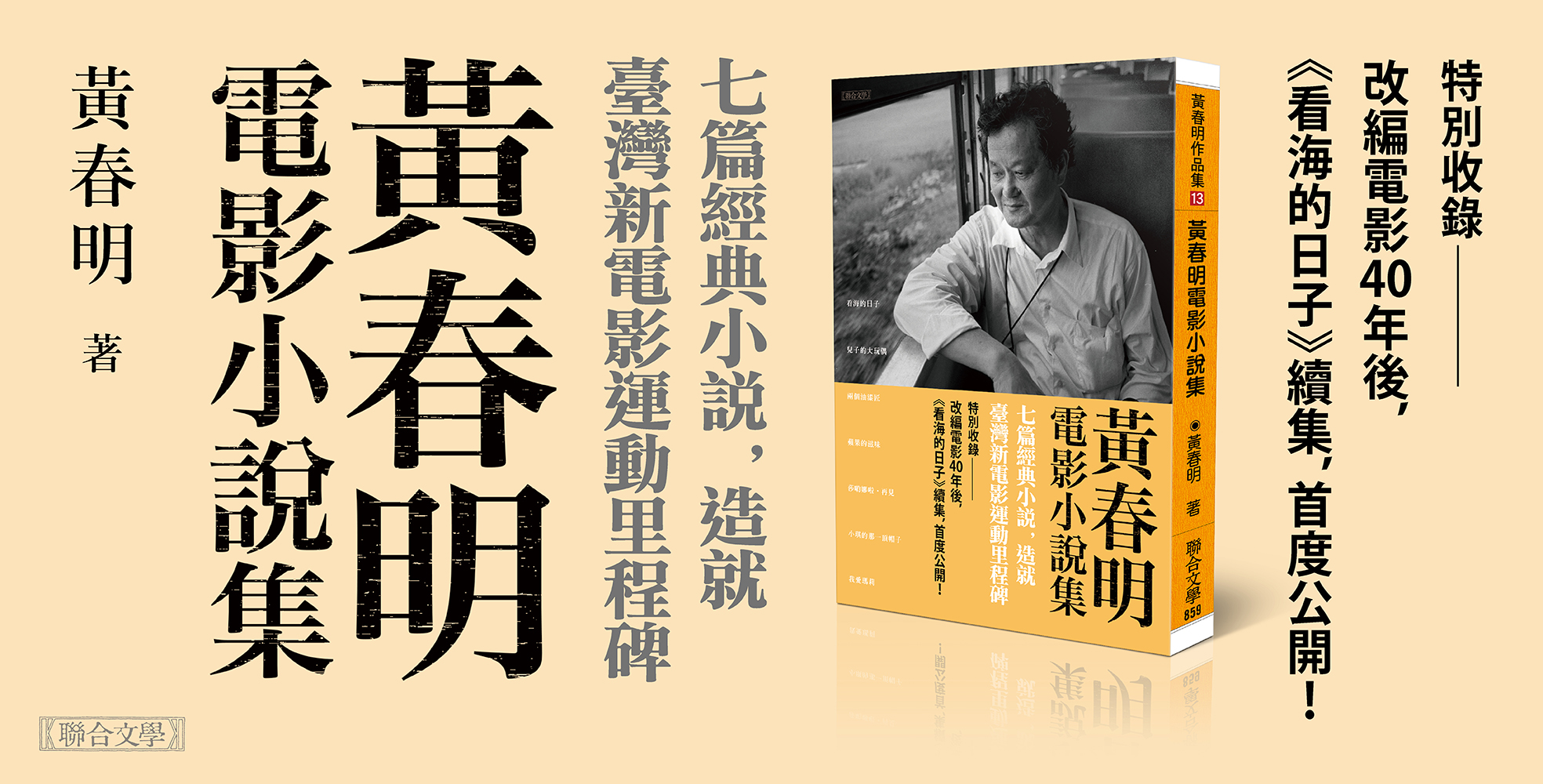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