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在前頭,《同情者》未必是你所定義的推理小說,故事沒有明確的謎團,作者也不刻意製造懸疑感,如果不能從緩慢的文字行進間感受到一點美式冷硬派的精神,那這部小說可能不是身為推理迷的你會想要讀的。
但我還是推薦你讀它,因為它真的很精彩。
故事發生在越戰結束前後,主角是個無名的敘事者(冷硬派精神之一)。他的父親是來到越南的法國傳教士,他背著私生子、雜種的身分長大,對西方──如同對他父親般──懷著莫名的嚮往與恨。青少年時他在同儕的感召下加入共產黨,稍後以「研究敵人」為目的赴美留學,畢業後加入南越政府,成為負責情資保防的「將軍」(一樣無姓名)最親近的副官。他於是成為雙面諜:為北越情蒐,同時在美國顧問的指導下嚴刑審訊北越情報員。
1975年,西貢淪陷,主角伴隨將軍流亡洛杉磯,一面過著與眾多亞裔移民一般的美國新生活,一面繼續監視南越的流亡人士。當他發現,他最好的朋友將加入將軍組織的先鋒隊,準備從泰國「反攻越南」時,他陷入兩難,他必須將情報提供給河內,他也必須遠赴泰國,希望救朋友一命。
整本小說約莫四百多頁,但其中所使用文學技法之豐富,涉及題材之深廣,實在難以泛泛討論,我只能略提其中與推理小說相關者。主角的形象帶有很強冷硬派角色的影子,他不是叛逆刑警,不是私家偵探,也不是勒卡雷筆下史邁利那般高階的情報員,他僅是一個鬆散體制底層的小間諜,遊走在失根的越南移民間,不停向一個「巴黎的堂姑」寫信,卻從不知道自己匯報的上級是否存在。但他仍承襲了那些白皮膚冷硬派前輩的DNA,在冷漠寡言的外表下藏著一縷詩人般碎唸易感的靈魂,他穿梭在洛杉磯的街巷,冷眼觀察這個曾承諾要保護、隨後又遺棄越南的國家,酒精與槍火是他的生活日常,他很少獲得,經常失去,經常掙扎在利與義之間,經常見到那些死去的亡靈。
喔,他承襲的傳統還有一項,就是對女人的獨到哲學,例如這段:「我來到蘭娜身旁坐下,什麼都沒想,只是依循著直覺以及我與女人攀談的三大原則:不要徵求許可、不要打招呼、不要讓她先開口。」獲益良多。
作者並不刻意「探討」什麼,只是讓那些沉在深處的議題自然而然地浮到故事的表面,將詮釋議題的權利交給讀者。我特別喜歡「吃喝無度的上校」之死那段所呈現的心理掙扎,關於越南流亡社群的描寫,與台灣眷村文學也有種似曾相識之感。
最後我想引用一小段《同情者》故事中的文字做結:
我閉上眼睛,經過一段時間的黑暗,我躺在床墊上漂過一條黑河,前往一個不需要護照便能進入的異國。在當地眾多謎樣的特色和可疑的動植物與人當中,我現在只記得一樣,我的心被抹得一乾二淨,只留下這枚致命指紋,那是一棵古老的木棉樹,是我最後休憩的地方,我把臉頰貼在那有如罹患關節炎的樹皮上。夢中的我倚著那棵長滿瘤的樹幾乎就要睡著,卻漸漸發覺我耳朵貼靠的那個節瘤其實也是一隻耳朵,扭曲僵硬的耳朵,它聽覺史上累積的耳垢就嵌在彎彎曲曲耳道的青苔裡頭。木棉樹有一半聳立在我頭頂上,另一半隱沒在我身子底下紮了根的土地中,我抬起頭,看見的不只有一隻耳朵,而是有許多耳朵從厚實樹幹的樹皮突出來,數以百計的耳朵在聽著並聽到我聽不見的聲音。

延伸閱讀
1.【書評】臥斧:越戰、間諜,以及人性──讀《同情者》
2.【書評】葉佳怡:為了相愛,遺忘仇恨;為了謙遜,記住相殺──讀小說《同情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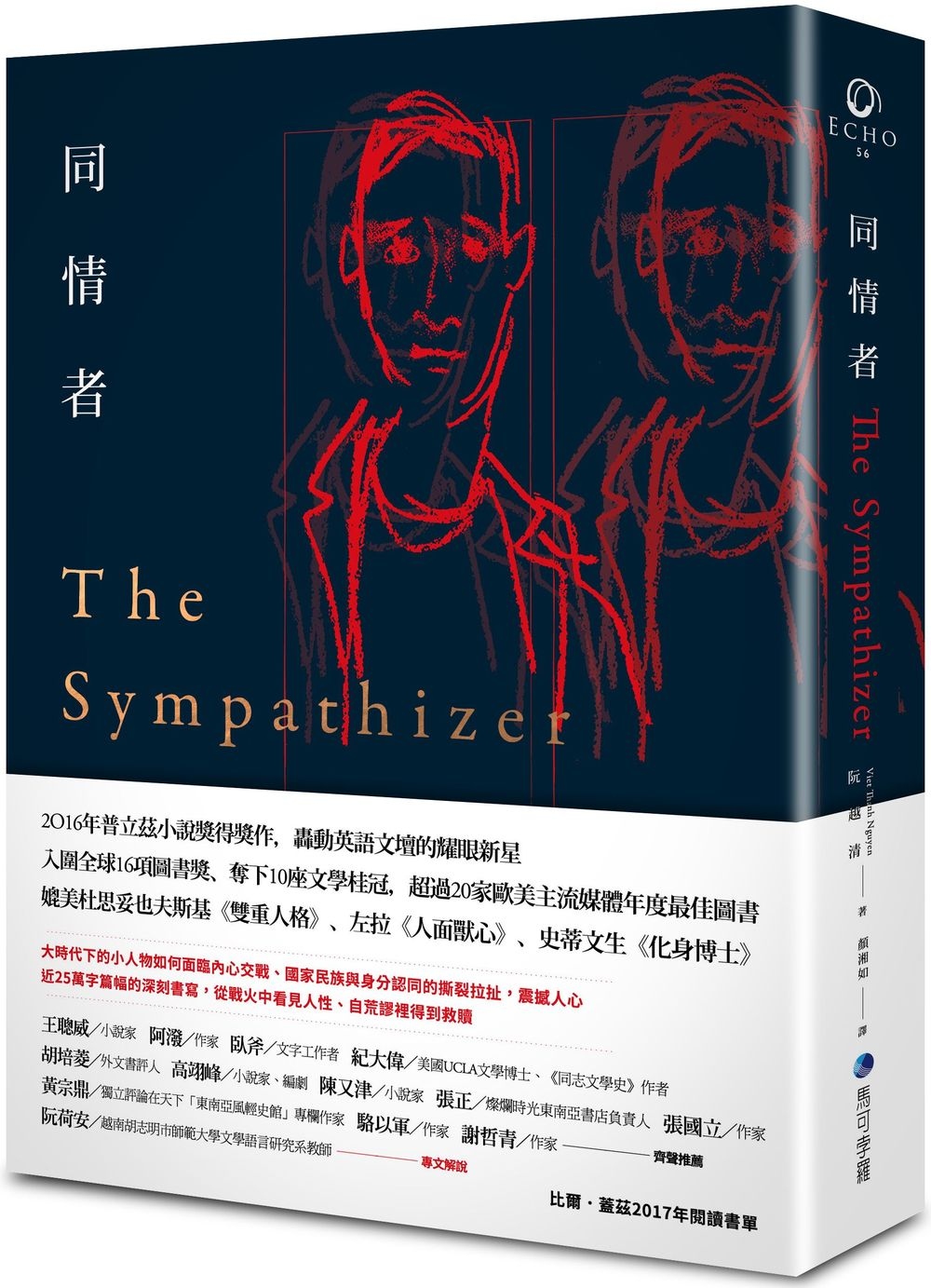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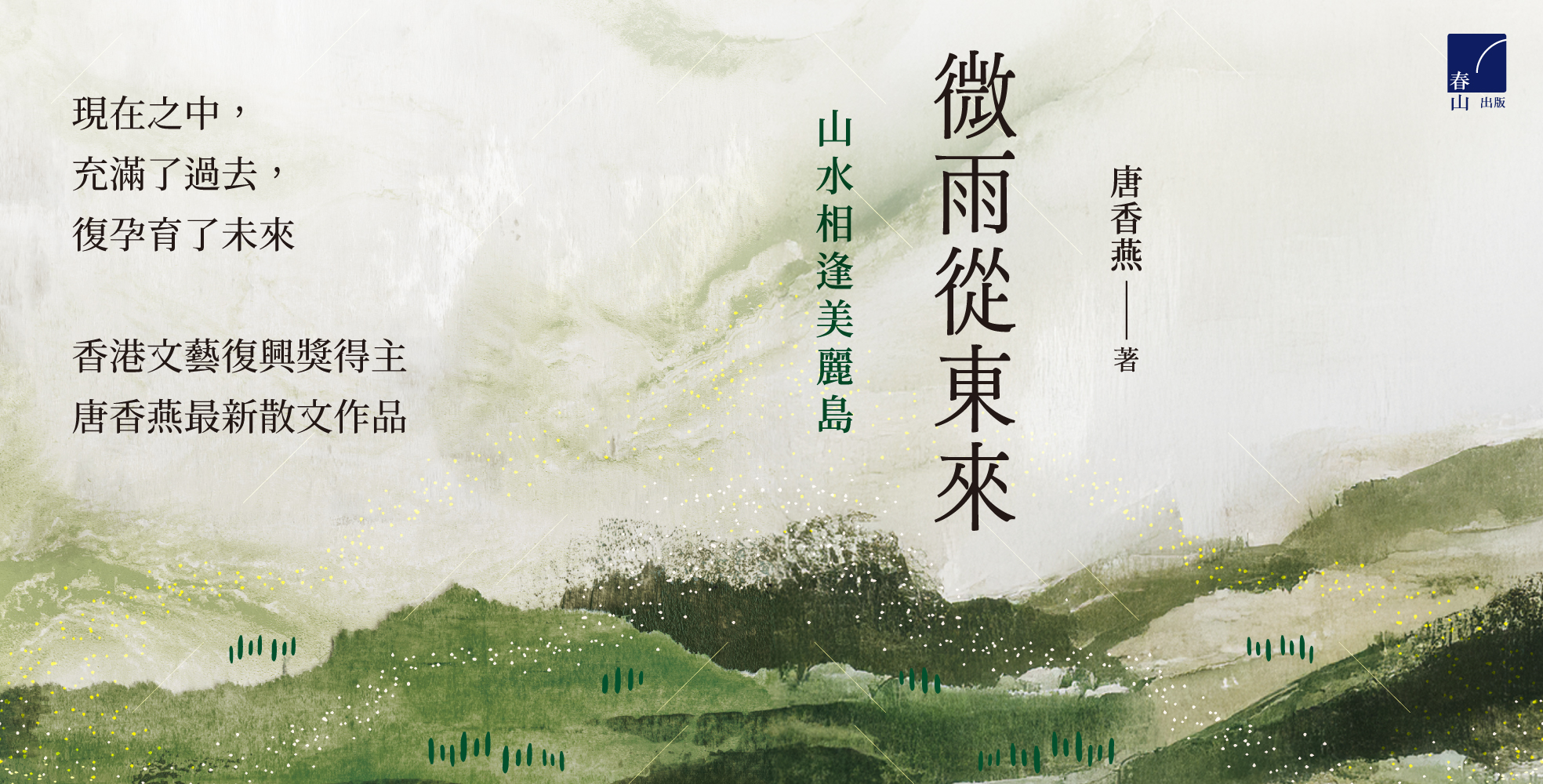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