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書之子》,我訪問了原始構想者山姆.溫斯頓(Sam Winston)之後,一直掛在心上的是有幾個問題一定要請教繪者奧利佛.傑法(Oliver Jeffers)。譬如小女孩為什麼是藍色的?為什麼她漸漸從部分藍色變成全部藍色?這種問題,如果以文字書面去詢問,往往斷章取義,就算列出幾個問題透過電郵詢問,也像是問電腦而不是問本人。這段期間,透過出版社、版權公司、Oliver Jeffers工作室助理往返確認拜訪時間,即使約到時間也非常匆促,難以成行,加上他的新書Here We Are (歡迎來這個美麗的星球)即將出版,得配合遍及英國與美國各地的新書宣傳行程,在這樣的時刻,想要問他前一本書的問題,的確強人所難。
經過幾個月的考量,我很固執地一直等到他的新書發表巡迴,趕到現場,充當第一線的粉絲。甚至因為擔心人生地不熟,我跟隨了兩個城市的書店,先面對面打招呼與說明,加上一封誠意十足的信,才進入Oliver Jeffers的工作室採訪。這一天是他出門五個星期之後,回到工作室的第一個工作日。完全進入工作模式,在我拍照的幾分鐘裡,他和助理們持續忙著回覆網路訊息和調整各路進度。幸好年輕、體力足,這種拚命三郎的工作方式,幾乎插不上一句話,連原來想要的問題也覺得看到本尊、進到工作室就心滿意足了,因為現場的能量太強大,一股「一定要做好」的信念與積極的動力,圍繞在他的周圍。
 馬不停蹄的Oliver Jeffers與他的工作室一角(攝影 / 賴嘉綾)
馬不停蹄的Oliver Jeffers與他的工作室一角(攝影 / 賴嘉綾)
我們先從Here We Are 的書店巡迴分享會開始,創作這本新書的原因是Oliver Jeffers當爸爸了!當了爸爸更感受到:大人們應該告訴孩子們什麼?留什麼樣的地球給孩子?突然,心情嚴肅起來,在享受與孩子相處時光的同時,越發啟動身為父親的使命感。面對自己的孩子,那其他孩子呢?新書發表的對象是小孩,家長自然也是重點,這本書讓家長一邊對著孩子讀書,也詢問自己在地球上的參與感。
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書店的新書發表會,一上場,Oliver Jeffers率性的連麥克風也沒拿,以他獨特的北愛爾蘭快語調,先說起他自己。「所有的故事都是真的。」他說,「我每一本創作的書都來自真實的故事,不過得要用引人注意的方式來說故事。」他的第一本書是How to Catch a Star,這原來只是幾張畫;話說他曾經舉辦過油畫展,而這也一直是他創作的重要部分,他經常在完成書與書之間的時間創作油畫,也經常在創作油畫時想書、做書,這些不僅是工作的分配,也是調劑。

Oliver的畫具(攝影 / 賴嘉綾)
Lost and Found(中文版《遠在天邊》)當然也是真實故事,他曾經是那個走失的男孩,只不過企鵝是他另外加進去的。至於後來那個喜歡吃書的小孩The Incredible Book Eating Boy(中文版《不可思議的吃書男孩》),其實是他的弟弟,但他可不覺得吃了書會變聰明。Oliver Jeffers說話非常快,而且他說每個巴爾法斯特(Belfast)的人都很會說故事。他在澳洲出生,那兩年恰好是爸爸媽媽在那邊旅行,出生後回到北愛爾蘭,在巴爾法斯特長大。他從來不認為澳洲對他有特別影響,他完完全全是北愛爾蘭人。
 Lost and Found中迷路的男孩就是Oliver Jeffers本人(圖/中文版內頁)
Lost and Found中迷路的男孩就是Oliver Jeffers本人(圖/中文版內頁)
 「吃書男孩」原型是Oliver Jeffers的弟弟(圖/中文版《不可思議的吃書男孩》內頁)
「吃書男孩」原型是Oliver Jeffers的弟弟(圖/中文版《不可思議的吃書男孩》內頁)
那個把心裝在瓶子裡的女孩呢?曾經一度失去好奇心的女孩,決定把心放在安全的地方,就是背在身上,隨時可以看到,不至於失落;在經過另一個小女孩的協助後,她找回對人生的思索與好奇,決定將這顆心完整地放回。The Heart and the Bottle (中文版《害怕受傷的心》)初讀是個憂傷的故事,但延伸之後,就成為一個尋回自信與愛的過程。
他的故事中幾乎不明講每個角色之間的關係,也有知名書評認為他的故事不清楚完整,但這都不影響讀者,尤其孩子多半不在意人與人之間的角色關係,孩子在意的是人與人的情感關係,是爸爸還是爺爺?是女兒還是偶遇的小女孩?都沒有關係,重要在彼此的互動與互信。在戰火下的童年確定是有影響的,只是我們不能說到底是哪些。但他處理人際關係的手法,顯然別出心裁,譬如一群長一樣的The Hueys in The New Sweater,當其中有一個變化出不同後,整群人也群起效應,從不同到相同,從相同到另一種不同,在在提醒讀者自主性與同中求異的特質。
Oliver Jeffers創作繪本15年,已經出版14本書了,在藝術界、繪本界游刃有餘。而且他每一次的作品都啟動讀者的哲思,即使用小小的哏,也一而再的變化。加上他的手寫字體在繪本界成了顯學,引領繪本使用手寫字體的風潮。此外,他每一個活動都是話題,譬如2014年與U2合唱團合作的MV,〈Ordinary Love〉 這首歌曲為電影《曼德拉:漫漫自由路》的主題曲,講述南非總統曼德拉爭取人權與自由的歷程。
2015年,Oliver Jeffers在倫敦Lazarides Gallery舉辦個人油畫展,以藝術與科學不同觀點詮釋風景。2016年他與字型藝術家Sam Winston合作的《書之子》,讓繪本藝術不設限,把文字變成圖像,拓展繪本的多面層次,蘊藏經典文學於繪本中,並在波隆那得到拉加茲大獎(BolognaRagazzi Award)。接下來,2018年在德州 NCCIL(The 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ren's Illustrated Literature)的原畫展、2020年在倫敦的油畫個展。
其中有一本2012年出版的The Moose Belongs to Me(中文版《這隻麋鹿是我的!》),一直被擠在許多大型活動中,多年過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The Moose Belongs to Me 的故事是這樣的:男孩Wilfred夢想有隻麋鹿,某天真的有隻麋鹿出現,所以男孩開心地為牠繫上名牌,名字是Marcel。男孩設了很多規矩要牠遵守,但是有些對麋鹿來說很容易,但其他的牠就不理會了。後來除了男孩,也出現了不同的人對麋鹿呼叫不同的名字,而麋鹿也似乎有所回應和回報。從人的觀點出發,這是一隻無法確定所屬於誰的麋鹿,但若是從麋鹿的觀點來看呢?
循著這樣的脈絡,看到新書《歡迎來這個美麗的星球》時,覺得他多年來以做書準備好當父親,而當了父親之後,用這些對人際的關懷輔佐許多人邁向好父親的路。隨手翻閱一下,這像是一本任意揮灑的知識類繪本,告訴孩子我們身處的地球在太陽系裡的位置、地球的組成、海與陸地;儘管人類吃喝保暖的是很重要,人又有各種顏色和大小尺寸與長相,動物們何嘗不是如此?當我們慢慢學習到用適當的語言交流人際關係時,地球也在物換星移中漸漸變化;如果有什麼不明白的,就問吧!但仔細品嘗後,感受到他對世界溫暖深度的關懷。

而《歡迎來這個美麗的星球》的寶寶為什麼也是藍色的呢?記得《書之子》裡的女孩嗎?那天在第一個簽書會排隊排了將近一個鐘頭後,問了這個問題。他頭還沒抬起來,就說:「因為沒有藍色的人種。」「啥?」我為什麼從來沒有想到?我們有白種人、黃種人、暗膚色、紅色的⋯⋯但沒有藍色的。在簽書會或是訪問中,他一直明白闡述想法,又設法留給讀者想像的空間,一如《書之子》的最後,那張在鑰匙上繫著的紙標:「想像力無限供應」。
受訪的當天,他穿了工作室設計的厚棉套頭T恤,以Once Upon an Alphabet, Short Stories for All the Letters 這本書的封底字母做的圖案,淡亮悅目的粉紅色,非常有精神。儘管已經五個星期的旅途,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馬不停蹄。提到兒子、妻子、與另一個即將報到的新成員,原來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但現在他會陪孩子早餐、晚餐,如果有必要加班的話,也是等孩子入睡後。這位年輕的父親,眼中閃著的盡是對人生與工作的熱愛。
 Here We Are 的寶寶是藍色的,Oliver說:因為世界上沒有藍色人種(圖/Here We Are 內頁)
Here We Are 的寶寶是藍色的,Oliver說:因為世界上沒有藍色人種(圖/Here We Are 內頁)
作者簡介
部落格:Too Many PictureBooks
工作室:在地合作社The PlayGrounD
延伸閱讀
1.【主題繪本控】賴嘉綾:突破極限的繪本創作者──拜訪《書之子》作者Sam Winston倫敦工作室
2.【好設計的理由|繪本篇】印刷、選紙、裝幀、字體,超越原創構圖框架,以細節決勝負的書籍設計
3.【主題繪本控】繪本的「暗號」你接得到嗎?──繪本職人賴嘉綾帶你認識8個常見圖像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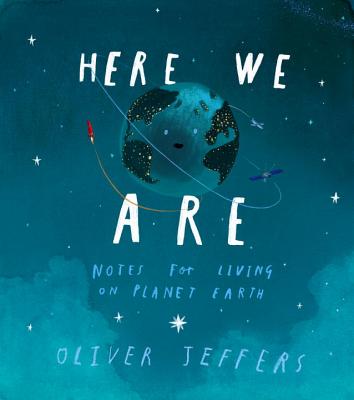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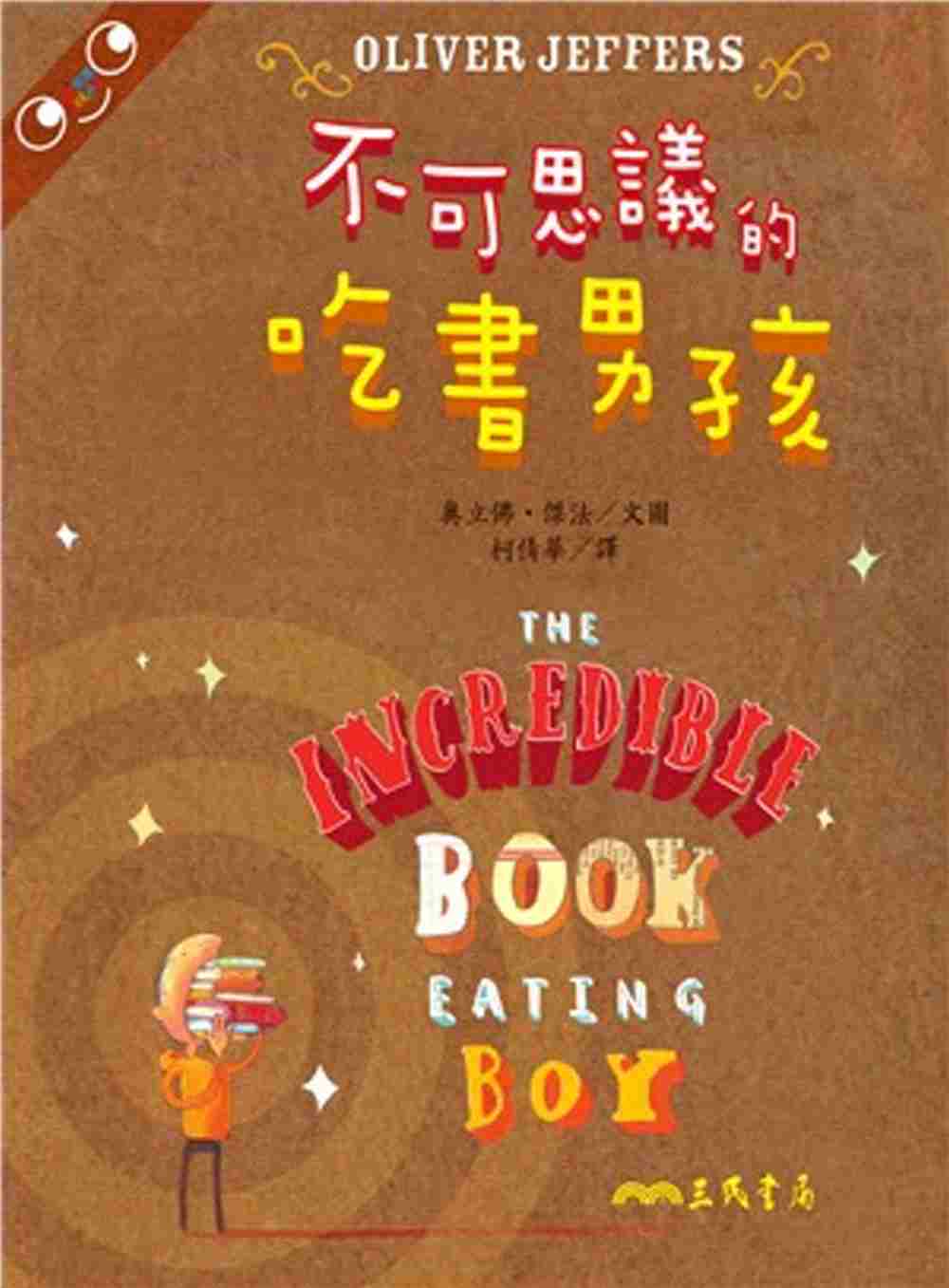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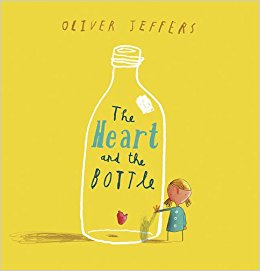
 害怕受傷的心
害怕受傷的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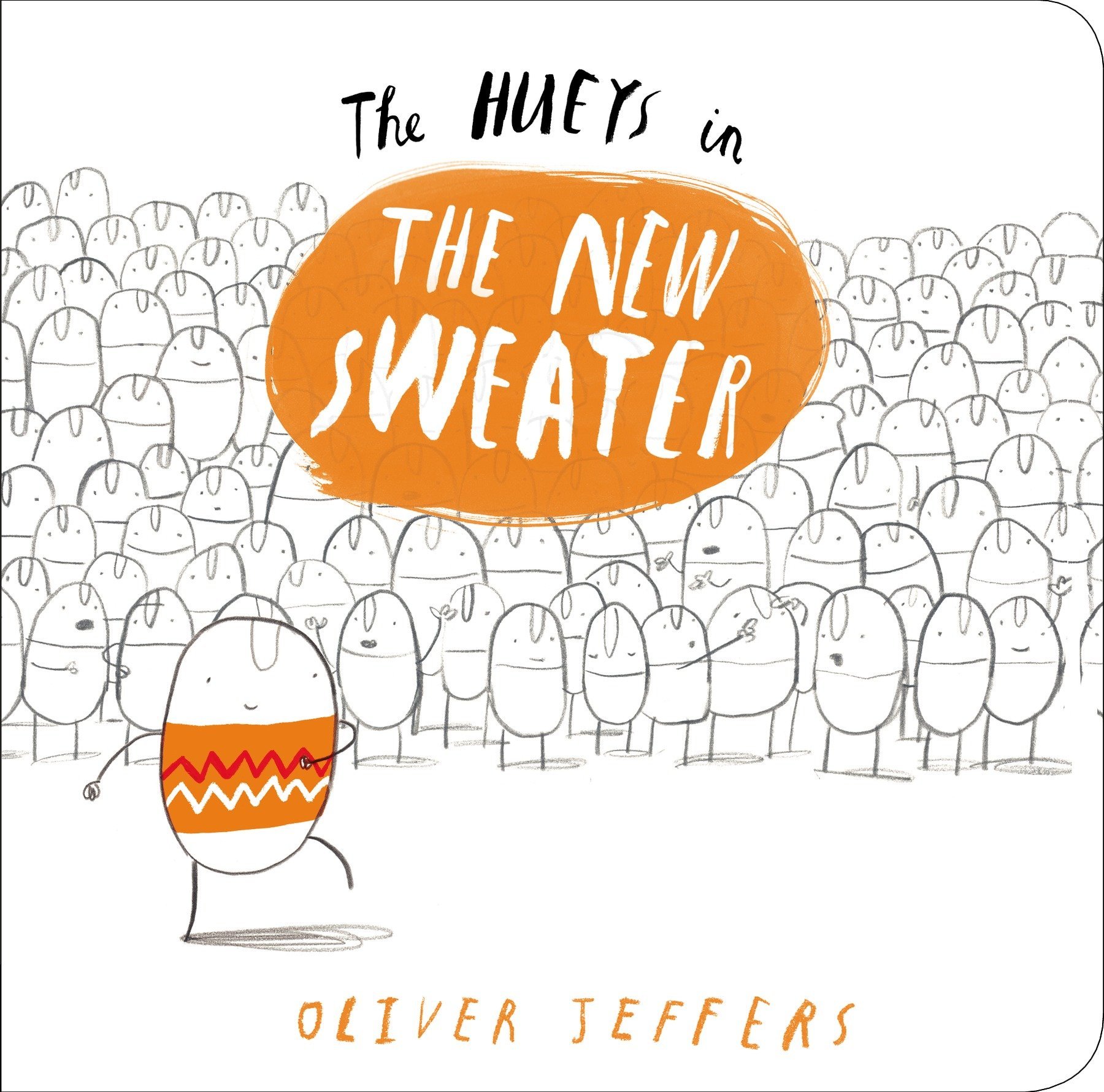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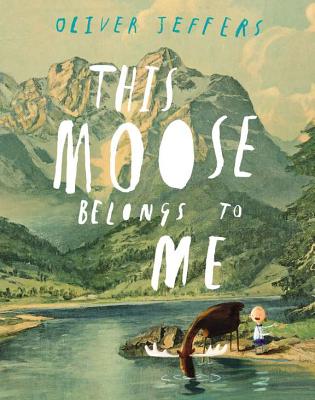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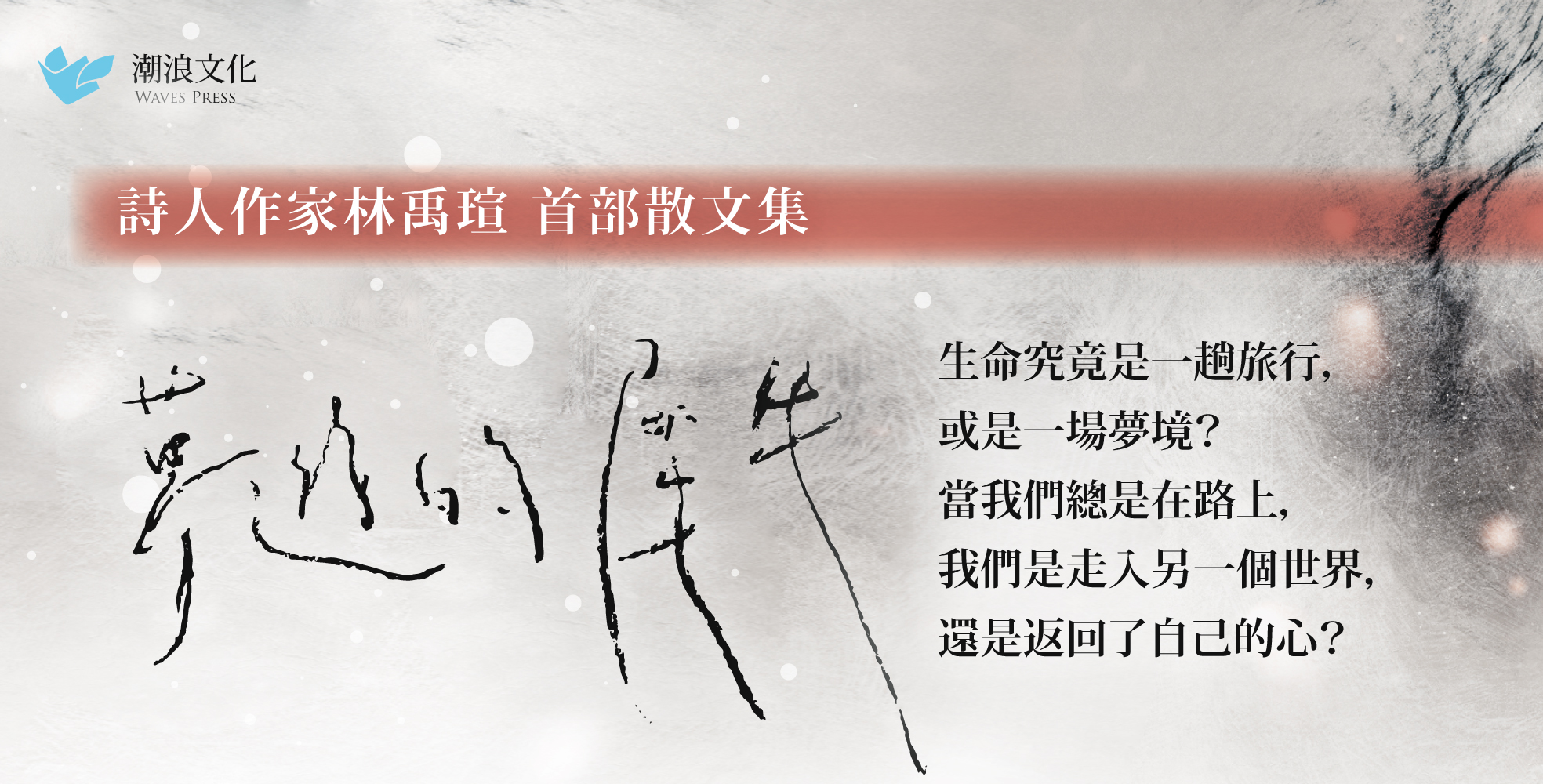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