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個女同性戀,我對異性戀女性的懷孕生產經驗非常感興趣,不只因為那是我選擇止步的陌生領域,也因為孕生是人與人之間能發生最親暱的關係,身體套疊著身體十個月,比交媾的嵌合更密切百倍。
閱讀《以我為器》,出身中醫家庭的李欣倫宛若巫女,召喚我進入她的女身,貼附她的胃囊與肚腹,感受紮實孕吐和勃然胎動。但巫女在現世也是學院老師,篇章間旁徵博引的論述,牽引魂魄稍稍抽離洶湧的感官經驗,旁岔至智識思考的明晰象限。學者精神結合巫女體質,李欣倫以文字建構出精確迷陣,引領讀者感受身體幽邃角落,同時對身體與社會文化環境的互動保持高度自覺。
痛並思索著
提到身體書寫,西方哲學傳統長期受身心二元論影響,男性心智被視為唯一理性思考的主體,身體經驗被貶抑忽略,直至上世紀哲學論述才又聚焦於肉身。但大眾文化再現女性身體時,仍然多以男性目光投射的客體形象出現,女性描述自身感性經驗的聲音依舊零落。
《以我為器》承襲了李欣倫對身體書寫的一貫關懷,由出嫁寫起,一直寫到懷孕、生產、育兒,省思女性肉身在婚姻體制內遭遇的規訓,並以知識女性所受的智識訓練與之辯證。在主題為生產過程的〈踩著我的痛點前進〉,作者近乎聲嘶力竭用盡各種意象描摹產痛,「扭轉、重擊、切割、打磨」,刀削斧斲、沸油淋焚皆不足以形容分娩的痛,語言逼近斷崖盡頭。然而歷經痛楚絞扭的百種狀態後,作者仍以文字掐準痛苦漫溢的感受,捕捉宮縮的頻率層次,產誕出母女動人的分離:「我永遠記得她從下體滑落出來時的感覺……成熟的熱帶瓜果,以她芬香的果肉摩擦產道,最初也是最終的路徑……」
從纖銳戳觸到地撼山搖的劇痛,李欣倫寫活了被視為裝載胎兒器皿的子宮,使身軀由被動承載的意象,轉為與疼痛搏鬥並創造生產的主體,強悍又柔韌的女體於她筆下冉冉而生。
時間肢解憂鬱母體
生產後接踵而來的哺乳與育兒等繁忙瑣事,也被李欣倫以滴水穿石的毅力記錄下來。〈月子中心十則〉與〈一日〉兩篇文章都以「時間」區隔文字段落,呈現母親時間被育兒雜務切割的碎裂感。在月子中心裡,嬰兒的需求取代母親的飢餓睏倦,成為丈量時間的刻度,女人下意識抹去自身的生理感受,異化為準點哺乳的母獸,在哺乳室成群聚集。過往個性女子消失了,憂鬱趁機冒芽,裹覆新手母親體膚,透不過氣。哺乳時凝視的卷曲花草壁紙,在她眼裡逐漸幻化出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小說〈黃壁紙〉般獸化的女體,童稚的甜美變色為鬼祟夢魘。
〈一日〉更是以長短斷句,表達照顧者生活節奏頻頻被打斷的倉促,句讀剁碎早餐時間,母女間千手千臂你丟我撿短兵相接。母親好不容易拾空閱讀,體味羅蘭巴特雋語浸潤身體的綿長,女兒便大搞破壞,擾亂母親與文字的親密接觸,將母親注意力轉移至巴特另一段關於薛西弗斯移石的話語。在此,李欣倫巧妙接合論述內容與不停被截斷的閱讀情境,暗喻孩童的情感與物質需求有如橫亙在薛西弗斯眼前的巨石,母親一次次移除,下一次仍面對同樣的障礙。重複的重複,斷裂的斷裂,即使卸除了胎兒,女子仍是不斷奉獻乳汁與愛的器皿,自我在紛亂雜沓的身體感中碎裂一地。
書寫做為一種救贖
不禁好奇,在消耗身心的母職生涯中,李欣倫是如何創作出這般壯麗緻密的文字?原來在繁重家務間,她瞄準襤褸時間每個孔隙,「見縫插針」地讀與寫。書寫助她褪除包覆在外的母親身分,還原本來面目,重新整合她身為創作者的心靈。李欣倫並未直指父權體制對母親的剝削,只以衣服被丟擲入洗衣機不由自主的高倍速旋轉,比喻母親在空轉的勞動中被擰乾抽空的自我,慢下來的書寫乃成為她對抗外在的方式,「它(書寫)對抗速度、質疑現狀並在每個理所當然的答案中顯出它的不服從」,讓她在茫然困頓中保持警醒懷疑。儘管李欣倫自言偷空寫作時經常「沒有心理準備和情感醞釀,無法重讀上文並根據脈絡」,她必然在瘋狂忙碌之際蓄積了極大的能量,才得以回到書桌前灌注力道至鍵盤,敲擊出充滿分量的淨實文句,如皮鞭抽刮出風。
一路凝視著往昔旅行、跑步和騎車的青春肢體,到孕期受限於隆起肚腹的不便身軀,與哺乳照護的母職勞動身體,李欣倫在產育過程中,迎來與過去身體經驗斷裂後、層剝分析痛楚的銳利知覺,進而體察到照護幼兒割裂的時間固然擾亂心象韻律,卻也賦予她打亂直線敘事方式,拼貼重組文本的能力。李欣倫原是一身分化為巫女與學者,各自修煉,在本書又匯合為一,感官經驗與知識話語交相滲濡,滋養出澎湃女性身體論述,彷彿撐拉開一個文字世界,創造出容納讀者探索的小宇宙,另一個抽象的器皿。
而我讀著異性戀女性艱辛習得的母職技藝,那些陌生又熟悉的血、黏液、乳汁與眼淚,赫然想起我也曾寄居母親的身體,天真無知地茁長,卻對母親未能形諸語言的痛癢酸麻一無所知。這世上有多少啞口的器皿?我嘗試著溯回我的源起之處,卻發現手中握著的臍帶,已脫落太久。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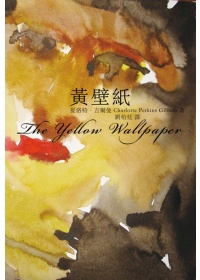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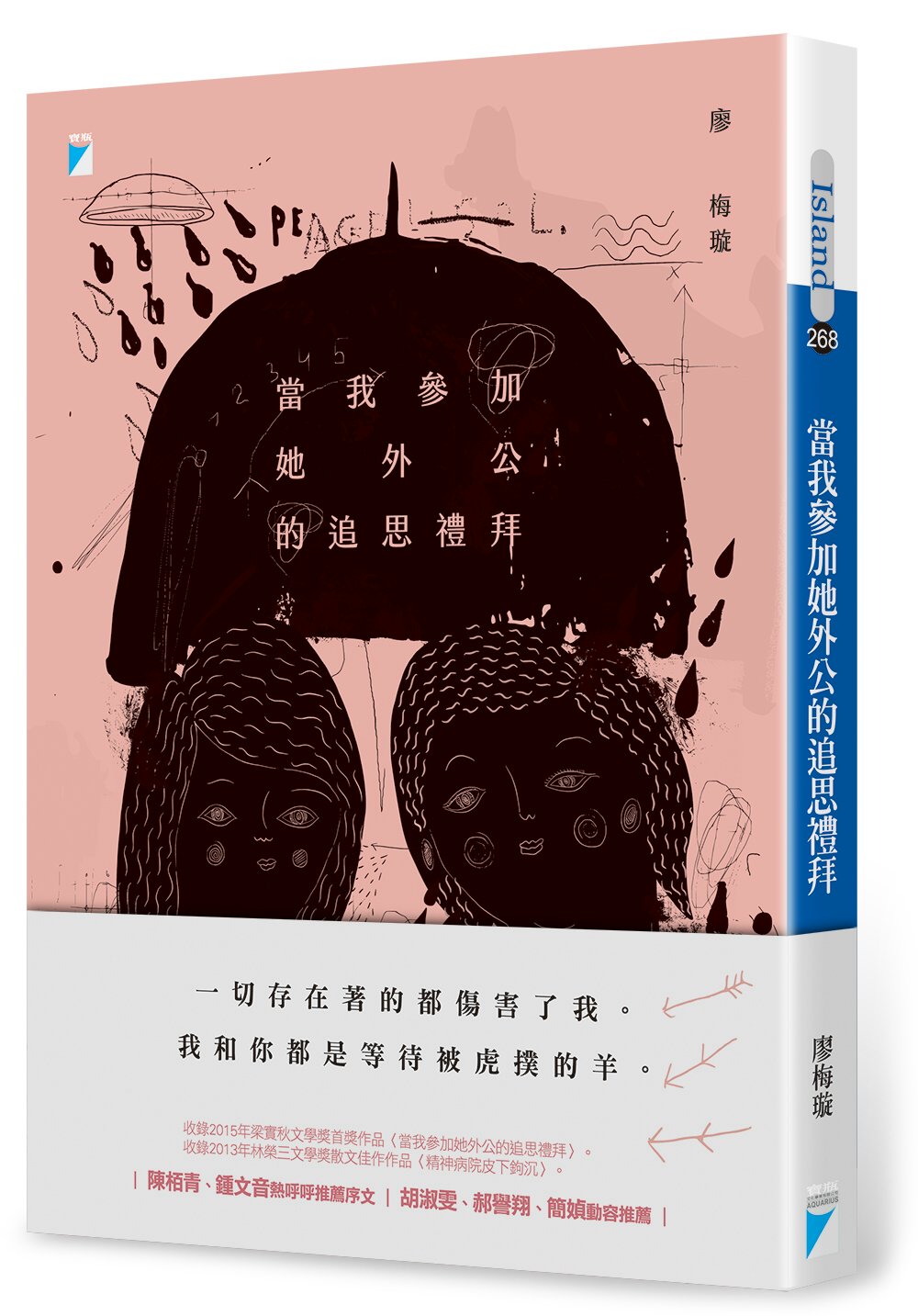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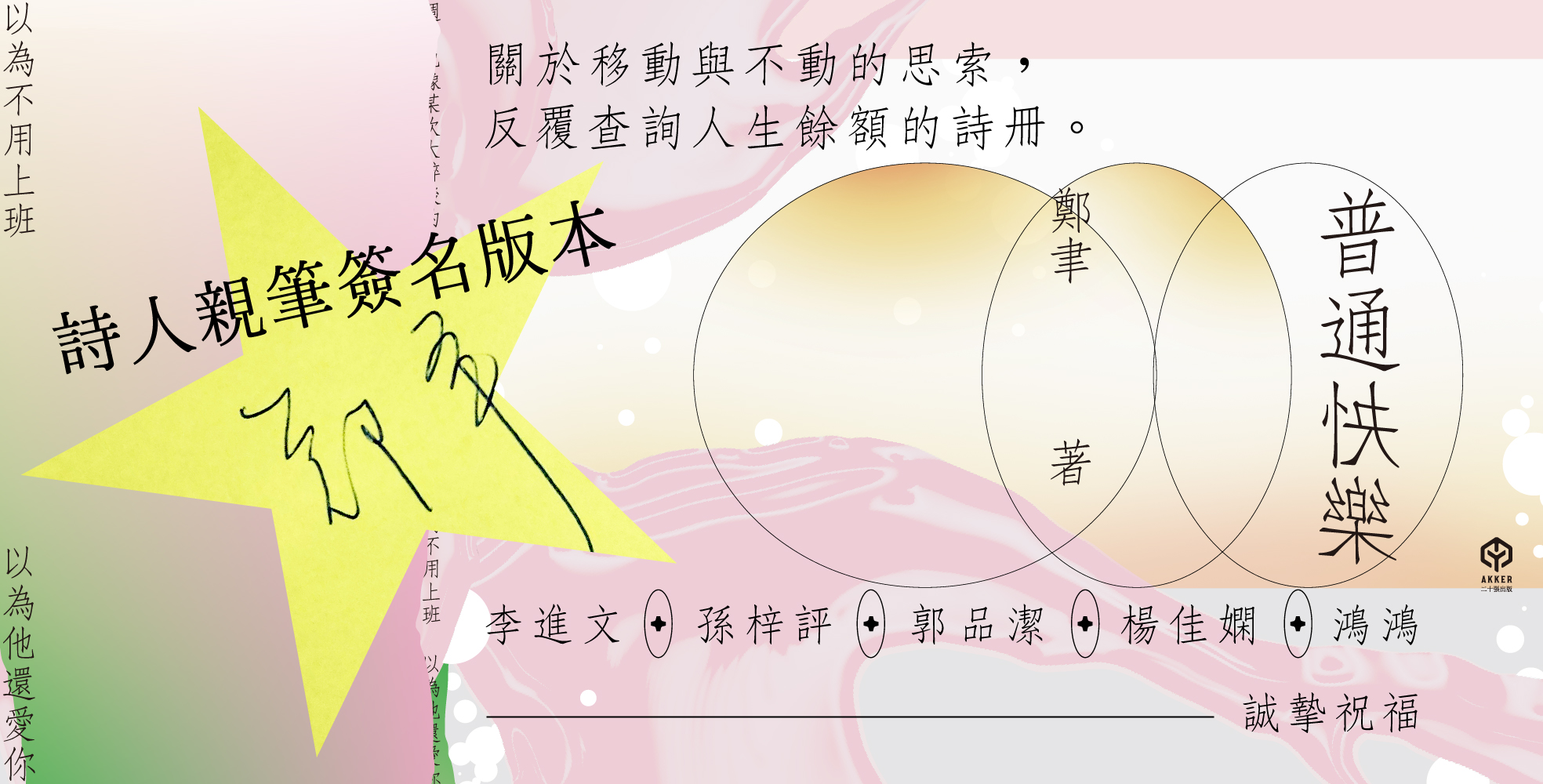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