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但以理)
隨著《賽德克.巴萊》越來越多的內容披露,似乎也出現了許多「霧社事件」的專家們提出意見,但這部電影的美術設計與考證,邱若龍當然也就是個專家,雖然他自己可能從來不這麼想。
從動手編繪「臺灣第一部原住民調查報告漫畫」《霧社事件》、拍攝《Gaya──1930年的霧社事件與賽德克族》紀錄片、擔任公視電視劇《風中緋櫻》美術設計、製作原住民神話故事的卡通動畫,到《賽德克.巴萊》。邱若龍這個名字,一直和「霧社事件」連結在一起,更特別的是,這還跨越了各種視覺表現形式,除了研究,那許多的文獻紀錄與田野調查,彷彿還有種為此紀錄為此發聲的動力。
他能為我們解釋很多事,而且總能用有趣而生動的方法。訪問當天他第一件為我們解釋的事情,是為什麼他沒能應我們請求,帶一把當年在霧社實際使用的番刀來。這原因當然不是他那如同博物館般豐富的工作室裡沒有這物件,只是當他要出門前,不知道樓上的阿伯發生了什麼事,大樓裡出現了大批警察。
我們腦中很難不浮現他頂著平頭戴著巨大圓黑膠框眼鏡,騎著打檔機車背著番刀,從他在台北的工作室出門,杵在街頭等紅燈的影像。
但當我們翻閱這位被以老師尊稱的邱若龍,為電影所繪的詳細美術設定手稿,物件的比例、構造乃至材質的細節,他隨時可以一絲不苟。當工作人員送來一個「作舊」的道具請他看,他對於刀鞘底的弧線就皺起了眉。但更不容易的是,他有的是瞭解越多越知道重點的包容與彈性。
有看到網路上的許多質疑與回應嗎?對於這,他很快舉了一個例。有人指正當時的日本警察配戴的是頸章、而非肩章。他知道這問題,除了這時代確實有日本警察是配肩章之外;更重要的理由是,在視覺上若用的是小小的頸章,畫面裡日本人學生軍警看起來會幾乎類同,除非要像老電影那般,在電影進行中打上「日本警察」,否則觀眾可能會看不懂。他又舉了一個例,片中有一場賽德克人與布農族人的戰鬥,但其實片中的布農部落位在今日的仁愛鄉,部落服飾與賽德克人極為相近,為了讓觀眾看懂,只好「把位置往南移一點」,讓他們換上靠近今日信義鄉的布農人服飾了。
「總要讓觀眾看得懂,才能繼續。」當時他完成漫畫《霧社事件》,這是個嚴肅的作品。他用較寫實的畫風,選擇了一個比較簡單的角度來說故事:將「德克達雅」(Tgdaya)群的莫那魯道當作英雄。但他也清楚地知道,這只是一個角度而已。無論是1950年代的抗日愛國意識,或者是當前積極建立本土意識的熱血,都只是當下的一種風潮,但曾經發生過的事情就在那裡,他一方面得紀錄、一方面得找個方法讓大家看得懂,並且繼續去瞭解。
最初只是個偶然,開始接觸賽德克朋友,甚至成了賽德克女婿,長住於春陽部落;後來也認識了霧社事件的重要人物(怎麼認識的?「我朋友的弟弟的太太的姑媽」)。她有三個名字,賽德克族名:娥賓.塔達歐、日本人要她改名高山初子、國民政府又改她名為高彩雲。——作為當事人與倖存者,她的口述歷史,曾改為小說與同名電視劇《風中緋櫻》。
身為漢人的他,與道澤群賽德克人成為親友、但又從德克達雅群的高山初子口中聽到了另一角度的霧社事件故事,這樣的位置讓他對於詮釋角度容易敏感,不再那麼容易去用不同立場,簡單地作出道德判斷。
他更在乎的,可能是賽德克文化本身,與周圍的歷史元素。所以他用自己的力量,為部落耆老作的口述歷史紀錄片,要在這些無盡的文化寶藏還未凋零之前,把「藏在老人衣櫃」裡的真實文化智慧盡量留存下來。

筆下莫那魯道嘴上煙斗,
他也能自己製作(攝影/但以理)
他也能自己製作(攝影/但以理)
「一部電影只是一部電影,一部電影不能解釋一段歷史、一個文化」作為《賽德克.巴萊》的考證與美術設計,他對於引發的爭議與討論並不反感,無論是族群的或者是考證細節上的,「就像是二戰的納粹,有這麼多各種媒材的作品出現,我們不該只相信單一的哪一部,也不用去擔心他的爭議,因為他被說出來了,也出現不同角度的各種詮釋,之中的仇恨有所化解、而歷史也被記得了,能繼續下去瞭解。」
「就像一個同心圓,對這段歷史與文化越瞭解熟悉的人,在上映前,一定反而對這部電影有些擔心與質疑,但我想對於霧社事件,《賽德克.巴萊》用大的架構和規模把故事說了出來,那些技術上困難的戰爭場面、時代場面,導演也已經建構出來了」他開玩笑地說,「這部電影裡可以有的爆炸刺激場面,應該可以讓觀眾看到飽,其他導演不用再苦惱要拍這些,之後就能有更多其他的角度,更精緻地說之中個別角色的故事。」
「其實也不只是霧社事件,還有很多屬於我們這塊土地上的故事我們可以講,畢竟我們不講,別人更不會來講吧?」他說這段話時的表情可是很認真,「而且啊,如果別人真的要拍,我們反而還更不放心吧?」

作為第一個知道OKAPI這動物的受訪對象,邱老師和兩隻OKAPI合照(攝影/但以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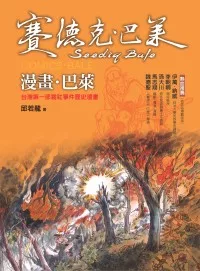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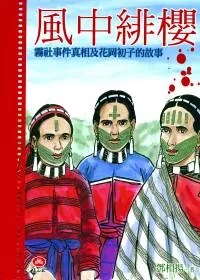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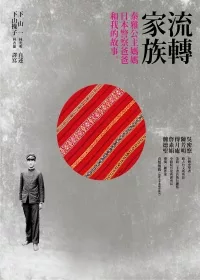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