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採訪=阿虎 攝影=但以理)
「大約小學四年級時,一次以遠洋船員為職的父親返家時,帶回一袋錢幣,其中有來自烏拉圭的錢幣。只是自己完全看不懂上面的文字,當下便立誓將來有一天,一定要看得懂。」懵懂卻堅定的想望,就此在小女孩的內心萌芽。她是葉淑吟,一名西班牙文譯者。
不知道能夠如此堅定的人有多少,但我相信,多數人回想起自己小時候的願望時,至多只是回味或嘲笑自己的無知。然而,葉淑吟卻是從一而終,期間或許曾經動搖,一如她提到,無論高中畢業後選填志願或者選修第二外國語言時,她都曾猶豫是否選讀德文,然而,那蟄伏體內多年的西文夢,總在最適當的時機清醒,並召喚她的靈魂。這般無悔,在大學時期前往德國自助旅行後,更是明確。「我沿著萊因河一路玩下來,或許因為文化的關係,我無論是到博物館參觀,或是走進科隆大教堂的禮拜堂,我也沒有覺得特別感動。那一年我十八歲,當下備感自己與德國性格的不協調。」
大學畢業之後,她完成心願前往烏拉圭,這時,錢幣上的文字她也認得了,也到了父親那艘遠洋漁船曾經停泊的港口。回來後,她讀卡洛斯.M.多明格茲《紙房子裡的人》,此際,經驗與回憶,不時觸動她的思緒。
有趣的是,在言談中,她提到烏拉圭,她笑著回憶與《十二神探俱樂部》作者帕布羅.桑帝斯的會面經過,她談到翻譯《聖草之書》時,那些墨西哥食譜的味道,獨缺同屬於西班牙語系的西班牙。只見眼前的她,斬釘截鐵的說出她心目中來自西班牙的文學創作,總在內戰與暴力之間遊走,往往閱讀之後,難以感同深受。而對於熱愛拉丁美洲文學,她也沒有過度誇張的論述,卻在娓娓道出時,表達了她對拉美文學的劇烈疼痛與不捨。她認為,來自拉丁美洲的人,個性熱情、自然、不矯情。當這般性格與國家經歷的創傷相互碰撞時,其所迸發綻放的火花更是炫爛的痛與解脫。例如在《蜘蛛女之吻》裡,作者馬努葉‧普易於其中所提及的傷口源於八零年代的白色恐怖,時間流逝,當作者再度回憶起這段過往,只覺那是一種歷史過程,他不過揭示內心一隅,而非刻意挖開歷史傷口,再次切割痛楚。當她品味作者如何描寫自身國家的傷口時,的確享受到一種猶如觀賞電影的精采,然掩卷之後,人們樂觀的性格與真實的創痛彼此衝撞、調和後的蕩漾,竟在她內心凝結成深刻的傷。
承襲著對拉丁美洲的熱愛及執著,往後翻譯的工作,彷彿是為了這片袤廣的異鄉而發聲。於是,她雖以來自西班牙的阿圖洛.貝雷茲-雷維特《南方女王》與《海圖迷蹤》啟程,卻往返於阿根廷的《謎樣的雙眼》與《十二神探俱樂部》、智利的《電影女孩》,以及近日出版、來自墨西哥的《聖草之書》。即便在台灣,西班牙文譯者顯得孤獨,她還是撐持下去。每每遇到翻譯上的困難,在乏人可以彼此討論的情況下,她仍盡力搜尋最佳解答,也因此她找到語言論壇「word reference」。在論壇裡,聚集了世界各地西語系國家的文字工作者,人們在此或提問、或討論、或解答,讓她在遇到難解之詞時,有了討論的平台。例如前一陣子她在翻譯時,遇到一個詞,若以中文直譯的話,意即「某個人是家中黑色的花」。由於這是作者自創的詞彙,為了深入其義,她便在論壇上提問,經過一番討論後,多數人皆同意,黑色的花意指家醜。而如今,論壇上來自各地西班牙語系國家的人們,已然成為她唯一討論的對象。
又或是2011年,她因為懷孕、生產,原本屬於正職之外的兼職翻譯時間更是壓縮。以前,她會利用午休時間、下班之後以及假日從事翻譯,未想接下來竟面臨了懷孕期間的體力挑戰以及生產後專注力無法集中的問題。為此,她以兩年的時間調整孩子與自己的作息,至今才能持續翻譯。或許在這段磨合期,她曾感到痛苦,但如今的她,反而認為翻譯不再是壓力,而是一種暫時的解脫、是一種日常的轉換,摒除了白天工作時必須處理的人與人之間的應對進退或生活雜質,唯留思考,她因而快樂。
翻譯即便有孤獨、有難耐的時刻,她仍期待更多後進有機會的話,能夠嘗試翻譯,前提是,必須大量閱讀,並從散文或短篇故事開始試譯,且虛心接受他人指教。必須大量閱讀的原因在於,西語區分布廣,不能僅單純接受來自特定國家的書,如此才能多方了解各地區的文化背景,不致在翻譯時犯錯。而散文或短篇小說的試譯,相對比長篇小說輕鬆。除此之外,試譯後,一定要請另一個人閱讀譯文,畢竟身在其中的自己,往往難以看出其中的差異與謬誤。

(攝影/但以理)
在與葉淑吟聊天的過程中,無論是她的談吐、她的表情,總不時流露出一股雲淡風輕的氣息。然後,我細細回想她的話,卻感受到她的無比堅定。時間回到她初次真實碰觸到拉丁美洲的土地,並與那些異鄉人相處的景象,她沒有後悔且肯定自己最初的選擇。接著,我的思緒不覺回溯得再久遠一些,我彷彿親眼見到那個四年級的小女孩,她站在我面前,她執著的眼神。我忽然意識到,或許,當時她便有了信仰,對於重新設定語言、對於拉丁美洲的信仰。
〔葉淑吟譯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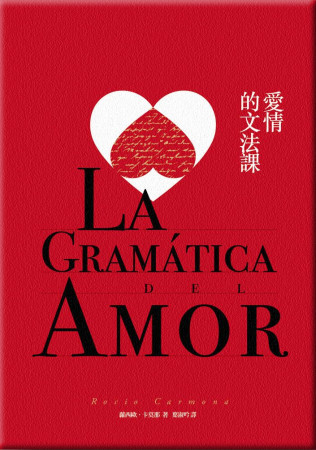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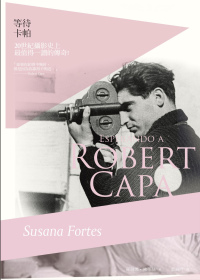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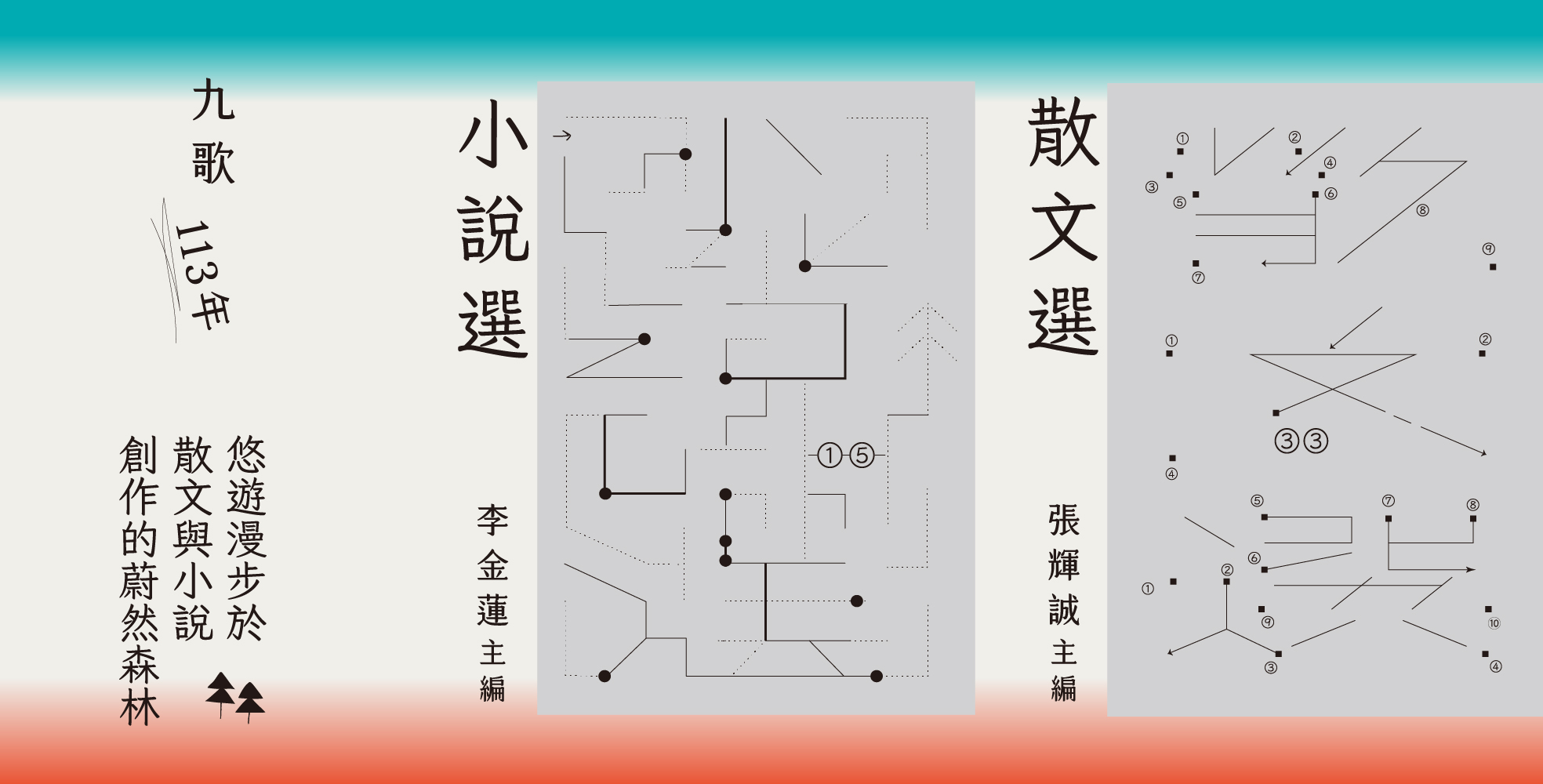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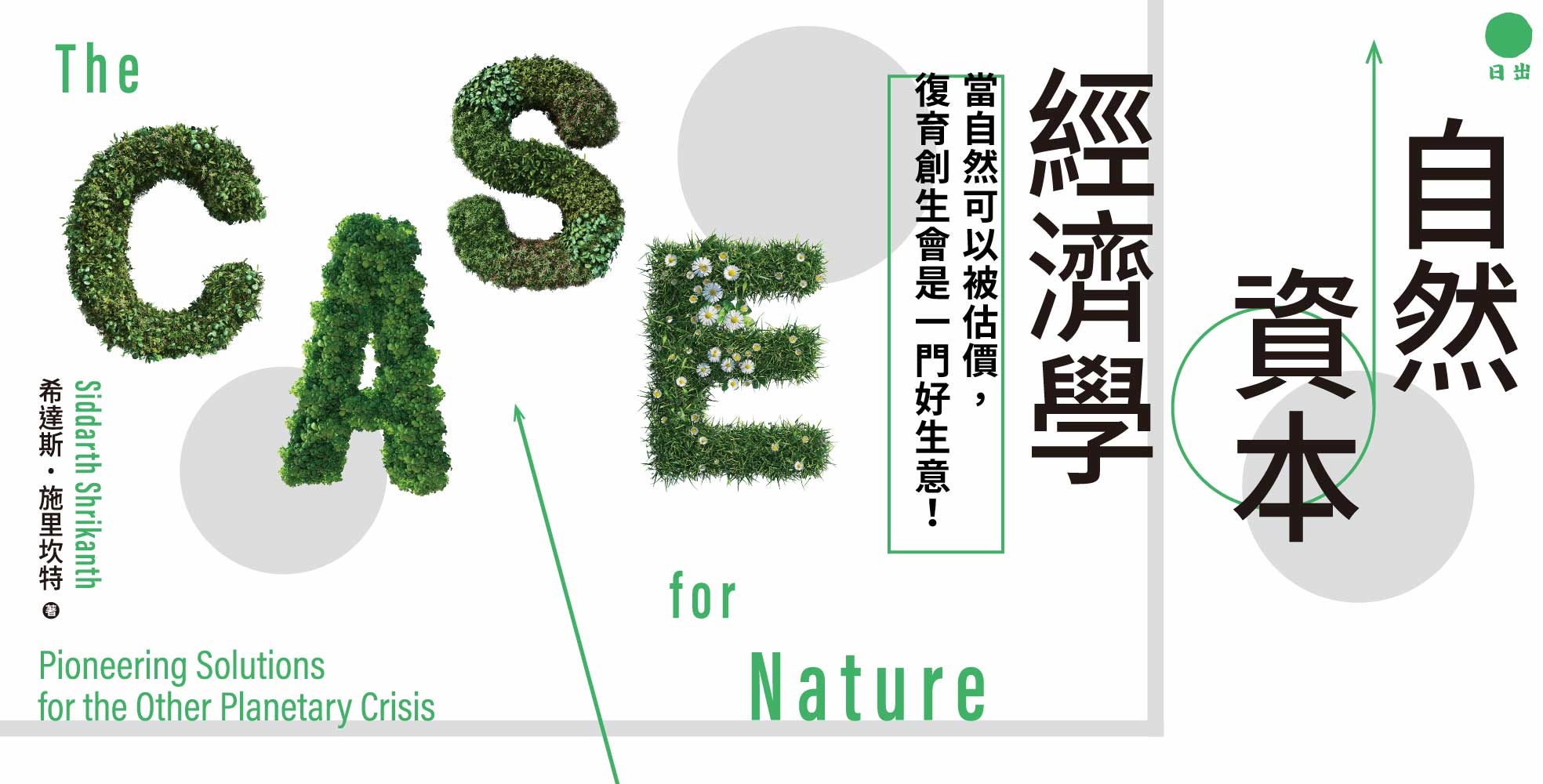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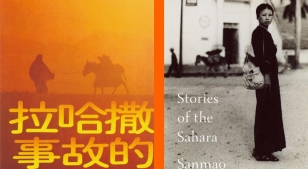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