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與明鳳英約在3月25日見面。3月18日,因「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起的太陽花學運方揭幕不久;3月24日凌晨,警方捨棄和平驅離方式,以暴力鎮壓前日晚上衝入行政院的學生與民眾……一幕幕的流血現場、一則則難以釐清的真相與謊言,在網路上不停流傳,種種餘波,要明鳳英此時此刻輕鬆談述她首部作品《一點一橫長》中所寫的種種童年眷村情事,氣氛上,似乎有點違和。
因感冒啞了嗓的明鳳英,以鍵盤上的雙手,或快速、或沉穩地,以文字替代語言,回答我們的問題。她的指尖不時顫抖,眼眶的紅潮隨著打出的每一字句浮起又褪去。她說,經過那一個黑暗而狂亂的週末,今天這個採訪,對她來說,一樣很是困難。
「大部分的人對自己身在歷史當中是沒有感覺的。生活在其中,往往看不見自己。當初我也是看不見的。」
明鳳英的父親是中國江西的客家人,隨著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娶了來自雲林台西鄉的台灣妻,一家子落腳在南台灣的山間眷村。明鳳英的童年,可說是台灣省籍交融過程的鮮活場景,也是被時間之手所翻去的,一頁似遠實近的歷史。
「我是客家跟本省的混合體,兩邊的情懷都有。但人總要有了『他者』,才會需要開始思考自己認知的文化是什麼。」明鳳英的『他者』,是在她1980年留學旅居美國、於漢學界執教20年、加以於中國往返工作十多年後,才開始出現。「起先是因為我父親去世,那時我住在上海,投了一篇回憶的文章給《東方早報》。登了之後,《上海壹週》的編輯來找我,問可不可以用這種很簡單的筆調書寫台灣。」
中國有一定的讀者群對台灣相當著迷,有一陣子為了促進兩岸和平往來,只要是台灣相關主題,都會刻意放寬。「在出版方面有一句話:『只要是台灣的,就一路開綠燈』。但是到2012年,這樣的空間又關門了。」明鳳英收到編輯給來一張紙,上面註明哪些字眼不要出現,起先只規定「國民黨」「陳水扁」等字詞,後來連「台灣」這個島名都不能有,只能直接寫「高雄」「鳳山」等地名;講到兩岸,「和平」二字也別出現,總之就是不要提這些。「中國的出版界每幾年就換風,時鬆時緊。所以他們就說,與其等他們來抓,不如我們先自己抓。」有個出版社發行一部台灣作家的作品,整個出版社都被封掉。「編輯就要我寫,說看會不會有人來抓。」明鳳英聞之不免失笑。
也因為明鳳英的筆調與陳述絲毫不泛政治,讓她平安地在中國持續書寫,也開啟了她回溯過往的機會,更為台灣眷村與這群流離他鄉的父執輩,在完全消失前得以留下幾抹記錄,逐漸集結出《一點一橫長》中的文字。

紀大偉在為明鳳英執筆的序文中寫:「她(明鳳英)的散文或隱或顯地強調這些散文有意促進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兩岸理解與和平——她這種心意,在台灣這邊,很容易被簡化的政治標籤或潔身自愛的心態所吞沒。」明鳳英說,她很清楚自己一定會被貼上標籤。「正因為我看到的台灣,是一個太乾淨、太沒有心機的地方,是台灣的養成,讓我可以保持一顆純淨的心靈,因此我更要用我的心靈來寫我看見的、我經歷的台灣。」畢竟時間對生命並不留情,每個人終會死去。「那活著的時候,就說一點真話吧。」
相較於同世代友輩的遭逢,明鳳英覺得自己既有幸運,也有遺憾。「我不在台灣的時候,正巧避開了省籍認知最為衝擊的階段,我從來不需面對群眾,解釋自己是芋頭還是蕃薯,不管走到哪裡,我都很清楚地認知,我就是台灣人。」也是這樣篤定的本質,讓她得以更無雜質地看進台灣深處。「好好壞壞加加減減,我們擁有一個很棒的台灣。即使有動盪的時候,都會過去。因為我們有一個從裡面長出來的、很好的底子,會慢慢把這些東西消化掉,一定會。」明鳳英微微泛紅的明亮雙眼中閃著堅定,「要有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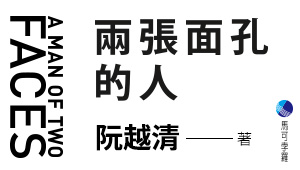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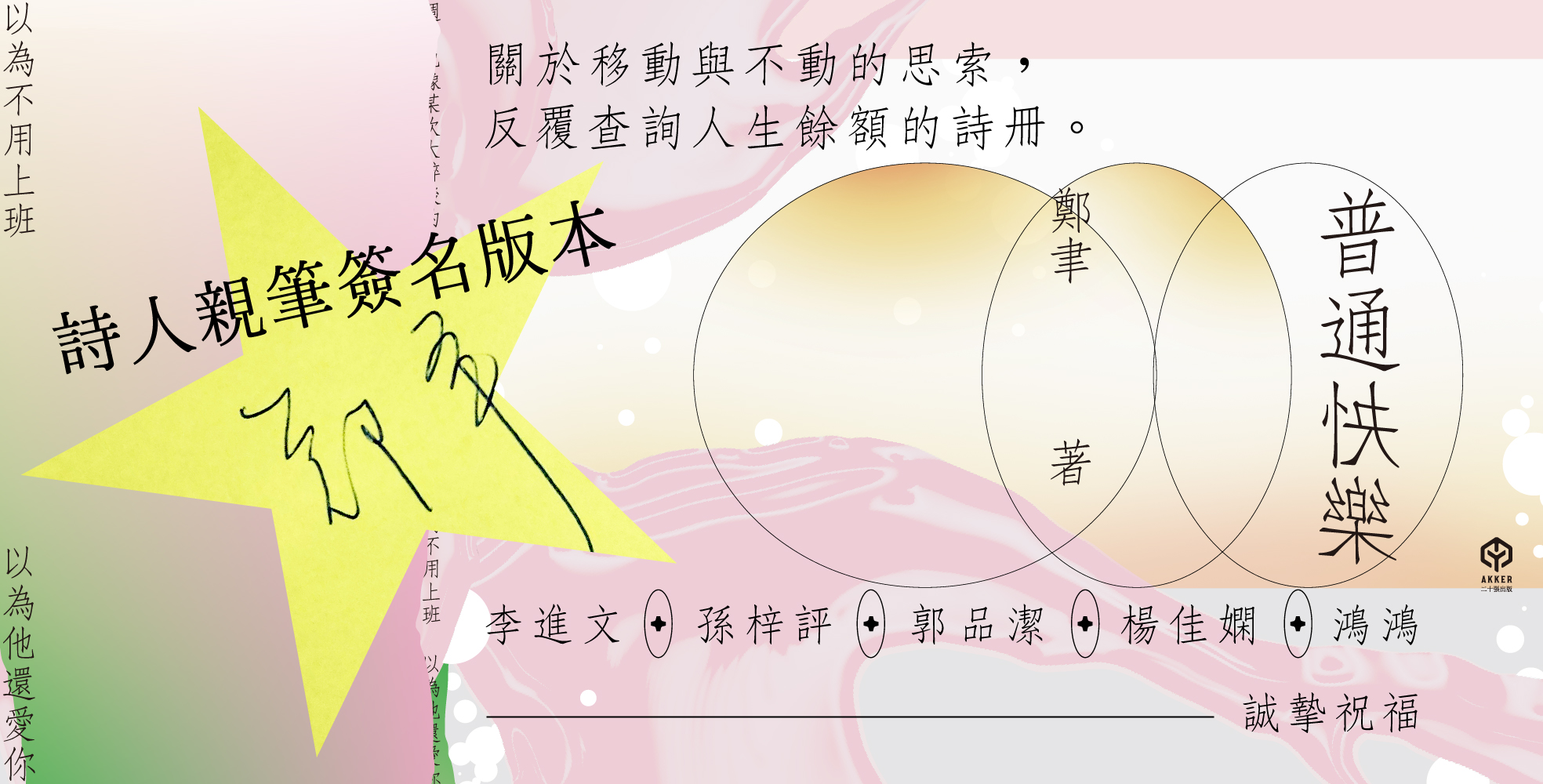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