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採訪當天,陳曉蕾拖著行李箱走進來,還沒說上話,就先給了好燦爛的微笑。她似乎有用不完的能量,抵達台灣才一天多一點,已經跑了好幾個行程,甚至還去看了台北101大樓的廚餘分類室,拍了許多受到完善處理的「精美」廢棄食物照,《剩食》已是她2011年的書,而她的關心仍在持續。
陳曉蕾從1993年開始記者生涯,後來選擇離開報社,踏上一條前途難測的道路,成為獨立記者,做自己想做的專題報導。她的書寫貼近生活,《香港正菜》寫香港農業、人與自然;《剩食》寫廚餘及資源浪費;《有米》寫人與食物的故事。日前才於香港書展推出的新作《死在香港》則挑戰禁忌,探討死亡及其延伸,她與採訪夥伴直面注視死亡,試圖從中尋找「好死」的各種方式。
「如果做了這本書,人生可以寫的書又少了一本。」陳曉蕾說,時間有限,議題無窮,這段時間拿來寫了這個題目,肯定有其他題目被暫時擱延,她說起尚在蒐集香港殯葬資料的階段,去聽了兩場殯葬講座,那些原本禁忌的,在這些場所變得百無禁忌,現場許多婆婆媽媽踴躍發問,每個人對死亡都充滿疑惑。「你完全知道該怎麼帶小孩,怎麼選奶粉、選學校、選各種東西,可是面臨死亡呢?」陳曉蕾這主題打動了,決定開筆。
殯葬議題牽涉的層面浩大,陳曉蕾找來蘇美智和周榕榕兩名記者協助,她則負責決定採訪範圍,擔起主編和作者工作。「死亡不能避免,但如果社會更人性化,很多痛苦是可以避免的。」她一開始先採訪喪親家屬,做殯儀資料的搜尋,隨著整本書的架構展開,從一件事又會發掘出更多不知道的事。然後,根據訪談的內容再向下挖,深入瞭解民間應對、醫療資源、官方政策,《死在香港》最後長成一部超過20萬字的作品,由她們三人分工完成:陳曉蕾十二萬字,周榕榕五萬字,蘇美智四萬字。上冊《見棺材》報導現代殯葬業的改革,訪問業界人士、學者、宗教領袖;下冊《流眼淚》則關注悲傷輔導,探討醫療和社福制度。
「我們現代人那麼努力去活著,如果對死亡卻連談都不談,到時該怎麼面對呢?」走訪眾多家庭,拜訪相關機構,衍生的枝節太多,這本書對陳曉蕾來說好像怎麼也寫不完;採訪的過程,更像是按下生命的快轉鍵,讓她一下子看見人生百態,例如去殯儀館採訪時,她看見子女來送父母一程,也看見白髮人送黑髮人,「我觀察到,死去孩子的,總比死去父母的難過。父母愛孩子,好像永遠比孩子愛父母多一點。」現實遠比想像殘忍,那些在採訪中遇見的真實事件,光是紀錄就會用上好多眼淚,為了不讓眼淚變得廉價,她在文字拿捏上格外謹慎,讓讀者在閱讀過程得到療癒。
「死亡只是個人的結束,對亡者的家人來說,死亡才剛開始。」書寫如此貼身的議題,也讓陳曉蕾回過頭思考自己的身後事,「如果我死的時候父母還在,會希望可以讓一些朋友、讀者來,幫忙安慰我的父母;如果到時候我父母已經不在了,那我什麼都不要做,直接燒掉,海葬就好。我有個阿姨就是海葬,家人想她時就去海邊,像一趟小旅行,不僅容易接近,心境也不一樣。」

與死亡的緊密接觸,也改變陳曉蕾的人生價值觀。當她想像自己面對死亡,發現最重要的還是父母,進而意識到對父母的愛。她甚至開始不太為錢擔心,她說生命就是一場旅行,「好像你換了一些英鎊去英國玩,錢在英國花掉就好。人生就是這樣,錢用完就好。」資料搜尋的過程中,她還意外發現香港有二、三十億港幣放在銀行沒人領,都是往生者留下的,她笑說,「所以我已經把自己有哪些銀行戶頭寫下來了。」
因為籌備《死在香港》,陳曉蕾重新檢查自己的人生,以「死亡」作為最終的判斷基準,更能排序出生命中各種事件的輕重緩急。「我喜歡寫東西,幸好已經在做這件事了,這樣就好。」密集寫稿的日子太累,她有次夢到已經寫完整篇稿子,夢太真實,早上六點鐘起床才發現什麼都沒有,讓她很是惱怒,「醒著在寫稿,睡覺也在寫稿,根本就沒有休息到!」後來她氣得發一封e-mail給編輯,說不要再寫書了。真的不寫嗎?她說,「至少休息個半年不要寫啦。」
作為獨立記者,必須要有調配工作與休息的能力。陳曉蕾習慣工作幾年,休息一年,節奏如同休耕,休息的時間拿來進修。第一次是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她去英國念文化研究;到了2005年,她專心念財經、全球化的書,發掘看世界的多元視角。那些日子她不寫作,單純用以學習,這期間獲得的養分,會支持她看得更深更遠。
儘管總是活力充沛,但如果用上二分法,陳曉蕾卻自認是悲觀的人,「但是我的正能量蠻大的。」她補充,「就像當記者很難、報館很討厭,可是不能因此不做我喜歡的東西。我知道這題材很困難,所以需要更多能量來做這件事。」
《死在香港》不只針對香港,而是每個人都需要面對的題目。陳曉蕾說,「我期望扭轉現代人對死亡的態度,不再那麼怕老、怕死;如果可以讓人知道,死亡不過是這樣,也許我們可以活得更勇敢。」
★ 陳曉蕾繼《死在香港》之後最新作品:
《香港好走 怎照顧?》、《香港好走 有選擇?》、《平安紙》,探討香港人晚期醫療和護理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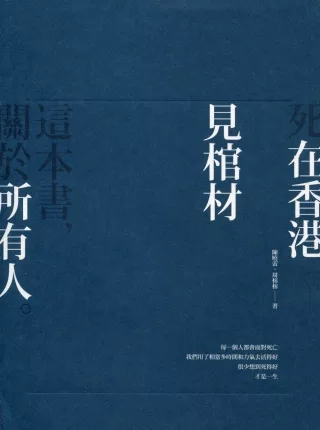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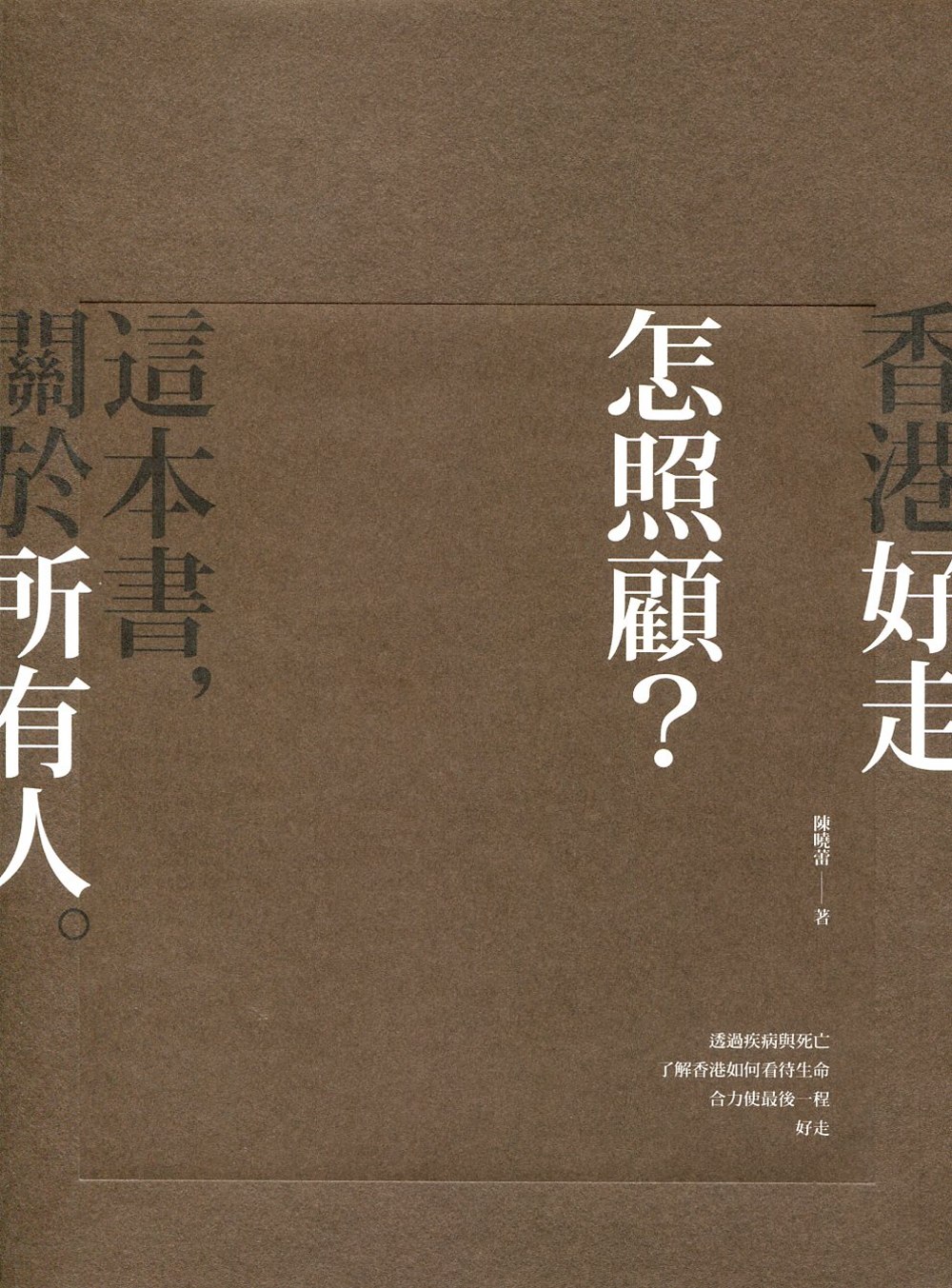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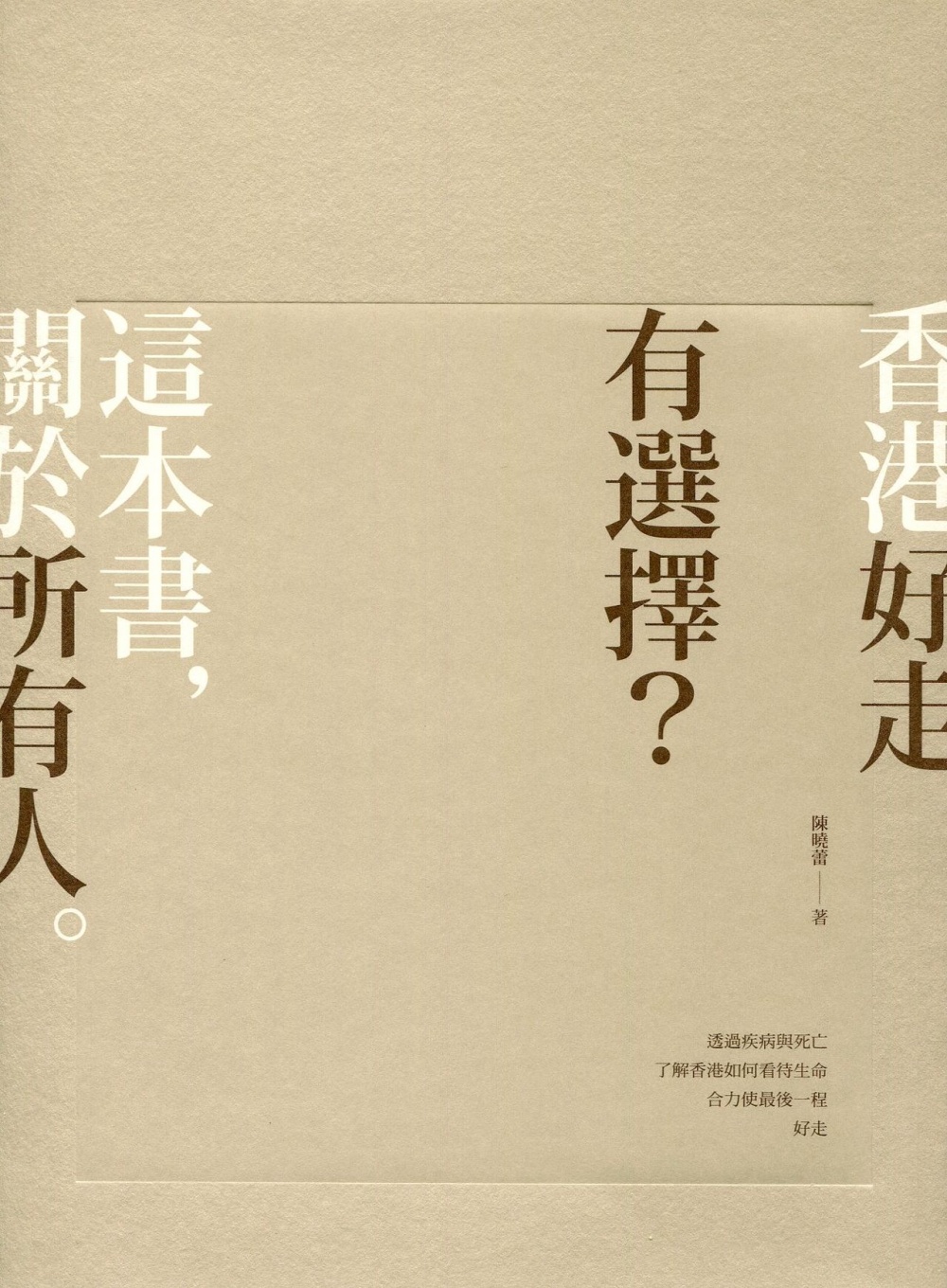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