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獨立作家、譯者、旅行者周成林(提供/大塊文化)
獨立作家、譯者、旅行者周成林(提供/大塊文化)
生於1966年初夏的周成林可說是與文化大革命一起落地,卻說十年文革對他影響不大,「那時很小,對這件事沒有意識,物質生活則深有體會,我們總是在窮困、無法吃飽的狀態,還被洗腦成世界上最幸福的兒童之一。」當時頻繁的集會批鬥、死刑犯遊街,對他不成恐懼,「因為生活就是這樣的。」
然而,幾乎糾纏半生的貧困生活及受政治影響的家庭背景,仍是他渴望訴說的故事,於是到了不惑之齡編織出散文集《考工記》,這書在2013年與梁鴻、李娟、野夫等人一起入圍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周成林也受到些許矚目。約莫也是這段時期,周成林開始出行東南亞和南亞,頻頻在雜誌報刊和網媒發表旅行散文,最終集成《跟緬甸火車一起跳舞》一書,並於日前在台灣出版。
原本他是計畫在中國出版的,但一個朋友讀了他的書稿後,順勢引介給大塊文化董事長郝明義,台灣因而成了這本書的出生地。周成林同時尋求簡體出版的管道,抱持著就算被刪節也該在中國出版的想望,把稿子給了過去合作的出版社,編輯邊看稿邊苦惱著那些該刪去的部分,「我寫緬甸那幾篇,只要牽涉到中國都得刪,關於西藏流亡政府和難民的也要刪,柬埔寨波布(Pol Pot)也不能放……」
波布也有事?
「因為中共禁止出版物談論赤柬波布那段歷史,這歷史和中共有關,那種血腥鎮壓會讓人聯想。」周成林口氣無奈,喃喃說著這樣刪來刪去,書就面目全非了,出簡體版幾乎是絕望。
《跟緬甸火車一起跳舞》由周成林在緬甸、柬埔寨、印度和尼泊爾的遊歷所構成,談緬甸難以避開中國,寫柬埔寨也得談波布,而作者行旅南亞更是為了理解西藏難民,換句話說,這本書幾乎全面地踩到審查的那條線。他還有一本原定今年6月在中國上市的文化隨筆,則因談及蘇聯和古拉格集中營而遭大規模刪除,能不能出都不知道,「這些文章前兩三年都在媒體上發表過,如今做為書卻無法通過審查,可見這兩年文化控制愈來愈緊,愈來愈嚴厲。」
或許是命運牽引,這個「文革之子」所到的國家和區域,或多或少和他的祖國有著類似的歷史和問題,即使周成林不斷強調人民和善、車況良好,只是更加凸顯普通老百姓的無奈。這些國家跟中國一樣向外開放,但枷鎖仍存在,不論是政治問題、媒體控制或言論審查,做為外國人,他只能記下那些抗議和變化,記下當地人的話語:「會變的,我們現在有了民主,會變的。」做為中國人,他有些羨慕。
但旅行前,周成林無法察覺這樣的內在呼應,更別說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去。他之所以選擇到這些與中國相鄰的地區,最直接和現實的因素就是考量預算和簽證──「中國人」這個身分不易獲取簽證,何況他還是個貧窮的中國人;另一個原因,則是出於對第三世界的興趣和關注,「全球化的衝擊對第三世界來說是最激烈的,變化也是最迅猛的,例如我第一次去緬甸恰巧遇到歐巴馬出訪,是一個希望與問題並存的時期。你去了那裡,就像中國告別毛澤東時代時,西方作家、記者蜂擁而來記錄那樣,是會讓寫作者激動且興奮的。」
周成林的成長階段也面臨中國社會的劇烈變革:隨毛澤東去世與文革結束而來的是經濟上的改革開放,不論怎麼變,僅有高中學歷的他即使流轉於各種工作間,仍不忘閱讀 。約莫1986-1989年,他滿20歲這幾年,這段中國最自由寬鬆的時期,為他們這代人帶來了民主人權的思想,過去習慣偷聽「敵台廣播」的周成林,也藉這時的「知識熱」明白了些什麼。但他自身的「改革開放」,則是八九民運後到澳門工作才開始,即使當時澳門還是殖民地,相較於中國仍是自由的,他在那裡瘋狂閱讀港台書報和外國作品,「我整個人都不一樣了。」
自由了5年,回到中國的周成林因文化氣場改變,有些呼吸困難。從事翻譯的他發現譯作被審查刪改,驚覺:「不能再看中文書了!」自學英文的他,這時徹底轉向英語世界,除了還得看看中國媒體新聞和社交網站了解中文的變化,基本上只讀英文 ,「這就像走上一條寬廣大道一樣,再也無法回頭了。」
為了解釋這個轉向,周成林寫過一篇題為〈在母語中流亡〉的文章(在審查制度下也被刪除),他以歷經種種險阻而後定居英國的匈牙利作家亞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的說法來反證自己:「從1940年起,我一直用英語寫作,用英語思考,讀的多半也是英語文學。語言不僅用來表達思想,也形成思想;採用一種新的語言,尤其對於作家,意味著他的思維模式、風格和趣味、態度和反應不知不覺漸漸轉變。簡而言之,他不僅獲得一種新的溝通手段,也獲得一種新的文化背景。」
科技的進步,也給了他這種人一個機會。每天,他會拿著平板電腦到戶外坐上半天,閱讀大量英文書報。他也開了微信公共號,無限制地放上自己的文章,找自己的讀者。問他為何在公共號上自稱「精神移民」?他答,「我想擺脫這個思想文化環境的限制,但身體上暫時沒辦法離開這個國家。所謂精神移民,對我來說就是盡量不讀中國出版的書籍,因為自己不完全以中國為寫作對象,每天的具體生活也能夠接觸到社會,我希望自己可以在精神上做到眼不見心不煩。」
即使只是閱讀《跟緬甸火車一起跳舞》,都能察覺這個中國「獨立」作家的「反動」,我擬的題綱就跟著「逆麟」。送出題綱那天剛好是6月4日,不免自我審查,擔心自己踩到線;幾天後,連線訪問頻被雜訊打斷,如機械那般疵疵聲,切碎了周成林慷慨激昂的話語,除了狼狽沒有別的形容。在費力的對話中,有個句子不斷出現,且特別清楚,「這問題太刁鑽了!」我的心都快要掉到地獄裡。後來才知道,因為他喜歡這些題目,答得開心,才給了「刁鑽」的稱讚。
例如這一題:為什麼你不斷強調自己是獨立作家、旅行者?
「強調獨立二字,對我來說,既是個人微弱的挑戰和蔑視,也是堅持與體制內的那些人產生本質區別。」周成林解釋,只有共產主義國家的作家是拿工資的,在國家編制內吃共產黨的飯成為共產黨的頭腦,他們活得不錯但精神上有些分裂,「中國境內完全不依附體制的獨立作家不多,敢於堅持高標準寫作準則的也不多。所謂高標準,是一個嚴肅寫作者最起碼的標準,就是不迴避任何敏感題材,頭腦沒有任何外在或自加的禁錮,不違背文學或寫作的良心,不說假話,敢於挑釁或挑戰固有觀念和傳統。」周成林認為,中國現在的言論和出版環境,並不鼓勵真正嚴肅的獨立寫作者,而他堅持這條路。
周成林的寫作與言論,讓人想到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而他確實也喜歡歐威爾,書中關於緬甸的篇章都帶上幾筆,甚至追隨他而行。
「歐威爾對我的影響,或者我對歐威爾的喜愛,遠遠早於我去緬甸旅行。大約七八年前,我用一段時間集中讀了他的大部分原著,才真正理解和喜愛這位作家。」他進一步解釋,《一九八四》寫的不只是極權主義當道的噩夢,也是對威權統治、排外心理和洗腦灌輸等人類愚行的最佳寫照,即使放在今天也沒過時,不論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脫歐公投以及當代中國,都讓人想到這本書。「歐威爾的正義感,反抗威權,同情弱者,自甘清貧,這些都對我觸動很大。當然包含他的寫作風格和語言對我的影響。」
擔任過緬甸殖民地警官的歐威爾,曾在〈殺象〉一文描述當地人對歐洲人的憎恨,將近90年後旅行該地的周成林,也發現自己的國家並不受歡迎。他在書中寫道:「在仰光不過幾天,我已感覺緬甸平民對中國的不置可否。或許出於禮貌,他們的不滿和敵意並未當面顯露。」敵意源於北京對緬甸軍政府的強力支持,而這兩個獨裁政權本質上並沒有分別。周成林為無力改變國籍而尷尬,幾乎一路隱瞞自己的身分,有時佯裝香港人,有時默認是日本人,而「偽裝身分」這件事成了日後每趟旅行的習慣。甚至,只要被誤認為當地人,他就得意開心,「我無所謂祖國,我在心理上距離當代中國漸行漸遠。」

仰光街頭書攤。(攝影/周成林 提供/大塊文化)
 位於卡塔的英國俱樂部舊址,歐威爾小說《緬甸歲月》場景所在。(攝影/周成林 提供/大塊文化)
位於卡塔的英國俱樂部舊址,歐威爾小說《緬甸歲月》場景所在。(攝影/周成林 提供/大塊文化)
為何必須得如此掩飾自己?他坦言,「一是尷尬,二是羞恥,因為我來自這個國家,而這個國家的這個政權又有很多不光彩的歷史記錄,更不要說它在當今自由世界的真正形象,我不想被人誤解,也不想隨時隨地跟人解釋自己的立場。」
畢竟,他的書寫並不背負著中國,而只關注著「在地」。「人對人的態度更有普遍意義,我想一方面突出在地,另一方面也把眼界放得更高一些。」周成林引述了英國作家毛姆的話:「旅行出門的時候不要把自己帶上。」
訪談中,周成林不時提到蘇聯或歐美作家,問他是否師法這些作家,他並不否認。在他的期望裡,做為作家應該要面對沉重且關懷的話題,「不一定每個作家都必須這樣,但我認為寫作就是一種抗議,一種關懷。如果我有足夠的條件,我在緬甸一定會去看難民,但苦於盤纏不夠,做不到,但至少我有這樣的企圖跟眼光。這就是我以為寫作要達到的境界。」
周成林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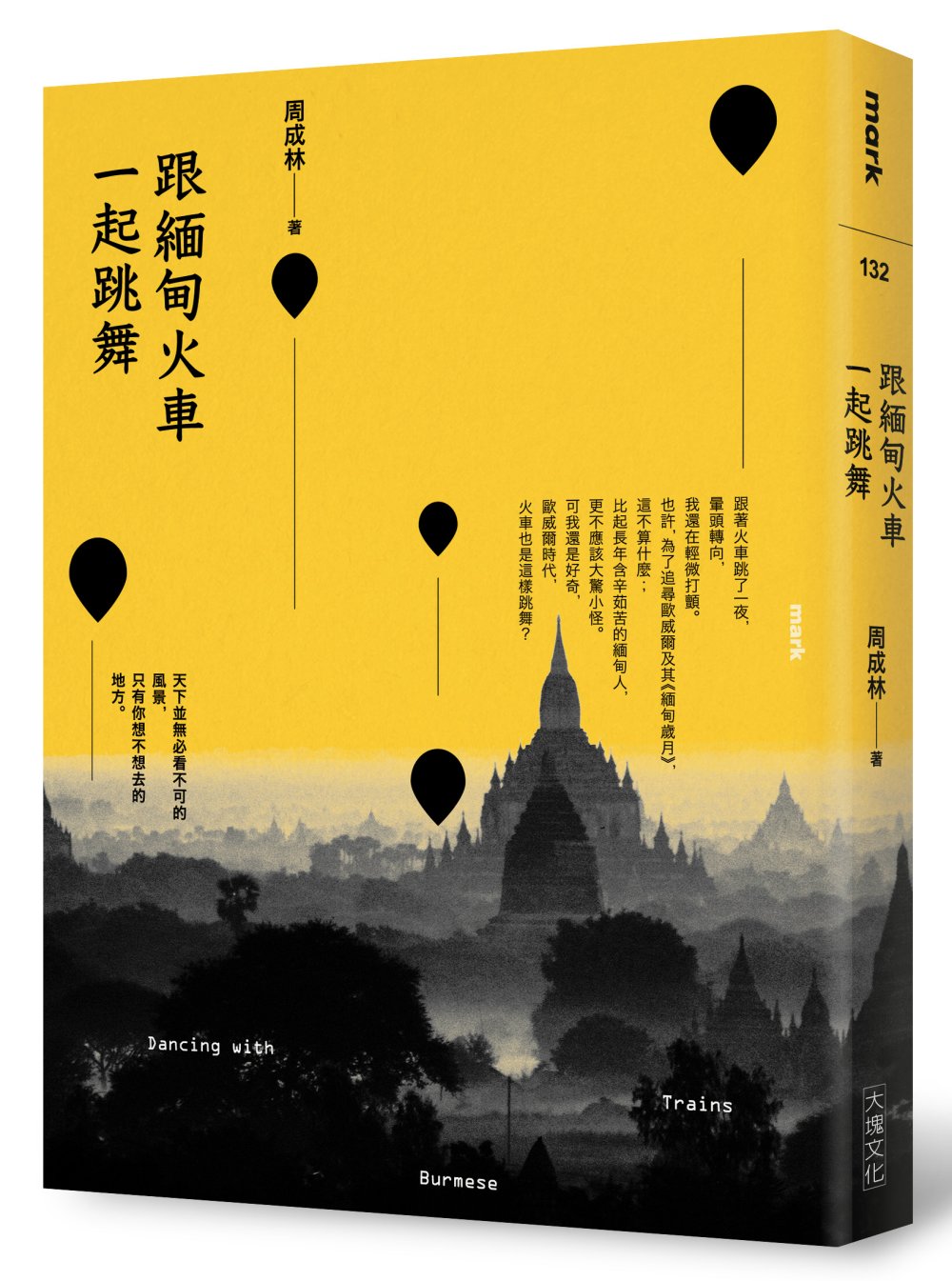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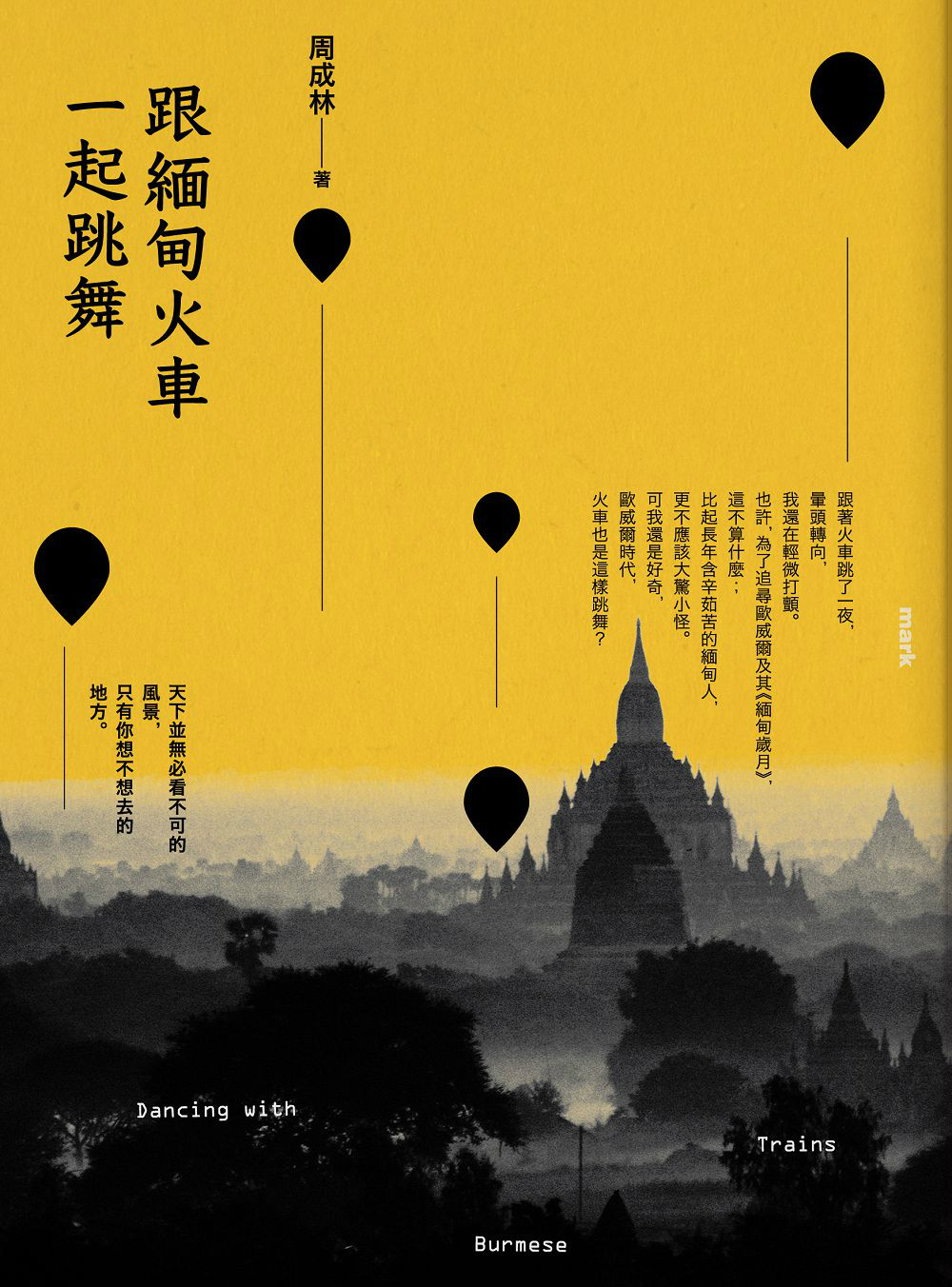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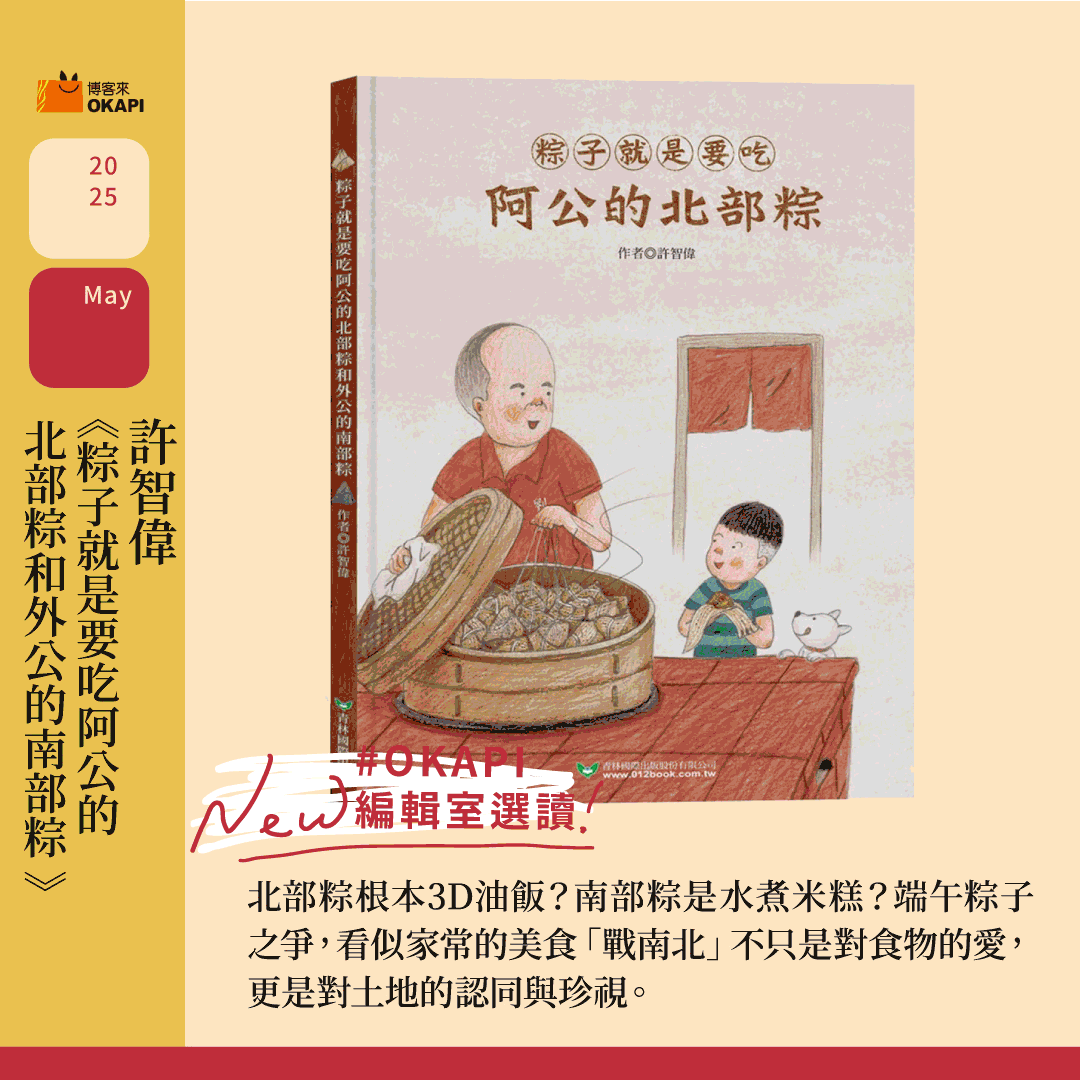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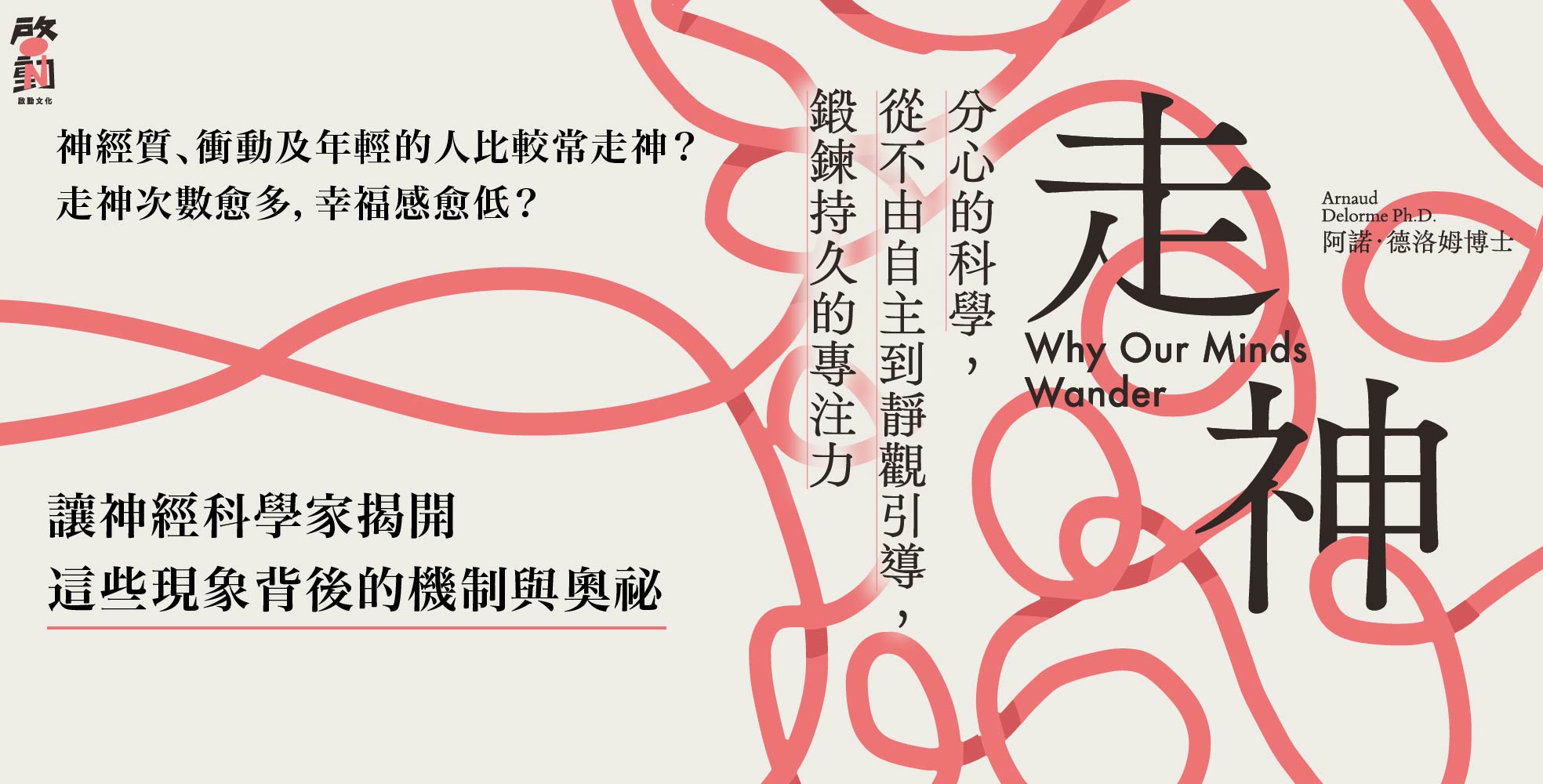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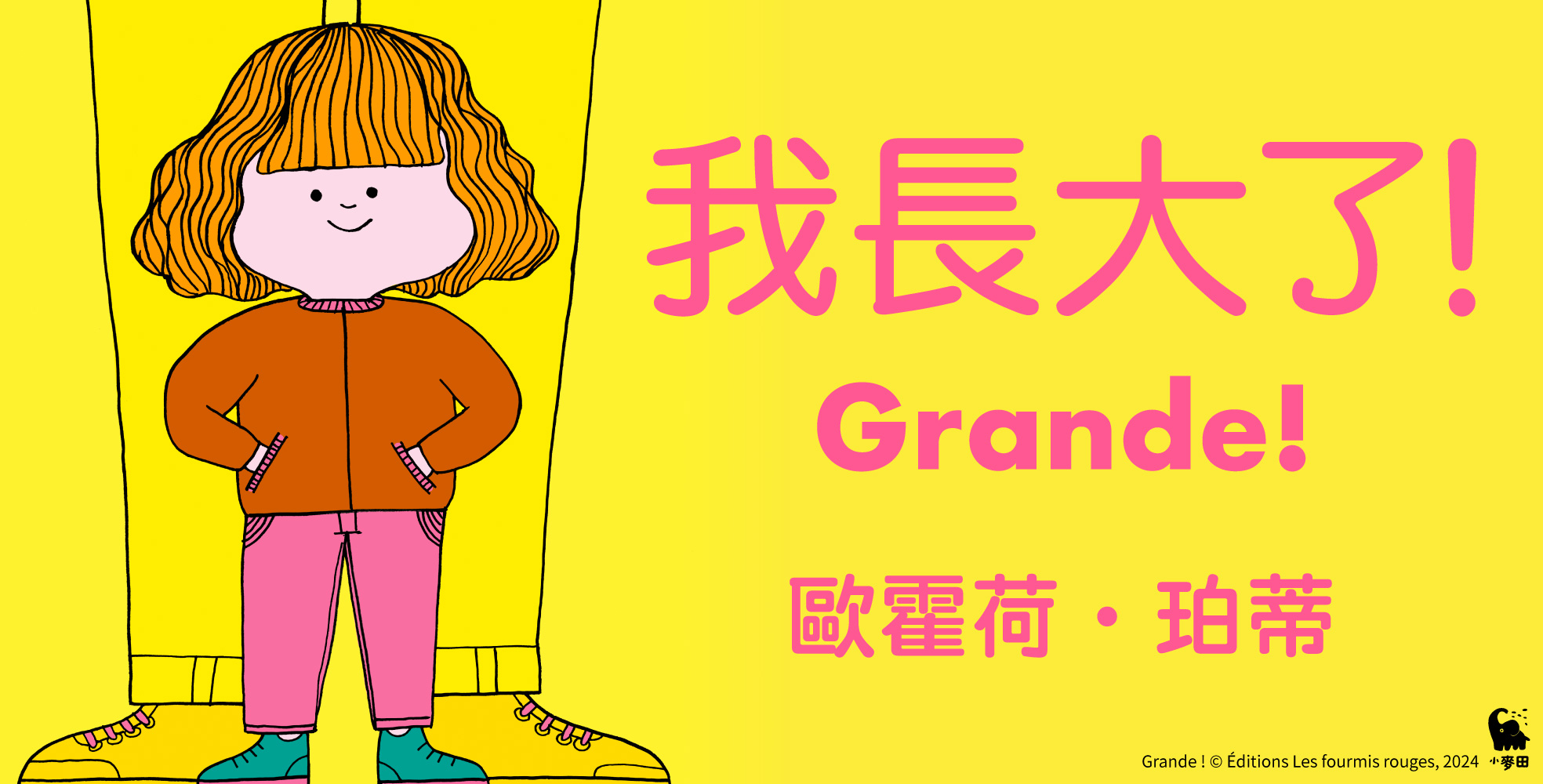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