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坂幸太郎的推理作品《不然你搬去火星啊?》是一本很奇特的書,文友提子墨認為這是 以市井小民的角度,仰望強權政體與極權制度所帶給他們的傷害與恐懼,作者把我們自以為遠在天邊,又事不關己的歐美與中東國際動亂局勢,巧妙地揉進書中的日本宮城縣與千葉縣。這是一種看法,但我個人倒認為這是作者對於日本目前政治態勢持續右傾的一種憂心預言!書裡警察的行徑已經和二次大戰爆發前後的「特高」警察如出一轍,極為類似的情景也可以在宮部美幸的《蒲生邸事件》等書中看到,怪不得伊坂太郎會憂心忡忡地提出警示。
作家把自己的看法或預言以小說形式表達並不少見,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的《1984》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故事不僅僅適用於共產獨裁國家,也適用於一些「所謂的」民主國家;而他的另一部作品《動物農莊》裡的情景,更是讓一些對人民鼓吹正義的道貌岸然的革命者徹底現形,將他們真正的嘴臉打得腫腫的。戒嚴時期的台灣,這本書還被譽為對共產黨的挑戰批判書,何嘗不是對蔣家政權的莫大諷刺?
推理作家因作品裡常常描寫關於殺人的情節,在罪與罰的相對情形下,死刑的存廢就成了推理作家的關心焦點。高野和明《十三階梯》、島田莊司《淚流不止》和東野圭吾《空洞十字架》就不約而同地探討這個問題。而作家們各自提出的論點都有其說服力,幾乎是一種文以載道的精神。例如島田莊司的《淚流不止》,竟然整整花了八十萬字來編寫一個故事在討論這個問題,這幾乎是一般博士論文的六倍篇幅!但是,如果讀者可以繼續深究下去,這些推理作家並不一定是「廢除死刑」的支持者,他們強調的是有可能發生冤、假、錯案,如果執行死刑,人死終究不能復生,一旦後來發現是冤案,將無從補救起,對於罪與罰的公平正義性也是莫大的傷害。可見推理作家們主要害怕的是偵查錯誤而造成了冤案,至於是不是真的因為其他理由而贊成廢死,應該還在兩可之間吧。
正因為對於社會議題的關注,同時幫助了推理作家開闢出許多新的思考路徑,日本社會派推理便因此誕生。松本清張剛開始寫的《零的焦點》和森村誠一《人性的證明》,就指明了美軍進駐日本之後引發的社會問題;在《日本的黑霧》中,松本清張更是直指GHQ和日本政府的勾結弊端,那已經近乎直接的批判,只是用推理小說來加以呈現而已。這些作者把社會上繁榮的外表掀開,讓讀者知道美麗的皮毛底下只是可悲的骨頭,用批判的眼光讓讀者產生共鳴,推理小說不再只是休閒娛樂的膚淺作品。
前人已經把路打開,後人就更能把自己的意念用故事來說給讀者聽,這種情形不吝是另類的文以載道了。中山七里就用《連續殺人鬼青蛙男》這本精采的小說,來挑戰日本刑法三十九條有關「精神異常」殺人犯的問題;《開膛手傑克的告白》則是直指當今社會「器官移植」問題的盲點。這類作品在歐美並不多見,應是文化差異的問題,但在台灣則不然,例如臥斧的《碎夢大道》就是一本很有野心的作品,以冷酷派的筆法直指都更抗爭、政治陰謀的黑暗面。知言的《正義・逆位》讓我們思考所謂「正義」的真正意義;天地無限的《第四名被害者》則是把公共工程弊病和媒體操控輿論批得體無完膚。冷言的《輻射人》既有對核能發電的疑慮,描述公家單位的顢頇無能,甚至憂心核能外洩的重大危害,已經不只是文以載道,更是大膽預言了。
有人說,「歷史除了人名是真的,之外都是假的;小說則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推理小說家並非只是憑空想像的夢囈者,更像是告訴你已經發生或即將發生的示警人,那麼,你怎能不愛推理小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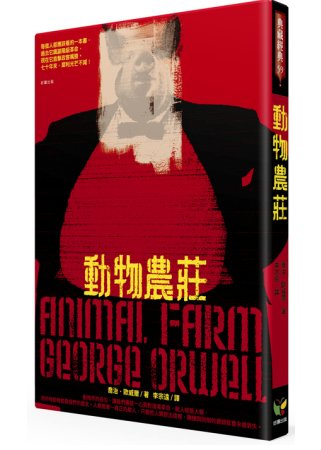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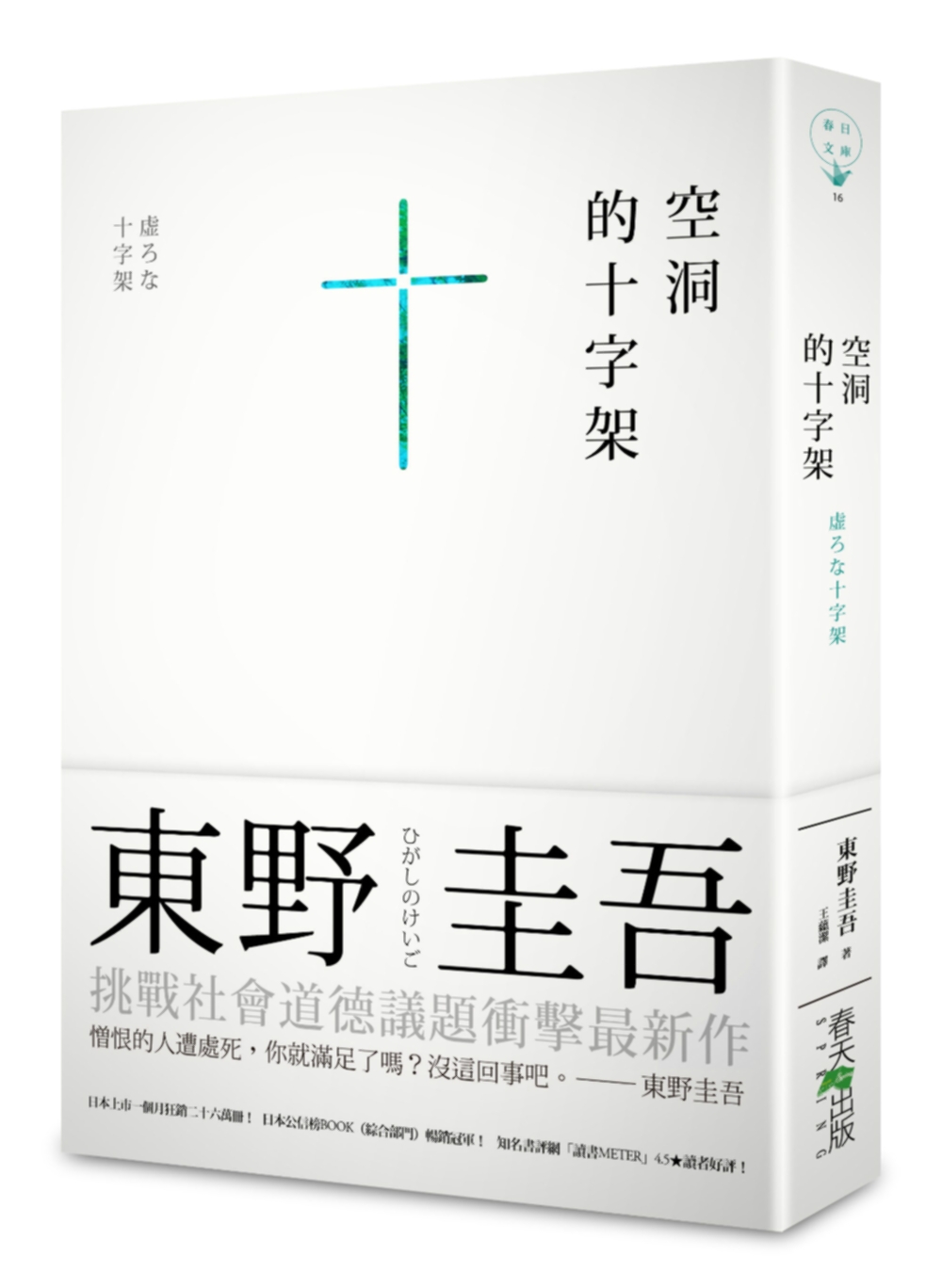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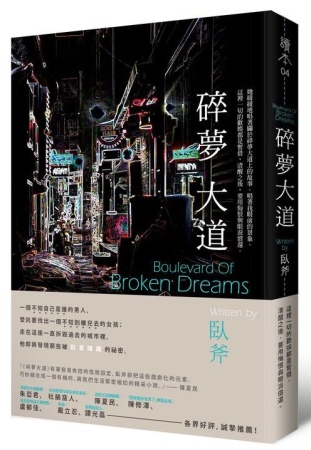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