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陳佩芸)
(攝影/陳佩芸)
12年後,短篇小說《縫》依然有股血的味道,陳舊,帶點鏽。
《縫》為小說家張耀升於2003年初出茅廬之作,一出手便引來眾人目光,筆下世界看似陰冷晦暗,卻緊扣人性細處,探鑽幽微心理。然而小說絕版多時,時有讀者詢問、出版社洽談重新出版,張耀升卻幾番猶豫。
最後讓他下定決心的關鍵,是小說家曹麗娟和出版人陳蕙慧。「幾年前,曹麗娟重出《童女之舞》,我非常喜歡她的書,重看後感動不減反增,因此也重新思考再出《縫》的可能。因為蕙慧姐的關係,選擇群星文化,我相信這群編輯的觀點能做出超乎我能力所及的作品。」
張耀升一直是文學獎常客,在中興外文就讀期間,因看了袁哲生的《寂寞的遊戲》深受啟發,他寫下第一篇短篇小說〈伊卡勒斯〉。「《寂寞的遊戲》讓我看到,你得真的對世界有話可說,而不只是站到舞台上大聲嚷嚷。」這些語言,通常來自情感,但得轉化成讀者也聽得懂的故事,〈伊卡勒斯〉表面上寫同性之愛的進退失據,創作初衷則來自於他和奶奶的情感,「當兵時,奶奶過世,我無法休假見她最後一面,所以有很大的生死隔閡感,我把它轉化成完全不同的故事,只保留內心的情感。」〈伊卡勒斯〉獲得全國學生文學獎大專小說第一名,也讓他自此開始認真寫作。
《縫》後又隔8年,他才出版第一本長篇《彼岸的女人》。他依然秉持有話可說的初衷,寫作,但不一定出版。依據中興大學台文所副教授陳國偉的說法,《縫》裡的小說有一種透明度,沒有太多作者主觀,呈現的是一個看似冷靜的世界。針對新版《縫》,張耀升從這幾年的作品中挑出四篇與舊版《縫》調性相合的作品,補強原有題材。其中,成為收尾之作的〈鼠〉特別引人掛念,小說敘寫日據時期一位底層女人在戰事下走投無路的處境,文筆淡漠,情節不疾不徐,卻將讀者緩緩逼入死境。
2006年,張耀升因編劇工作進行田野調查時,聽聞「吃老鼠的孕婦會生下像老鼠的小孩」的傳說受到震撼,2010年寫下短篇〈鼠〉,獲得台南縣文學獎後卻一直深鎖;他想把這篇收入新版《縫》,卻被編輯反映「看了令人不舒服」,他這才意識到自己寫作上的心理狀態,「寫《縫》時我還很單純,很多邪惡的事都是想像而來,沒遇過真正的壞人。出社會後,經歷一些事,遇到一些人,讓我對人有新的體驗。」經編輯提醒,張耀升發現,在此後的寫作中,敘事者不再同情主角的遭遇,「《彼岸的女人》就有這種現象,但我一直沒發現自己有此轉變。」
如夢初醒,他決定修改〈鼠〉,讓敘事者陪在女主角身邊,感受其痛苦與暫時的解救,呈現出一種同理心。「我有段時間在創作上失去對人的同情。過去,我的作品要改編成影像時,製片總說『太黑暗,要溫情有出路』,尋找溫情與出路的改編方式通常失敗,我不知道如何從作品中找出路。」但改寫〈鼠〉的過程中他發現,「不需要給溫暖給出路,只要改變敘事者的『態度』。」
 (攝影/陳佩芸)
(攝影/陳佩芸)
12年來,〈縫〉曾被改編為公視人生劇展《我的阿嬤是鬼》,也被張耀升自己改為動畫短片《縫》。書中的〈鮮肉餅〉則被改編為公視學生劇展同名作品,〈藍色項圈〉更有多達四、五個改編劇本。這幾年,張耀升漸漸將創作重心遷往影視圈,寫劇本,也拍片,更演戲。「我們可能覺得文學讀者跑掉了,但他們能跑去哪?文學人口的比例應該不會差很多,除非人類基因都換了嘛。愛看電影的人並沒有變少,所以我嘗試把小說拍成影像,讓兩邊的受眾有交流,互相影響。」他發現,電影圈非常缺故事,製片人普遍不讀台灣小說,甚至會問張大春是哪個朝代的人。於是,他乾脆從自己的作品做起。
編劇工作讓他溫飽,也讓他發現台灣小說的致命傷,「寫小說的收入太低,根本沒有本錢做田野調查,這問題很嚴重,所以我很鼓勵台灣小說家都來當編劇。」他以畢飛宇小說《推拿》為例,作者在盲人按摩院觀察了一年多,才能如此深入盲人的生命,帶讀者看到這麼多細節,「但一年沒收入,誰辦得到?台灣作家為什麼無法寫出《推拿》這樣的作品?不是我們文筆差或小說技術不好,或人文關懷不夠深刻,是我們沒辦法花一年只做這件事。」
相較之下,田野調查是編劇工作的起手式。他說,電影公司會要求寫作之前做田調,也會付薪資,「他們需要真的可以拍出來的東西,拍片是很真實的挑戰,你無法避開細節。」如果寫作就是有話想說,台灣文壇其實還有太多話沒說出口,張耀升說,「台灣有很多值得寫的小說題材,比如大埔張藥房或RCA汙染事件,這麼多不公不義之事卻沒人寫,在日本早就變成社會派的推理小說了。」
能寫、能演、能導,跨界尋找各種表達方式,張耀升對於這世界能說的話,也許比他想像的還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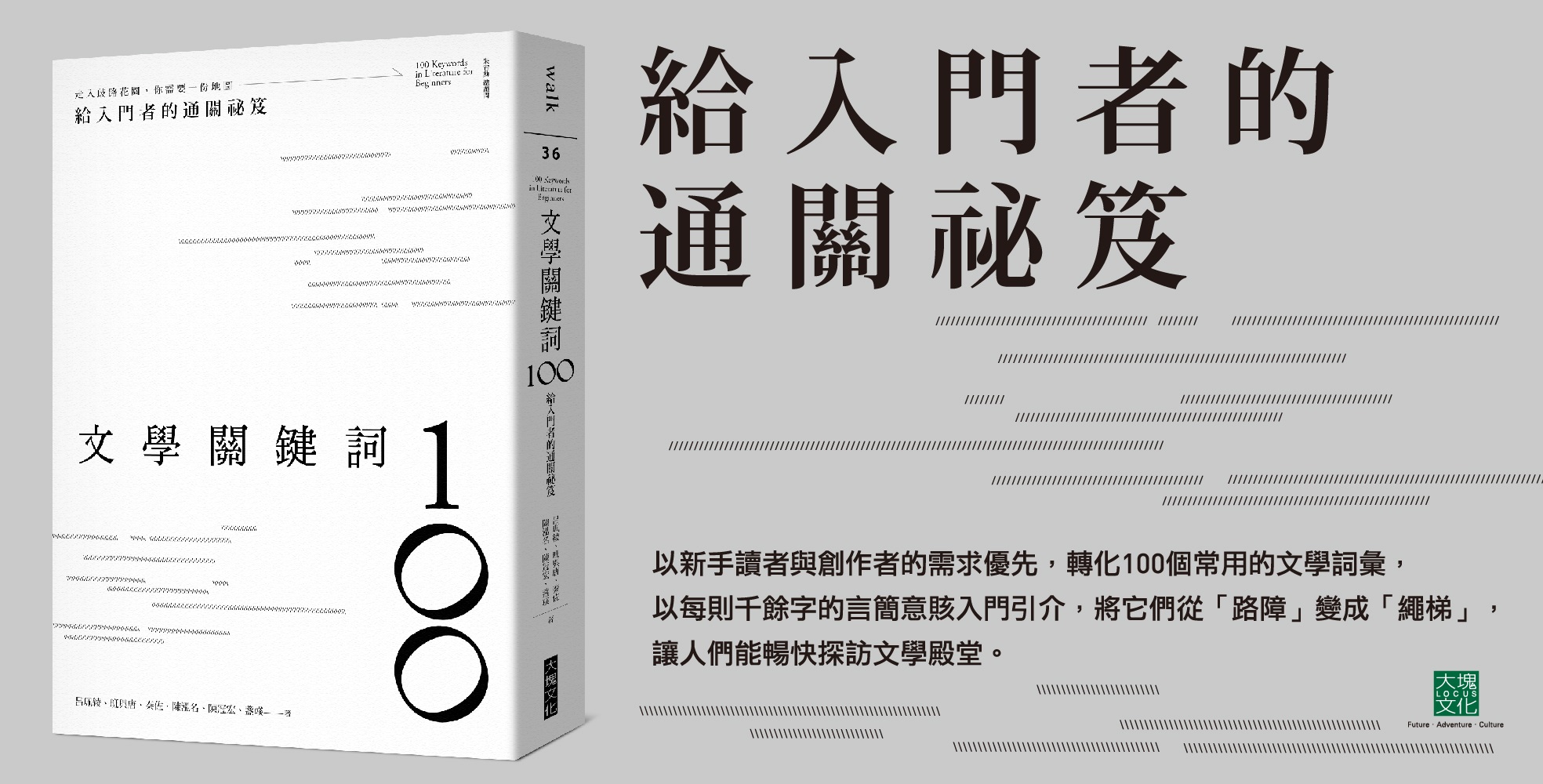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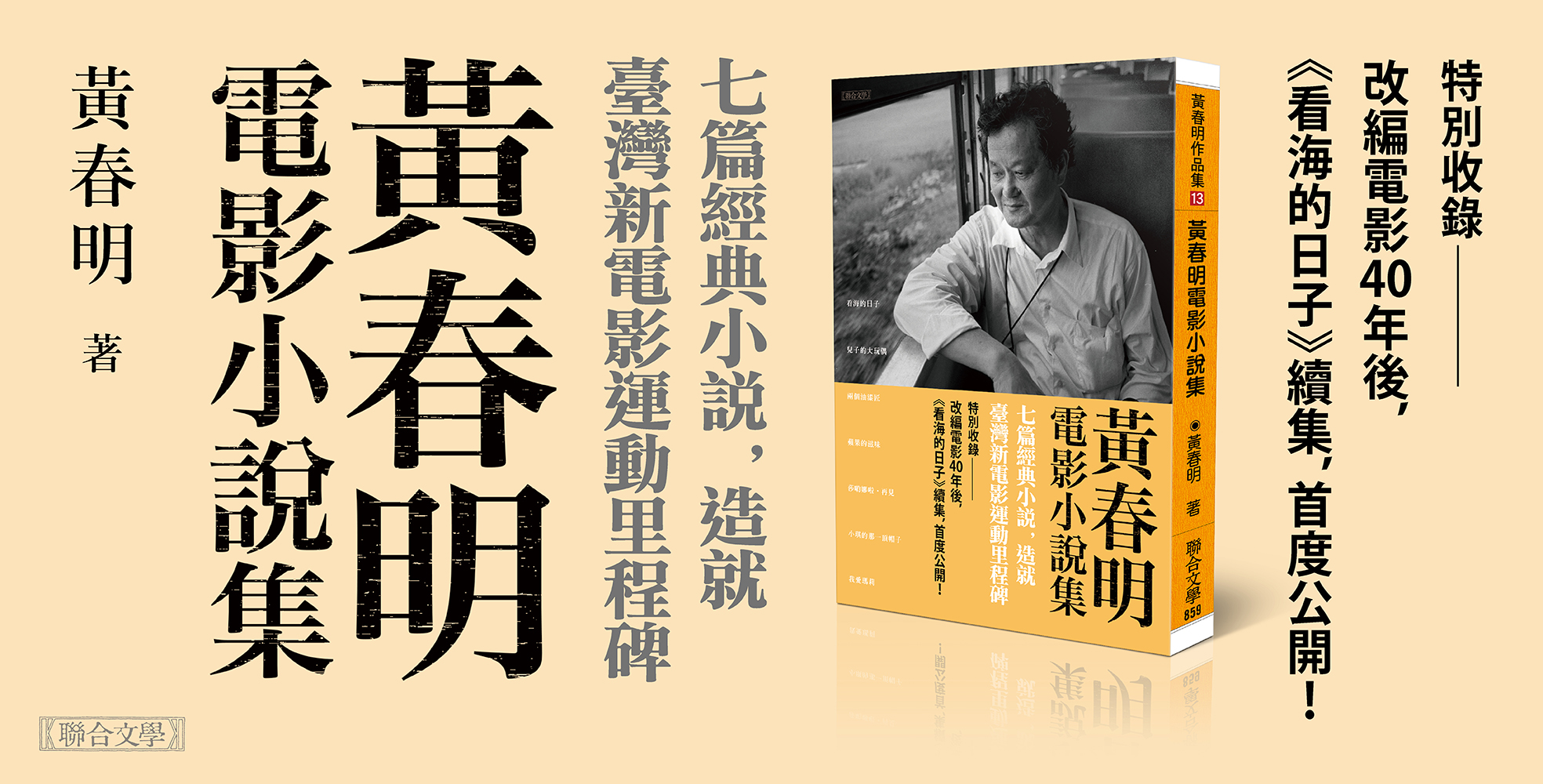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