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雖然他每年都會來聯合文學巡迴文藝營擔任新詩組的導師,我常常有機會遇見他,但其實很少有機會跟他說到話。他不是在忙文藝營的事情,要不然就是在睡覺,呃……或者是我以為他坐在沙發上,就等於是在睡覺,我搞不太清楚,因為他是瞇瞇眼。
有機會說話的時候,當然不用說,有關於詩的事情他什麼都知道,他可是向陽啊,他的詩被收入課本,被李泰祥編成歌,至少有七部碩士論文以他的詩作為研究主題,他是年紀輕輕就擁有巨大詩名的詩人,是80年代最新潮的詩刊《陽光小集》的發行人,當過大報的總編輯,現在又是國立大學的教授,編撰過無數文學選輯、評論集,然後又很會打電動玩具和玩臉書(去年文藝營期間,三不五時就用休息室的電腦上臉書去照顧水族箱,看有沒有人送寶物給他)。所以,有關詩的事情他什麼都知道沒什麼了不起的,我覺得他最了不起的地方,簡單來說就是,他是神仙。

(攝影/王聰威)
我們一起去了西藏旅行,就是之前寫過的,李昂揪的那一團。因為非常擔心高山症的關係,所以絕大部分的團員都準備了充足的藥品。忙碌的神仙向陽當然沒空去理這檔事,我不記得他是不是在機場被迫吃了一顆半顆的,才上了西藏高原,但總之等到我們登上五千多公尺的山地,他居然跟大家宣布,「你們看,我跟王聰威最厲害了,都不用吃藥,也沒問題。」
我不好意思地打槍:「老師,其實我有吃啦!」
他轉頭看著我,一臉不敢置信的樣子。
「你都沒吃藥,晚上不會睡不好嗎?」我有點膽顫心驚地問,因為幾乎沒人睡得好,一晚總是要醒來好幾次。
「我很好睡,一點問題也沒有,一覺到天亮。有人在旁邊看電視講電話聊天,我都照睡。」
這還不是最令人驚訝的神蹟展現,某天某人買了顯然不太新鮮的紅油抄手跟大家分享,所有吃的人幾乎都拉了肚子,唯有向陽自己一人把一整碗抄手全部吃光抹淨,而且一點事情也沒有,照樣背著他的書包,戴著他的紅白雙色小呢帽悠哉悠哉地在含氧量只有平地百分之六十八的西藏高原上閒晃。
然後,最神奇的事情來了!在參觀雪頓節曬大佛的登山途中,我們一團十餘人,幾乎全陷在令人窒息的二十萬人潮如逃難般的擁擠與生死關頭之中,神仙向陽拉住了本來也快陷進人肉磨坊的郭強生,「別進去。」他輕聲地說,於是兩個人從人潮中溜出來,站得遠遠的,輕輕鬆鬆抽菸聊天,直到人潮鬆解,他們才像乘著雲彩一般,一路超前我們飛上山頂,後來下山時又找到一條穿越哲蚌寺的無人石階小道,一邊散步拍照一邊跟和尚聊天,就像只是去街角買份報紙一般悠閒地回到集合地點,其他人面臨的那些可怕擁擠與迷路下山全身泥灰的慘事,與他毫不相關。
最後一日,在離開拉薩的機場等待行李托運時,我忍不住問他,為什麼你總是能夠這麼瀟灑自在,好像沒什麼事會讓你緊張焦慮。
神仙向陽頭戴紅帽,改背新買的喇嘛袋,手上抱著一幅藏紋門簾和一本《從唐卡看西藏歷史》一類的書(所有人在八角街集中精神買項鍊或佛像的時候,只有他不知道從哪裡找來這些玩意兒),他看著我說:「只有兩點。第一,一定要睡飽。」所以能坐就不要站,能躺就不要坐,「不管要做什麼事情,只有睡飽才會有精神做。」
我一個勁地點頭,這簡直是禪宗的頓悟開示!
「第二,要有目標。」
這個我就有點不太懂,我說:「老師,那雪頓節那天,你一起床決定的目標是什麼呢?」
「走路。」神仙向陽說,「能走到什麼程度,就走到什麼程度。你做雜誌也一樣,只要達成你設定的目標就好了,其他人怎麼想,都沒有關係。」
我一聽,淚水已在腦殼裡翻滾,這就是向陽教我的事,我想,也只有神仙才能毫無掛礙地說出這樣的話吧。
【向陽作品】
王聰威
小說家、《聯合文學》總編輯。著有《戀人曾經飛過》《濱線女兒──哈瑪星思戀起》《複島》《稍縱即逝的印象》《中山北路行七擺》《台北不在場證明事件簿》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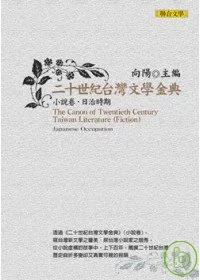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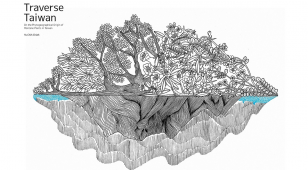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