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要介紹這位台灣電影人,是該從音效師:以《最遙遠的距離》,與師父杜篤之一同得到金馬獎開始?或該說他是紀錄片導演:《海有多深》、《山有多高》、《路有多長》一系列紀錄片得到了「金馬獎」、「金鐘獎」等等國內外大小影展的肯定。
若你是從電影《賽德克.巴萊》才開始知道這位電影圈人稱「湯哥」的重要電影人,其實他還在上集電影《太陽旗》裡,義氣剃頭客串了臭著臉與日本人交接的清朝大臣李經方。
不過關於他和電影《賽德克.巴萊》,或者還有一點更為重要、更值得注意。他除了擔任本片的錄音工作之外,也擔任紀錄片《餘生》的導演。這部電影將紀錄「霧社事件」遺族,甚至日本人後代們的故事與現況,讓《賽德克.巴萊》成為更有意義的三部曲。
看湯湘竹湯哥的紀錄片作品,題材不盡相同、但同樣充滿人味,或許,他也就是最適合完成這第三部曲,為《賽德克.巴萊》作結的人了。
回到電影《賽德克.巴萊》這故事的開頭,湯湘竹與導演魏德聖同在劇組裡跑腿。在攝影師秦鼎昌師傅那裡聽到過,那同一個情節,湯哥的反應可不一樣:「當時我在書店,看到魏德聖寫的那本《小導演失業日記》,還記得是在公館的『巴黎公社』咖啡館,我很火,對他說,你不應該是在寫這種書的人,應該是要去想辦法把電影拍出來!」
2004年的五分鐘百萬預告片,湯哥沒辦法參與拍攝,因為他人在香港工作。「當時一些香港導演開始想把電影推出海外、開始講究品質,所以找了台灣的錄音師團隊過去。」湯哥的電影工作生涯,從受到《戀戀風塵》的啟發開始,涵蓋了90年代之後許多重要的台灣電影,他第一部參與的電影是楊德昌導演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說是參與,其實類似錄音師的學徒。
「為什麼選錄音?半認真的說法是,當時這能讓我最快參與欣賞的導演拍的電影。」作為後來被認同為世界級音效師杜篤之的弟子,他在前段熬了很久,杜篤之一開始還覺得他太鈍了,問他是不是該轉行。「當時這種師徒制裡,師傅對學生只做兩件事:罵人,和不講話。」不挨罵就表示作得還行,那麼學徒該怎麼學呢?「除了跟著幫忙時認真看,都得要自己問,但也不能亂問,要問的對,否則也是挨罵。」就這麼熬了過來,在獨當一面之後,主要負責的電影也累積了許多:從蔡明亮導演的《你那邊幾點》、《天邊一朵雲》、《不見》、《不散》、侯孝賢導演的《咖啡時光》、陳國富導演的《我的美麗與哀愁》、《徵婚啟事》、《雙瞳》、張艾嘉導演的《心動》、陳可辛導演的《甜蜜蜜》,湯湘竹就像是他的師傅杜篤之一樣,早被認為台灣電影音效工作的王牌。
「在拍攝現場,其他人都不知道錄音工作在幹嘛。比如在香港工作的時候,很多場戲,導演會覺得這在現場很難錄到能用的聲音,反正事後音效再配就好了。這時就看自己的態度,你可以混著領錢、或者多些自我要求。」幾次導演事後看片花,才發現現場收音原來能作到這麼好。「作錄音最重要的,其實不是掌握技術,而是經驗累積後的判斷和工作的態度而已。」
「技術在進步,錄音或後製音效都是,但有時現場能錄到的,除了會是最寫實的之外,也會是最好的一次表演。像是這次《賽德克.巴萊》裡面,幾場關鍵的訣別或悲傷的戲,因為是高山環境,若還加上下雨等等,環境音很複雜,你要演員事後再配一次,也不會有當時他那麼好的情緒。我若沒錄到,就錯過他現場最好的那一次聲音表現了。」
收音師的工作方式,第一步也是讀劇本。從劇本搭配現場勘景,就能開始安排工作,「這部電影主要就是戶外高山的實景,再要搭配演員與攝影機的動線,地形部份對收音工作比較麻煩。」你若追問錄音技術細節與執行困難,湯哥會說:「那沒什麼好說的,事情有作到有做好是應該的嘛,畢竟是靠這個吃飯養家啊。」
關於如何開始拍攝第一部紀錄片,他曾在接受《放映週報》專訪時說過:「同樣的一個工作你達到一個技術水準,得到大部分的人的認可,這個情況維持個五六年,我看大概沒人受得了。」當時他正好在進行蘭嶼相關紀錄片的錄音工作,在這契機下,他認識了達悟族原住民馬目諾跟他的族人。馬目諾原本來到都市,在社會底層掙扎工作,三十四歲時嚴重中風,被送回故鄉等死。但回到蘭嶼後,湯哥認識的馬目諾,是與他一同下海捕魚時,在海中比他更俐落的優勢者,這部紀錄片完成後廣受好評,除了開始了他的紀錄片導演生涯,他也開始與這部《海有多深》的配樂者、金曲獎得主陳建年合作。
陳建年也為《賽德克.巴萊》的第三部曲《餘生》作配樂。「他給我的第一個版本,聽了實在太快樂了,就像在大海上滑拼板舟,我跟他說不行啊,我重複地跟他說這故事裡很沈重的部份。我想他的壓力也很大。」作為導演,這紀錄片的原型,可能是他讀的舞鶴相關題材小說《餘生》,「我當時讀了,覺得真的很對味,之中想要表達的那些,幾乎都能讓我清楚感受到。」
「男子漢」氣魄十足的湯哥,其實是所遇過的電影工作者裡,最不避諱文藝氣息的幾個。「我還記得紀錄片拍攝過程裡,看到了一張馬紅莫那(Mahung Mona,莫那魯道的女兒)的遺照,那張照片其實我不知在田調與文獻裡看過多少次了,但當時我忽然從後腦整個涼了起來。我感覺到那是utux(賽德克語的「靈」、「祖靈」),我在面對全部的亡靈。」他頓了一會說:「你一定也有讀過榮格吧?我自己後來是用榮格的理論來跟自己解釋。」
紀錄片《餘生》,名義上由魏德聖導演監製,其實也算在《賽德克.巴萊》的整個製片計畫裡,「錢是由魏德聖那邊統籌調撥,我不擔心他,他是那種欠一屁股債也會把這部份錢給我的人。」
拍攝《賽德克.巴萊》期間,對於參與過太多電影,與形形色色,好的、不認真的導演都合作過的他來說,是很感動的經驗。他也曾經在自己的臉書上以此寫過一篇短文,引發熱烈的轉貼。「當時是在桃園復興鄉小烏來,開拍前我看到大家都很嚴肅,然後幾十個賽德克人從林子裡走出來,那些演員即使是沒有台詞的,都是導演一個一個挑出來的,那個開拍的場面讓我一時震撼,我當時明白了:這電影是玩真的。」
「這電影的拍攝團隊裡,幕前幕後都有許許多多的年輕人加入,他們之前未必有電影拍攝的經驗,卻甚至比許多業內的工作人員或導演都還認真,我跟導演講:這些人這麼年輕,我們應該要讓他們看到一個典範。」如同他也曾受過一些典範的啟發,至今依舊認真堅守在崗位上一般。「但最後是我被這些年輕人激勵了,拍這部電影重新點燃了我的熱情。」
「我後來覺得,是這些沒經驗的年輕人,讓這變成一件很不一樣的事。這拍攝過程本身,就像受到一個理念的召喚,去對不可能的情況據理力爭。」這樣被燃起的熱情,也跟著他一起到了他的紀錄片工作上;又或者,是他對自己習慣「做好本來就是應該」這般的要求。
紀錄片《餘生》,幾乎地毯式地與所有相關人員作過了詢問或訪談,某些人沒有出現在影片裡,是談過之後對方不願意上鏡。「但他們這樣的心情也很重要,雖然可惜,但我能瞭解。」
這部紀錄片,在十足的時間與預算壓力下,除了也出機到日本拍攝,最重要也最艱難的一段是,他要與遺族一同回溯賽德克人的發源地「牡丹岩」(賽德克語:Psuqhuni,位於中央山脈白石山附近,海拔約3100公尺)。這是每年也未必有一個登山隊會到達的地方,但作為導演的他,不但一定要完成,還堅持拍攝器材不能因為難度而就簡。器材租用的費用,得到了中影的大力支援,另外還聘請「雲豹登山隊」14員,才能一同把器材都背上山。
「我和清流部落的賽德克人到了他們的發源地、他們的聖地,當時,我也很自然地流淚了。」他這麼對我們說,眼中看到的是沒能到達那裡的我們,還只能想像的流雲與山色。
然後才剛說過一定要一鼓作氣把這紀錄片完成,準備好好來重讀大江健三郎的他,就在播放陳建年為《餘生》做的配樂給我們聽完之後,口中喃喃說著:「這之中的鋼琴是用midi做的,看看是不是花點錢來租個錄音室和樂手錄一遍,在電影院裡放映的效果會比較好。」
或許,這些都可以歸納濃縮在我們台灣的電影工作者湯湘竹口中,那簡單的一句話之中:「事情有作到有做好是應該的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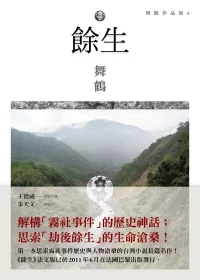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