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 汪正翔)
(攝影/ 汪正翔)
華文長篇小說四年一度的重要大獎「茅盾文學獎」揭曉前夕, 1978年生的中國小說家徐則臣應「兩岸青年文學會議」之邀風塵僕僕來到台灣;甫落座,談及已獲各大文學獎肯定的長篇小說新作《耶路撒冷》,抬頭便說,「耶路撒冷四個字,是黑色的。」
「我特別喜歡這四個字,喜歡它念出來的語感,文字本身散發出的味道,我能感受它的顏色,」他以小說家納博科夫為例,認為漢語與外語間的對位,有其特殊關連,「耶路撒冷,看起來肯定是硬的吧?黑色如石頭般的質地。」起自對這四個字的迷戀,徐則臣一寫就是六年。
題目先跳出來,是啟動他寫作的按鈕。2014年魯迅文學獎得獎作《如果大雪封門》便是信步街頭突然冒出的念頭,「我有一張紙,上頭寫的全是題目,有些很多年前就有了,有些你一輩子也不會寫它,但記得它們就在我的書桌前,我每天就這麼盯著看。」如同電腦數據庫,某天,一個故事,一個靈感,一個契機來了,與紙片上的題目接頭,小說便開始落實。「要我解釋《如果大雪封門》是什麼意思我說不清楚,模模糊糊感覺後面有個空間,我的小說都是這麼開始的。」
《耶路撒冷》書腰文案「七〇年代的成長心靈史」,小說所處理的,是徐則臣自身以及這一代人此時正面臨的問題,即台灣稱的「六年級」。來自不同地區的讀者反饋,小說讀來並未因區域形成隔閡,台灣的讀者亦同,徐則臣表示不意外,2010年10月參與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期間,他與來自32個國家、38位作家交流──作為70年代出生的這批人,有什麼想法?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最大的焦慮是什麼?對不是70後出身的作家同儕,則問他們眼中70後的人有什麼特點?「抽樣雖無法代表整個世代,但有一部分涵蓋到了。」這或許是小說讀來格外有共鳴的原因。
70年代出生的人,精神上普遍面臨兩種狀態,一是人到中年,再者是親見時代加速的過程,並身陷其中。透過微博與讀者即刻交流,對徐則臣而言已是再日常不過的動作;現代生活所具備的一切之於80、90年代出生的,那是「理所當然」,70年代這群人則是看著自己的時代如何變成80、90年代的,「尤其是網路,我到2003年才開始上網。」徐則臣說,網路讓生活乍看更便捷,但同時也變得更複雜。80、90年代的讀者看重他小說裡的人物如何面對家庭、愛情、事業等共通議題,問他:「你們70年代的人怎麼都這麼老呀!」徐則臣笑談年輕一代口中的「老」是指「你們想的東西太多了」,但他們這代人也開始感受自己正慢慢開始往老的方向去了,「要我說的話,80、90年代的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之外,我們這輩人則慢慢往自己的內在去生活,《耶路撒冷》裡頭的人會這麼複雜,道理一模一樣。」
 (攝影/ 汪正翔)
(攝影/ 汪正翔)
小說的開始與結尾,場景都在月台,強烈的畫面語言,《耶路撒冷》一新台灣讀者熟悉的中國小說家如余華、蘇童的作品印象。〈後記〉寫到:「那個美國的後半夜,我在桌子上留下一堆畫滿圖形與文字的紙張」,有畫面感的文字作品改編成電視劇或電影特別容易。徐則臣說,把眼睛閉上試著想個故事,可能沒法具體描述,卻隱約勾勒出個輪廓,那就是我們習以為常、能夠認可所謂小說的樣子,「想傳達的道理即使如何艱深,一部好的小說一定可以找到某種形式,轉化成具有形象的語言。」
《耶路撒冷》分單、雙數章前後呼應,小說家要處理的正是小說的結構,自第一章以專欄作家「初平陽」第三人稱視角,推展到終章初平陽第一人稱現身說法,前後11章,中間第六章以關鍵人物「景天賜」為題,將前代人如秦奶奶,同輩人如秦福小,過去記憶與現在進行式成功交揉相疊。「你在夢裡經常迷路,因為耶路撒冷布滿石頭」,第七章一開頭,書名「耶路撒冷」跟所有角色人物的線頭,以此為原點,輻射般爆裂發散。
結構之外,倖存者的概念貫穿整部小說,納粹屠殺、文革、川震,往小說核心再推進則是自殺者遺族。亡者總在歷史中被遺忘,徐則臣表示,中國的年輕作家已經開始觸及文革題材,早幾年有輿論方面的壓力,能不談最好不談;第二個原因是中國這些年對文革的認識並沒有更深入,所有相關題材的小說,基本上沒有超越80年代的作品,「只是變個花樣,卻沒有新東西,當然無法吸引年輕的寫作者。70後的作家都到了進入40歲的年齡,對於社會跟歷史,會有自己的看法。」徐則臣稱,這是「一個人的遊行」,從前個人是側身在隊伍裡的,與眾人振臂高呼,視自己為集體的一分子而自豪,「套用文革的話:我是一顆螺絲釘。」而年過30,逐漸意識集體是可疑的,眾口一詞是可疑的,集體是以取消個人為代價的,現在的中國開始有能力一一重新審視教科書形塑出的集體主義,「我看到很多與我同輩的中國作家,慢慢觸及文革題材,新的反思開始出現,作品才能擺脫束縛。」
《耶路撒冷》進行集體記憶的重組與解構,卻也縫進70年代以降的個人記憶,譬如六四,行文雖未明點,但在〈時間簡史〉一章透過被敘述者的求學經歷把年份埋伏其中,「我寫得很隱晦。希望透過這樣的過程,把個人從集體主義給掙脫出來。」
平日任職於人民文學雜誌社,徐則臣說固定且不被打擾的寫作時間是奢侈的,只能見縫插針,這也是《耶路撒冷》定稿修了三版的原因,「一週能有兩個完整的下午就很不錯了,但我現在愈來愈嬌氣了,求學時一間宿舍四個人怎麼吵我都能寫,但現在一定得關上門,哪怕是隻貓從身後安靜踱過,我都覺得有問題。」小說裡的專欄作家初平陽的原型,活脫出自徐則臣自身。
年紀漸長,看法也隨之變化,從小鎮前往城市,再去到世界,徐則臣年輕時的世界是米蘭.昆德拉的《生活在他方》,「出走是必然的,區隔於故鄉的才叫世界。中國跟台灣有個很大的區別,台灣是個飽和的區域,城鄉之間沒有太大的區別,但中國正在進行『城市化進程』,鄉村逐漸消失。」他點明現代人所說的故鄉指的是鄉土,「如今土地在消失,鄉村在消失,我們的鄉愁該怎麼辦?」在故鄉以外的大地方待了多年以後,人不會因此心安,回到故鄉更不是原來的情懷,徐則臣以寓言故事比喻,接受神諭出發尋找財寶的每個年輕人,最後都會發現世界就是故鄉,財寶就在自家門口,「所以《耶路撒冷》的秦福小選擇回家,她既是到世界去了,也同時回到故鄉。」
將二、三十年甚至更久遠的記憶與歷史,濃縮在五天內呈現,《耶路撒冷》40餘萬字,規模龐大卻節奏明快。下一部長篇,已經在徐則臣腦中盤組,元朝以降北大都建都以後,貫穿中國魚米之鄉杭州與政治中心北京的京杭運河1901年與2014年的古今映照。大學時期生活在淮陰,他對水的感情,追溯到兒時成長的小鎮,文革時期挖建、江蘇省最大運河石安運河從中貫穿而過,「初三住校,天冷水龍頭全結冰,我們一夥同學就端著臉盆到運河邊上刷牙洗臉;午休沒事,縱身一跳就在運河裡游泳。」
《耶路撒冷》的時間看似迢遠,幾小時幾分幾秒的子彈時間,卻宛如王家衛電影重現;開車行經國界邊境,徐則臣看見黑龍江上連緜不絕的滿天閃電,中國與俄羅斯的商船分兩道水線航巡,水文的印記,將緊扣小說家一生不滅。
〔徐則臣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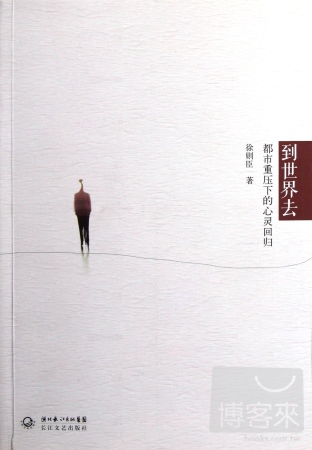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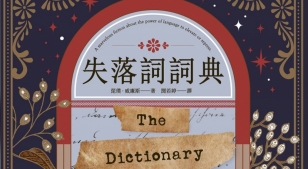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