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台灣人,既非從商,也非依親,只為了近距離觀察中國在近代的劇烈變化,更為進一步理解生活在中國裡的每一個人,將會如何因應轉型期間翻天覆地的浪潮。基於這些想法,身為台大法學碩士的李政亮,在2000年移居中國,一住就是11年。而他將這段時間的體會,寫入了《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成為最實地的在中第一手生活資料。
李政亮不僅在中國完成他的最高學歷(北京大學哲學博士),更在中國落實娶妻、生子與求職(天津南開大學傳播系任教)等人生過程。歸屬於「八零前」世代的他,因著生活與工作,同時接觸到中國八零前、八零後,乃至於九零後的人們,正是近十年來正面迎接變動中國的三大族群,也剛好分別代表了主力、承襲與醞釀世代。
帶著台灣的成長與求學經驗而去,對於中國這個近乎處處皆爭議的世界話題中心,李政亮既不用國際經濟的標準衡量,也避免用政治分化的眼光看待,而是以一個身在其中真實度日的知識小民,來接收與試著理解中國劇烈的變化。如同《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的副標所註解,在他對中國的初步結論中,包含了「1/3流行文化+1/3國族想像+1/3日常生活」;而在這三個層面裡,不同的世代,也有著不同的觀念與處置方式。
「在中國檯面上的年輕知識分子,似乎讓人感覺很樂於或勇於批判,其實不免也有『媒體化』的成分存在。」李政亮表示,中國的學者專家們與台灣一樣,都出現了體制化與邊緣化的問題,「一些敢言、敢動的學者,只要被綁在學校裡、卡在升等的規章當中,氣勢就會慢慢弱掉。」學者批判的聲音受困,線上媒體的記者或文字工作者們,多半只著眼於具時效的新聞議題,一抓到機會就窮追猛打,跟台灣沒什麼兩樣。差別在於中國尚有言論管控的問題,一旦受到管控,議題也就瞬間消失,等待下一個議題再出現。彷彿處於一種將鬆綁又未鬆綁的狀態,諸多族群伺機而動,隨時都要衝撞,但一衝撞又會遭到打壓。「有族群要衝撞,但也有族群要捍衛這個體制。」李政亮認為,這種弔詭的情形,在這一兩年會有相當關鍵的轉變。
或許我們可以說,隨時準備要衝撞的世代,屬於言論與行動都風風火火的「八零後」;而捍衛體制的,則是依舊抓著中國政治經濟重心的「八零前」。「就像中國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提倡的『唱紅歌』,就是呼籲要『回復過去的精神』。」過去的精神是什麼?是某些八零前的人曾經擁有的「上山下鄉」的經驗,他們認為這是此代人最重要的精神資產。「這批人覺得現代社會矛盾太多、過於空洞,缺乏一個共通的價值。」眼見貧富差距日漸擴大,社會缺乏團結的基礎,無力以實際作為去處理民生經濟問題的結果,就是重新用文化民粹主義,高舉著道德旗幟,來重建社會主義原初的精神,「唱紅歌」便因此出現。
「唱紅歌頌揚的內容,最經典的就是毛澤東說的:年輕人要『像八九點鐘的太陽』那般光明向上,要把當年上山下鄉勤勞刻苦發揮出來。」這樣的緬懷在價值虛無的環境裡極易產生,可說是八零前無力掌控國家轉變,於是呼喊回歸。「中國對『維穩』(維持穩定)的想法很根深蒂固,永遠覺得需要團結。但團結需要一個核心價值,當下找不到、未來看不到,只好從過去挖。」李政亮說。
即便是八零後,也逐漸進入了三十歲大關。「他們其實是物質最充裕的一代,還親眼見證了中國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過程。」八零後不僅看著國家經濟起飛,更經歷了北京奧運等全民事件,體會到前後的激烈昂揚與急速冷卻,「這讓他們對於國家與個人的聯結,產生了更多的反思。」加上八零後不只是網路與新媒體最重要的使用者,也面臨了相當嚴苛的城市生活壓力,要他們對這些問題視而不見,近乎是不可能。
「九零後,特別在他們的次世代文化裡,流行起所謂的『穿越』。」「穿越」簡而言之,就是跨越時空,回到過去(或未來)。此世代對此話題著迷的程度,不只在小說或戲劇裡,甚至發生北京的小學生因此自殺、留下遺書說明自己回到過去的哪個朝代。「很多人都在討論『穿越』出現的脈絡是什麼,甚至對之批判。」李政亮自己對這個現象也充滿好奇,認為是相當值得持續關注的一件事。然而,無論是八零前的唱紅歌,或是九零後的穿越,差別只在前者的概念曾經存在,而後者屬於架空虛構,兩者的根基其實很接近。
「當我們在現實上遇到問題,自然會從成長經驗裡,找出一些自己覺得美好的回憶。」也許在近十年的中國裡,我們可以看見的是,因為對現狀的無能為力,各世代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逃避或追尋,期冀有個場域可以交託自己。而,中國如此,台灣又何嘗不是?
〔李政亮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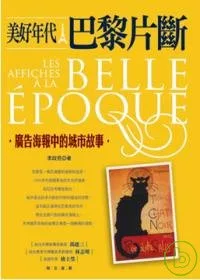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