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去了淡水,為了採訪。自從去年去拜訪一位在淡水的友人後,又過了一年,我沒有前往淡水,或為一杯咖啡,或為了在出海口岸邊,以啤酒換一杯發呆。在生活類型雜誌工作中,我比較喜愛的,該是採訪。以進行的方式來描述,更像是:提出理想的問題,然後聽別人說話。有時,不一定是有對應或共鳴的「聊天」。這些人,多半是某種專業領域的職匠達人,聽他們說話,很能獲得想法、觀點和故事。當然,偶爾也會遇見熱愛建築玻璃屋的善謊者。他們的故事,對我而言,也有不同流質的迷人處。總之,聆聽,是一件挺好的事。
在這趟淡水行程之前,有件事我一直掛心。我與另一位朋友聊到,向作家表達讀後感與想法的事。主因是,一位作家朋友請我看看他的書,然後給他意見。我慢慢看,閱讀的過程,把第一時間閃現的困擾讀感與疑惑,都寫落書的最後空白頁,列出了六七條意見。後來,我沒有太多修飾,一條條直白告訴了這位作家……有好話,也有壞話,但全是心底的實話。之後,我與另一位文學雜誌編輯聊到這事,我們來往推敲討論了一件事:不管實話,有幾分實,有幾分好幾分壞,作家們有沒有聆聽實話的勇氣?結論是,這個圈子(該是指文學圈),說好話的人夠多了,不差他與我兩個弱聲者,所以還是說實話好了。我想了想,打從數年前與幾位作家朋友一同在報紙副刊執行「只能說壞話」的一百日不斷電專欄之後,我就忘了「只說好話」的技能,也只能繼續說實話,時不時得罪不熟悉我的朋友。只是,不知從何時開始的,「說實話」不是美德,變成了一種帶有貶意與容易得罪人的不成熟狀態。
所以,每次碰到也說實話的人,總會想再聆聽他多說一些。這趟去淡水的工作行程,就遇見一位說實話的啤酒小店老闆A先生。A先生的店,就在幾乎費棄了功能的淡水第一港口邊上,室內室外吧檯椅子總加起來,也不足十個座位,卻也開店了六七個年頭。小小一間店,裡頭喝得到近二十個國家、三十多種啤酒。很多都是他出國帶回來的。
我說,謝謝這次讓我們拍攝。
A先生說,不打擾,平常客人也不多。
我說,怎麼選在這裡開這種啤酒屋?
A先生說,我本來是賣烤韓國魷魚的。喜歡啤酒,卻發現台灣人對啤酒誤會很深,所以決定賣啤酒……就像現在台灣喝葡萄酒的文化,真是生病了。
A先生告訴我另一個小故事。他有一位朋友,是葡萄酒進口商。有一回邀請他進口的葡萄酒莊園主人到台灣走走。他朋友帶這位莊主上大飯店的餐廳,為了盡興也表達大方,請莊主不用擔心價格,儘管點。莊主看了看菜單,然後點了價格偏低的一白酒一紅酒。他朋友有點愣,巧妙尋問,得到的答覆是:這兩瓶酒適合今天的菜。簡單試酒之後,桌間的台灣朋友們,開始看酒液顏色,搖晃酒杯讓酒呼吸,細看酒腳濃稠度,然後咬口漱口,有些還微微閉上眼,品嚐……過程中,這位葡萄酒莊主一臉不解,然後端起杯子,一來就是一大口。然後,尋問這位酒商朋友,台灣人都這樣喝葡萄酒的?他朋友反問,有什麼異常?酒莊莊主又反問,我們不是來吃飯喝酒的?只是單純的「吃」與「喝」,怎麼一頓飯變成了釀酒師的Tasting?
這真的說了實話。然後,我說了另一個實話,對不起,我被醫生告知,不能再喝啤酒了。
他說,年紀輕輕就痛風啊,那你真的不能喝了。只是不要以為喝啤酒會得痛風,應該說,痛風了,就不要再喝啤酒。不過,生活裡有很多日常食物的普林值,比啤酒高多了。
這是另一個實話嗎……(真好?)最後我還是沒能喝上一杯,因為要負責開車。
淡水的工作結束後沒幾天,我又因為工作,前往上回提過的George House coffee Workshop,拜訪真實存在的W先生。他是一家咖啡豆進口商的顧問,經常到世界各地的咖啡產區挑豆、選豆、烘豆、煮豆,擔任Coffee Cupper的工作。知道我也喜歡喝Espresso,便請店長J調了一杯「冰」Espresso。是的,將Espresso直接倒入冰出白霜的小角冰,請我慢慢的喝。這又成了我的第一次:冰的Espresso。很特別的一次過程:我從香氣爆發的狀態,分了五六口,慢慢喝到酸與苦出現平衡的新口感。說實話,是真的,冰的,Espresso。該有的酸醇苦體,喝到最後一口都沒有缺乏感。
這期間,W先生聊說,自己已經不太像從前那麼氣盛了。公司開George House這樣的客人自行配豆門市,經營並不容易,因為他的目的很單一:只是想讓真的喜歡喝咖啡的人,去George House喝咖啡。所以沒有提供吃的,也沒有講究的氣氛……在我看來,這是實話,但整個店家更像是一處設計俐落的「咖啡工作室」,一如它的店名尾字:Workshop。他年輕氣盛時,也常想邀請一些國外真的懂咖啡也有影響力的人,到台灣來走看交流。但不會像一些咖啡商,邀請產地的咖啡園莊主來台灣演講。對此,我露出疑問。W先生說,很多咖啡園的主人其實不懂配豆、烘豆,他們通常是留下這一年少量的自家咖啡豆,到城裡找家廠子烘豆,有時還直接磨了一麻袋帶回家,想喝的時候,就舀一杓來沖沖。W先生說,他們只是很懂種咖啡豆的農夫,不過,他們卻是真的喝得出什麼是好咖啡的人。
這一前一後,都是實話。我追問,他為什麼不邀請那些Coffee Cupper來台灣?
W先生說,不行,我擔心會讓很多同行做不下去,會死一堆人。
我說:怎麼說?
W先生說,我認識的這些Cupper,都只會說實話……
(PS.聽完之後,我多少感覺到心中的驕傲,即便知道以後如說實話,總還會得罪到什麼人吧……)

(攝影/高翊峰)
高翊峰
做過調酒師、廣告文案、編劇,也做了十多年雜誌編輯。得過一些文學獎和編劇獎。目前在《GQ》擔任副總編輯,並繼續維持寫小說的日子。出版了《一公克的憂傷》《奔馳在美麗的光裡》《肉身蛾》及最新長篇小說《幻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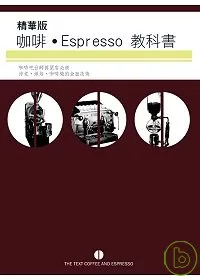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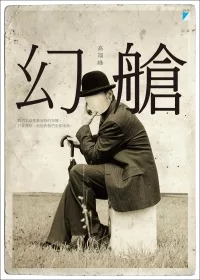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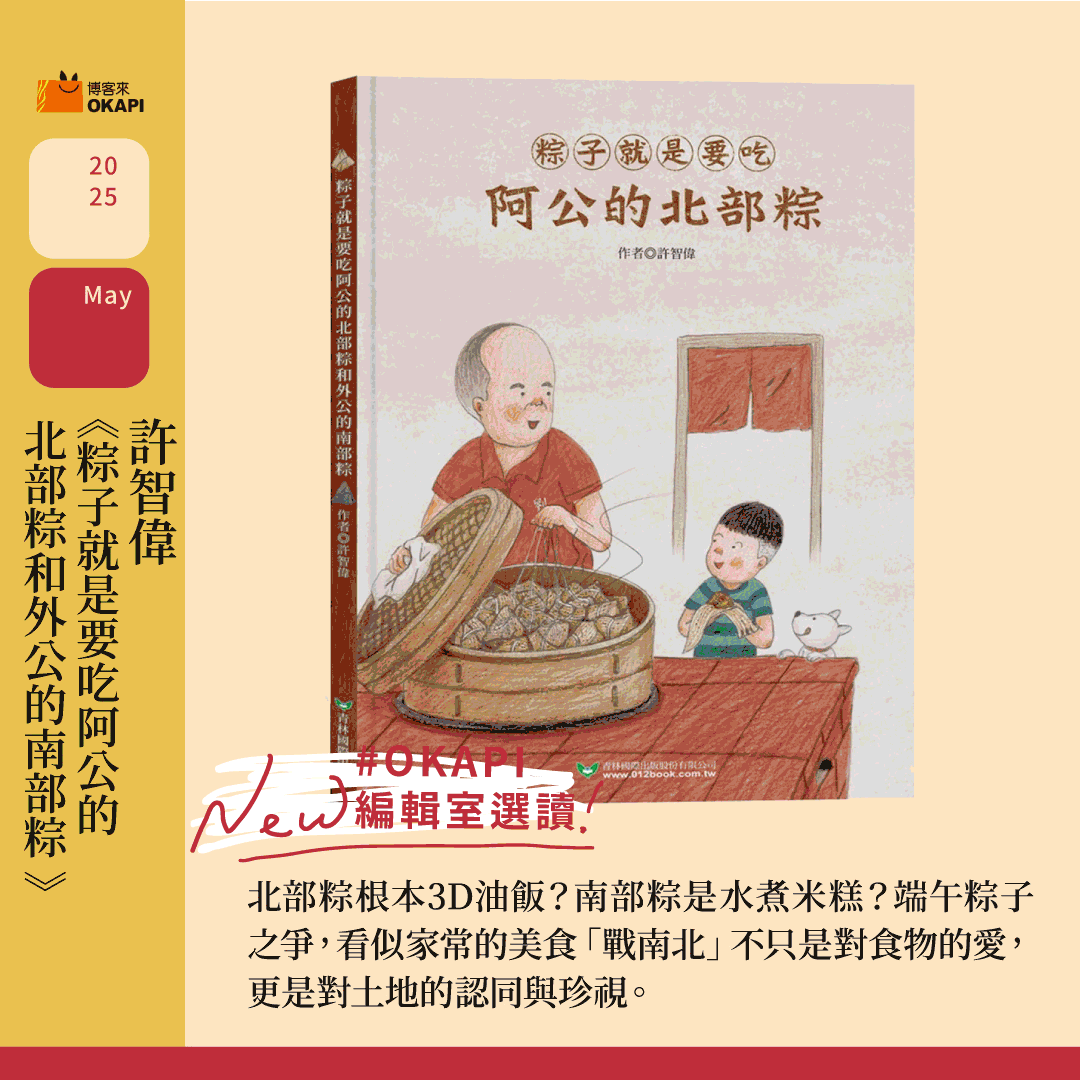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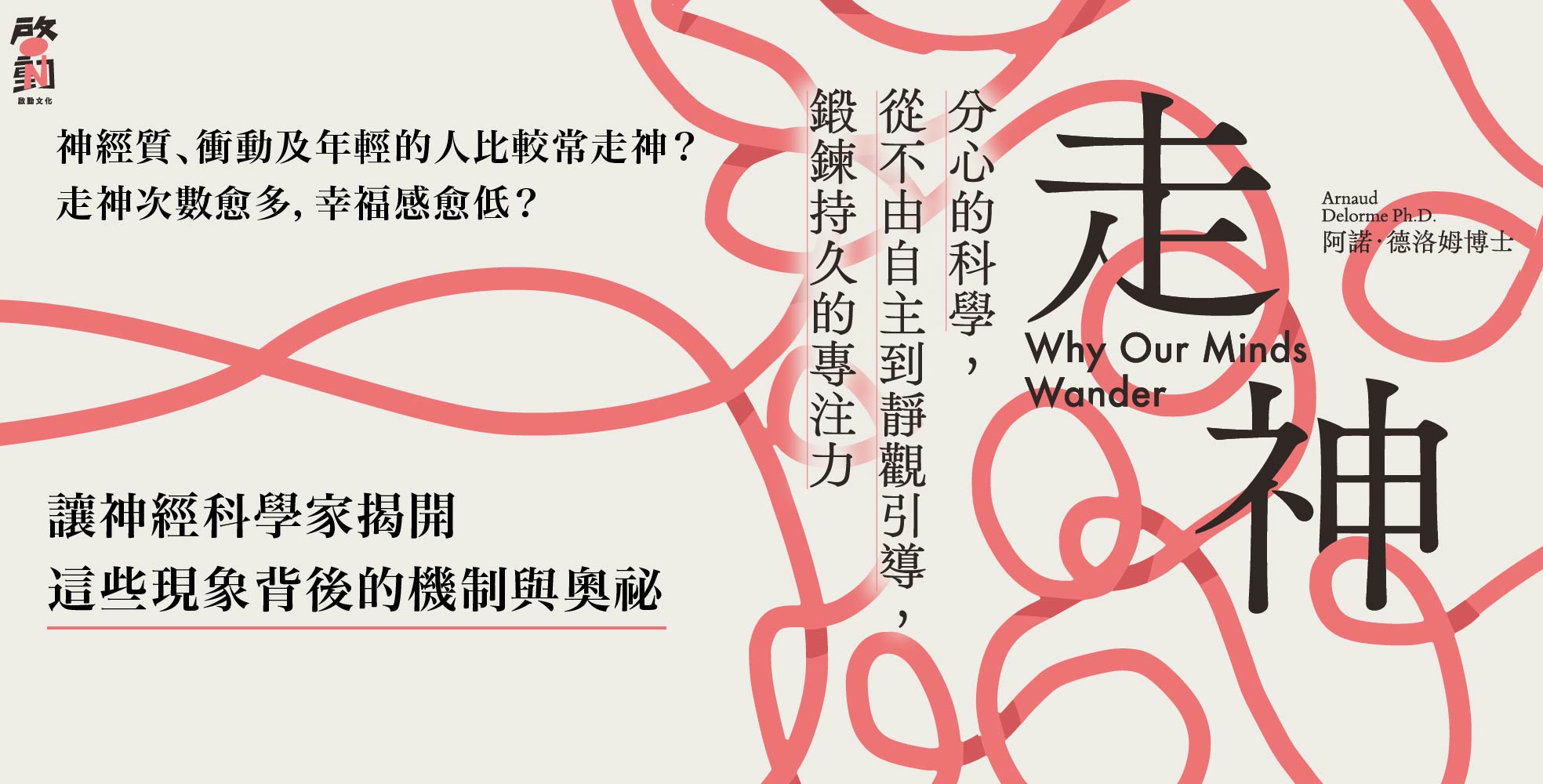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