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達利
「我對一個地方的評價和印象,主要還是對『吃』而來;一個地方東西好吃,我對那兒的印象就大抵不錯,但如果東西難吃,那兒有再多的靚女俊男,我的印象也好不到哪兒去。」2010 年 9 月份,以《紅高梁家族》、《豐乳肥臀》、《檀香刑》等小說聞名於世的大陸作家莫言來台,17 日午后,我們得到一個訪問的機會;走進飯店包廂的時候,莫言與出版社及媒體的餐敘還未散席,待到開始採訪,我們的話頭,自然從「吃」談起。
在莫言的作品當中,「吃」常佔據了重要位置,或許與故事主線無關,但為了求生存或者單純地嘴饞而「吃」,卻常是驅使故事中角色們進行某些行為、推動劇情前進的動力。先前在許多類似的訪問當中,莫言已經多次提過,這種情況來自幼年時清苦的家境;成為舉世聞名的作家之後,這類基本的民生需求自然已經不虞匱乏,倒是常在席間見著浪費食物的情況,讓他深惡痛絕。
因為對一地的評價大多從「吃」而來,是故莫言坦言對台灣的印象很好,「這兒吃的也好,人也好,所以叫做寶島嘛;」他瞇著眼笑著,又談起在世界各地有什麼飲食心得,我們趁機進言:不如未來,就來寫些同「吃」有關的食記散文吧?
莫言認為這主意不錯,回想自己發表過的散文,雖有幾篇專門談「吃」,但還是與自己的童年經驗有關,較少提及後來的飲食心得。事實上,莫言大部份的長篇,寫到主角們長大成人、遇上大陸近年的改革開放社會時,多已經是故事的中後段落,但剛才莫言已經從「吃 」談到近年來的物質浪費亂象、過度需索怪狀,可見得對於當今世界的種種異常,他一直沒有停下小說家的觀察視點。那麼,我們未來是否可能讀到一本莫言的作品,故事是從「現在」開始發生的呢?
「我一拿起筆啊,就會回到鄉村裡頭;」莫言回答,他對於變化中的鄉村十分關注,但一開始說故事,自己的幼時回憶便會馬上回歸,畢竟那是一切發生的源頭、是自己故事的起點。另一方面,莫言也坦承,這種情況有一部份來自於自己最瞭解那個年代的農村生活及農民心態。
「父親那一輩的人在想什麼、遇到事情會用什麼心態處理,我很清楚,」莫言說道,「我這一代的人,我也很能理解;但我在北京已經住了卅多年,比我在故鄉的時間還長了,雖然瞭解巷弄胡同、瞭解樹木景物,卻還不夠瞭解住在北京的人在想些什麼。在北京,每個人都自成一個小團體,我不能瞭解他們心裡深處的想法,寫起來自然覺得有些隔閡。」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莫言對故鄉青年的看法上,「我每年都會回山東高密東北鄉十幾次,村子裡的年輕人現在不下田勞動了,他們白天到城裡打工,晚上回家也會上網,自覺不是『鄉下人』了,但我估計城裡的人也不把他們當成『都市人』看待。」莫言笑道,「有幾次我和這些年輕人交談,想要瞭解他們的想法,但他們對我好像都挺敬畏的、想要快點兒結束和對話似的,『過得好嗎?』『還好』『掙多少錢啊?』『也沒多少錢』『有什麼想法呀?』『也沒什麼想法』......完全談不下去嘛!」
雖然莫言一人分飾兩角,演得十分逗趣,但我們心想,要是我們在故里忽然遇上這種情況,生出敬畏之心,大概在所難免吧?畢竟這可是一位寫出《酒國》、《生死疲勞》、《蛙》等重要小說的作家啊。
談到自己的作品,莫言還是聊得輕鬆,但很明顯地嚴肅不少;在莫言的小說當中,有不少酣暢痛快一氣呵成的長篇,不過也有幾部的結構奇特巧妙,「我先前的作品裡,結構最複雜的可能是《酒國》吧?」莫言回憶著,「這個故事有兩條主線,一是有個叫『莫言』的作家寫的故事,講述一個調查員到某城去調查當地吃嬰兒大宴的案件,結果一到城裡就被灌醉,弄不清楚自己看到的是真是假;另一是該城的一個『酒博士』不停地把自己的小說作品寄給這個『莫言』,和他來回地通信討論。寫到一半,我覺得這兩個故事可以合在一起,於是最後小說裡的『莫言』也到了那個城,見到了『酒博士』,發現了一些真相,卻也陷入一個虛實難辨的情況。」
這個例子裡的結構是在創作當中才逐漸成型的,但也有不同的狀況,「寫《檀香刑》的初衷,是想寫一個關於歷史的、大格局的故事,但又不想要照傳統的章回小說方式進行,於是我想出與主題相關、戲曲式的段落,」莫言解釋,「分成三部,角色的名字也照戲曲裡的命名方法,在第一、第三部用的是第一人稱,在第二部〈豬肚〉部,則用第三人稱的方式去建構整個時代背景。」
「其實『結構』就是『政治』,」莫言表示,「選用的『結構』不但定義了作品的調性,有些敏感的題材,也可以藉著『結構』來堂而皇之地講述。」
敏感題材其實莫言寫過不少,《豐乳肥臀》雖然得了大獎,但當年光是書名就引發不少反彈,最新的長篇《蛙》,更挑戰了沒有創作者碰觸過的生育管制問題。「這個政策所引發的後續影響很多,沒有身在其中,很難給予什麼評價,也得等到未來,才能由歷史來給論斷;」莫言說明著,「其實這個故事原來想的架構很複雜,是一個劇作家坐在臺下,看自己的劇作排演,在劇情之間插入劇作家的生活,以一種拼貼的方法表現;不過寫到一半我覺得不大對,於是先停下來,寫了《生死疲勞》,然後再回來,重頭寫過。」
《蛙》以幾封長信和一份劇本組成,正好都是一種「與現實相關、卻又不完全符合現實」的型式;莫言道,「最後的劇本,一方面補足了前面長信裡的某部份劇情,一方面卻又與某部份情節相悖,孰真孰假,需要讀者自己判斷。可以說是用這種結構,才能成就這部小說。」
除了這些長篇之外,莫言的中短篇作品其實也很精采;提到這個,莫言開心地道,「其實我一直覺得短篇是我的強項,可惜自幾年前的〈月光斬〉之後,就沒有再發表過短篇了,接下來應該找空再來寫一組。」聊了幾則我們印象深刻的短篇,當中有不少脫胎自莫言聽聞的軼事或鄉野傳說,也有幾則反應了他在現實當中的心境,比如我們覺得十分怪異恐怖的〈姆指銬〉,「那是在《豐乳肥臀》發表後,我遭到了很大的批評,心裡頭不大舒坦,所以寫了那個被姆指銬銬住的孩子;」莫言如此說明,也提及了結局與自己在現實裡最後決定的聯結,「畢竟想要自由,就得要有些犧牲。」
鄉野傳奇常是莫言作品當中重要的養份來源,在《檀香刑》中,莫言更提及了接近失傳的地方戲曲「茂腔」;這是我們都不熟悉的一種戲劇,不知道在《檀香刑》發表之後,對這種戲曲型式的傳承,是否提供了一些幫助?
講到這個,莫言來了興頭兒,先同我們描述了在《檀香刑》裡被稱為「貓腔」的這種戲曲型式「理論上就是個哭哭啼啼的戲」,再談到地方戲曲常常會依觀眾的喜好做出破壞結構的發展,「比如說有個悲劇,講到主角應該要開始復仇的橋段,被叮囑要去墳上點個燈籠;結果下一幕開始談他在返鄉路上看到燈會,整整有七百九十句的茂腔,都在描述燈會上的燈,什麼歷史人物燈如何如何、青菜燈怎樣怎樣,螃蟹燈又如此這般,等七百九十句唱完,這戲也結束了。我從前上課時老舉這例子說明傳統戲劇的不依結構,不過現在的看法改變了:這樣的創作方法,不也是另一種結構嗎?」
「不過傳統戲曲要能傳承,不能只是硬性地把樣版留著,那就只能保存在博物館裡頭,」莫言續道,「它得要注入新的生命,繼續地演出。近年我和幾個地方政府談過,他們也開始培育年輕的茂腔演員,只是目前還沒編寫出讓我覺得滿意的新劇碼。」
傳統鮮活的說書語言、不受限制的敘事結構,加上從鄉土及歷史當中滋養生長的故事種子,縱使已經是享譽國際的知名作家,莫言對未來仍有許多創作計劃;無論是前述的短篇或者是茂腔劇本,或者是下一部令人大呼過癮的長篇作品,依然都讓人引頸期待。
結束訪問時,莫言替我們簽了名,臨行之際,我們想起在莫言提過:餃子仍是他最愛的食物──「任何事都會變,唯獨我對餃子的愛,是不會變的。」在上回的電子郵件專訪裡,莫言是這麼說的;於是我們對他說,「希望下次有機會,能請老師吃頓餃子。」
莫言點點頭,笑了。
嘿。或許馬上會讀到莫言作品的,就是我們建議的散文食記了吧?
莫言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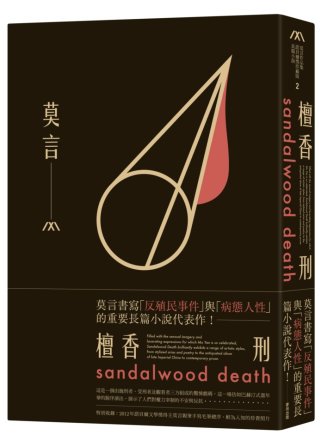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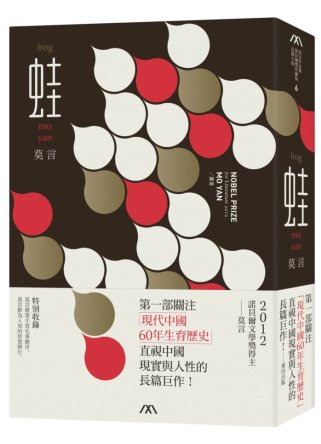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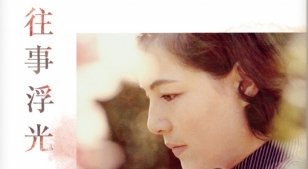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