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凱特琳‧彭歌於自宅客廳留影,手上拿著的是2010年4月於法國新出版的《中央公園的松鼠星期一好悲傷》一書。挾帶三部曲前兩本的聲勢,出書不久便攀上暢銷書排行榜。
(攝影:謝芷霖)
(攝影:謝芷霖)
與凱特琳‧彭歌的訪談約在三月八日下午,正好是國際婦女節。時間地點都是由她定的,就在她位於巴黎西邊接近布隆涅森林的家中,位於非常著名的高級住宅區,是現任法國總統沙克吉以前當市長時的轄地。能夠獲邀至作者的家中採訪,還真不是常有的事,尤其在保護私密空間的法國。能夠直接深入作家生活的空間,的確更能瞭解其人吧。
我按照計畫讀完1400頁的《鱷魚的黃眼睛》和《烏龜的華爾滋》兩部曲,寫下該問的問題,還有未形諸筆墨的諸多好奇,帶著錄音器材和照相機,準時按響了她家門鈴。因為曾在YouTube上看過她的訪問錄影,對講機中精力充沛的聲音一聽就知道是她本人。狗狗比她先衝出門來迎接我,哈,《烏龜的華爾滋》裡的迪蓋克蘭,靈感是來自於這隻狗狗嗎?她新出版的幾本書,在大門外擺了張桌子堆了一大落,是任鄰居取拿的意思嗎?好大方啊。踏進公寓,映入眼簾的又是幾大櫃的書,略帶中產氣質的古家具,以巴黎地區來說近乎奢侈的寬敞客廳、飯廳。客廳還有個真正的壁爐,旁邊整齊堆了一大落木柴,廣播輕輕放送。真是巴黎典型奧斯曼式公寓哪,卻多了份舒適隨意,感覺很溫馨。家具上到處擺滿了各式各樣的小鱷魚、小烏龜和小松鼠,都是書迷贈予心愛作家的紀念品,象徵了讀者對《鱷魚的黃眼睛》、《烏龜的華爾滋》與《中央公園的松鼠星期一好悲傷》三部曲的眷戀,這三本書的魔力由此可見一斑。客廳後面走道另一邊,書架的中間,圍繞著書桌,那裡便是凱特琳‧彭歌寫作的領空,與客廳可以說連成一氣,坐在書桌前便能環視整個客廳、飯廳,掌握屋內重要的一舉一動,完全彰顯出作家女主人的身分,果然有寫作人掌握一切的氣勢。
凱特琳邀我在客廳的沙發上入坐,我雖然有些緊張,但是凱特琳安祥自在的態度,讓我放心不少。我們只寒喧兩三句,很快便進入訪談的中心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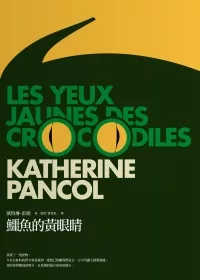 |
 |
《鱷魚的黃眼睛》《烏龜的華爾滋》與《中央公園的松鼠星期一好悲傷》書籍簡介......more |
謝芷霖(以下簡稱謝):《鱷魚的黃眼睛》的繁體中文版2009年在台灣出版,不但銷售不錯,也頗獲讀者好評。
凱特琳‧彭歌(以下簡稱凱):真的很令我驚訝,在所有其他國家的反應也是一樣,可是讓我覺得奇怪的是,對我來說約瑟芬(主角)應該是很法式典型的啊,她住在郊區,又在「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工作 。當我接到一位二十二歲在台灣服兵役的男孩寫信給我,告訴我約瑟芬幫他找到面對生活困難的力量,他很感謝我。我非常訝異,回信給他,他說,您知道,這個故事是非常具有普遍性的。我很高興,之後每次到國外接受訪問都會拿出來講,在西班牙、義大利,該怎麼解釋書在當地的成功呢,我就講述這段插曲,連在台灣都有一位二十二歲的男孩子寫信來了,就像解釋了這一切…
謝:2011年二月,《烏龜的華爾滋》出版。《鱷魚的黃眼睛》與《烏龜的華爾滋》這兩本書都有個共同的主角(héroine)—或者也可說是「反式主角」(anti-héro),如您在其他訪談中提過的—─約瑟芬,和其他共同的中心人物,但是兩本書主題不同,語調也迥異。《鱷魚的黃眼睛》著重姊妹關係、親子關係,特別是母女關係,家庭圖像以及創作書的過程;《烏龜的華爾滋》則把主題放在暴力、夫妻與情人之間的愛及不同面相、男女關係,而且以一種近似偵探或驚悚小說的筆調書寫。在法國,這一系列故事的第三部曲《中央公園的松鼠星期一好悲傷》已於2010年四月出版。這本書不會立刻在台灣出版,所以今天就先不討論這本,以保留一點懸疑。您可以談談這一系列故事是怎麼誕生的嗎?您為什麼創造了約瑟芬這個人物?您從一開始就打定主意要寫成三部曲了嗎?您還要再寫第四本嗎?
凱:我完全沒有想到要寫成三部曲。寫書是很奇怪的,很神祕,當我開始動手寫《鱷魚的黃眼睛》時,根本完全不知道我要朝什麼方向寫下去。我有了第一個場景,可以解釋的就只有這樣,第一個人物在第一個場景發生了一些事,他講了第一句話,從那裡開始,故事一點一點膨脹,膨脹,再膨脹,第一個場景、第一句話和第一個人物開始吸附,就像是放下一塊磁鐵,旁邊的鐵屑一點一點吸附上去,細節、旁枝、其他的人物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漸漸產生,愈變愈龐大,像是滾雪球一樣。一開始的時候,我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我現在回想的話,其實背後是有潛意識在作用的。常常,一本書結尾直到下本書誕生,大概要一年的蘊釀,這一年中間習慣上應該算是不工作的,因為我沒有每天寫作,然而我覺得實際上是比平時更加倍努力工作,因為頭腦把什麼都紀錄下來,就是為了準備有了第一個場景、第一句話後展開的故事。
我在諾曼地有棟房子,早上八點半還沒什麼人時我就去海灘游泳,遇到一位女士,我們一邊游一邊聊天,她在「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工作,非常溫柔和氣,她跟我講述國家科學研究中心這個特別的國度,一些花三十年光陰研究歷史上一小段時期的人,她做了三十年的研究,就在研究「十八世紀流動商販在鄉間兜售的年輕女子日記」。她的精力、熱情和整個生活,都圍繞著她的研究,她寫過書,許多論文,到世界各地演講。我喜歡深入未知的領域,約瑟芬這個人物便是得自這位女士的靈感,這算是有意識的部分。之後潛意識加入,有一天我聽廣播聽到一則新聞,一個姊姊犯了罪,卻讓妹妹去頂罪,我聽了覺得不可思議,一個人怎麼能頂替自己並沒犯的罪行,就算真的很愛她姊姊。又想到我小時候住在同一層樓的兩姊妹,一個長得十分漂亮,另個就很普通,可是大家都只看那個漂亮的,沒人注意那個長相普通的,讓我很為她難過。這些都是潛意識的作用。我想,冰山看得到的部分,就是跟我一起游泳的那位女士,冰山藏在水中看不到的部分,就是所有的記憶,當它們浮出水面,就是餵養故事的時候了。第一個場景,約瑟芬告訴安東尼,她知道他在外面有女人。之後,有了約瑟芬就要給她一個丈夫、一個姊姊、母親、父親、繼父,然後故事就層層建立起來了。常常一開始只像個針頭,後來卻成了一大團毛線球,好多線,許多故事。
謝:那在書寫完的時候,第一個故事看起來像是結束了,為什麼您會想繼續寫下去呢?
凱:習慣上,書寫完,書中人物也就離開了。那一次,這些人物卻不離開,我還是一直在想,約瑟芬、奧恬絲、若伊、菲力普、亞歷山大、艾麗絲怎麼了,我還想繼續講他們的故事。你剛才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字「暴力」,我的確是想呈現出這個世代的暴力,於是才寫了這個男人謀殺女人的故事。
謝:這次也是事先沒有料想到會寫成什麼樣嗎?
凱:這一次就比較有事先組織了,寫驚悚小說得先架構,不過我自己也不知道誰會是殺人犯。直到寫了四分之三、五分之四本書的地方才決定,我給了好幾個開放的線索啊。驚悚小說是一種比較需要精確組織的結構,不過還是同樣的原則,好幾個人物,幾個故事,然後把故事結合在一起。
謝:那您之後還想要繼續寫這一系列的故事嗎?
凱:已經花了七年在寫這個系列,真是夠多了。可是事實上,我卻仍然想著這些人物,做筆記。我心裡已有另一個故事了,我想我會在某個段落把故事接上奧恬絲和約瑟芬等,讓這些人物再次出場。
謝:在台灣的一篇討論《鱷魚的黃眼睛》的文評中,曾把閱讀這本書的經驗與看美國影集相比擬。這讓我想到您在一次訪談中曾提到:如果斯湯達爾(Stendhal)對小說的定義是「拿著鏡子沿路照」的話,您在現代可就是「拿著攝影機沿路拍」了。您在書中有許多豐富的視覺上的描寫。可以和我們談談您對小說的定義嗎?
凱: 我是法國人,卻在摩洛哥(Maroc)出生,在法國、瑞士、義大利、美國都住過,在紐約就住了十年,對我影響真的很大。我二十二歲時為一家女性雜誌工作,那時的女主編讓我學會了怎麼寫作,沒有這位主編,我大概不會走上寫作這條路。她總是說不要用抽象的詞,用具體的詞語,要能夠讓我看到你寫的東西,不要寫些籠統的東西,我不用知道你想什麼,只要展現出來給我看就是。不要光是說,要展現出來(Ne dites pas, montrez. )。不要光說她很悲傷,告訴我她的樣子,她怎麼坐,她的頭髮怎麼梳,她的頭如何枕在肘及手上,展現她悲傷的樣子,而不是只告訴我她很悲傷。告訴我她怎麼哭的,而不是只說她哭了。不要說雪就像件白大衣,陳腔濫調,找出別的說法。這位女主編教了我非常多。我想能寫出第一本書《我,首先》,也歸功於她,那本書展現了很多具體的影像與詞彙,我也把一般法文詞彙做了轉換,從那時起,我找到了自己的風格。後來到了美國,所有美國學院,所有的創作課(creative writing),講的都是同一理念:不要光是說,要展現出來。柯蕾特(Colette)也說同樣的話,她說要用自己的耳朵、眼睛、鼻子、嘴巴來寫,說得有理,當我們寫出細節時,讀者才能瞭解故事,知道你在說什麼,知道啊這是甜的,啊這聞起來很臭,噪音吵得耳朵痛。要用感官去寫,用文字表達感官。不過要這樣寫可就難得多了,每次都要想破頭,想出能打動人心的字句。當若伊在《烏龜的華爾滋》裡開始談戀愛,為了寫她:啊,我心中像是塞了個球一樣的飽脹,哈,這也許是想了三天的成果。這可比只寫「她談戀愛了」還要難多了。
凱特琳‧彭歌 書籍簡介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