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而為人,終其一生勢必難逃一種經驗:因為家人的存在,而湧現尷尬、難堪甚至是羞恥的感受。那樣的荒謬經驗尤其在第三者的介入或凝視時而攀到巔峰。可能是略顯誇張的音量或肢體動作、與現實脫節的社交辭令、對潛規則的蒙昧,或是置身資本主義洪流,卻無能帶給你足夠的、富貴上的顯耀。
其中有種情境特別荒謬,當他,你的家人,什麼也不做,但光是他在外觀舉止上明顯與他人不同的表徵,落入旁觀者的眼中時,你明白,你甚至可以感受到迫切、不容抗拒的期待,期待你解釋為什麼你的家人是這個樣子,甚至認為你有種義務,該分享一路走來的心境起伏。至此,你才懂,置身「被觀賞」的籠子裡的,不再只有你的家人,也包括你。
《背離親緣》作者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要說的,顯然是後述的情境,而他處理的主題依序為聽障、侏儒、自閉症、唐氏症及思覺失調。DNA,長鏈、雙股、螺旋,兩兩互補,其中的排列組合決定了我們身上所要呈現的,以及無法呈現的種種;也因著我們身上所能,或者不能呈現的,決定世人看待的眼神,或者,更早一點,父母的眼神。
安德魯.所羅門從不避諱去指出一件事,父母有他們對於自尊的需求,而這需求有時會走在他們對孩子的感受之上,有時不會。說得更明白一點,有時父母愛的不只是孩子,也可能是希冀在孩子身上找到自身的投射,「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這句話,在多數父母身上都受用,也經常被解讀為讚美。而在父母的期望被「出乎意料」的小孩打亂時,有些父母會長出韌性,竭力適應,但也有很多父母不能,他們選擇放棄。
像作者引述的〈歡迎來到荷蘭〉一文,你可能認為艾蜜莉.金絲利的觀點過度美化,或不夠全面,也不得不讚嘆她恰如其分的比擬,養育身心障礙兒,像是一場陰錯陽差的旅行,妳給自己買了義大利的旅遊書,在腦中描繪著名景點,安排路線,還學了幾句實用的義大利語,卻發現班機竟降落到荷蘭。更糟的是,而你無法離開,無法轉過身回到飛機上,說,我要去的是義大利。
此時,只能在痛苦與折磨下,時間線性前行的規律中,漸漸,緩緩,小心翼翼地拾得欣賞荷蘭的智慧。安德魯.所羅門致力的,無非是走進那些最終決定要「擁抱」異常(或者不以為異常)的家庭,把他們最終「在荷蘭過得不算差」的故事給帶出來。
在作者取樣的三百多個家庭中,每個場景、對白、重大抉擇,他都處理得真實卻又不煽情,我想他深深明白,每一個近似美或靈性的頓悟,均出自反覆的掙扎與對痛苦的耐受,而過度的美化可能會招致不必要的期待,而期待,有時比歧視,更讓人難以招架。
而在這些故事之中,我還看見一個較為隱性,卻又同等深刻的道理,那就是告別之艱難,放手之艱難。對「一般」父母而言,可能早在孩子出世前,他們就在胸中預演千百回,有朝一日,孩子羽翼會豐,屆時他們該以怎樣的姿態,去把曾經緊握的指頭一根一根地,輕緩不致傷地放掉。
但對於那些與眾不同的孩子,以及他們的父母而言,這樣的場景可能來得很早,也極度具體。以作者的語言是,傳承自父母的「垂直身分」與自同儕獲致的「水平身分」,該如何平衡與取捨。
聽人父母思索著是否把自己的孩子讓給聾人文化,手長腳長的父母思索著要不要把侏儒孩子帶去美國小個子組織的地區聚會,家有唐氏症兒女的父母重複地把收容機構放進考量又刪掉,養育自閉症小孩的父母閱讀「神經多元性」的主張時,心中強勢壓境的兩難。最後,也是最為艱難的,子女有思覺失調症的父母,可能得接受,孩子,不過是有著血緣的陌生人。
這些他們必須時時刻刻地警醒,掂量,轉移愛的砝碼。確保必要時他們愛得夠多,才能讓眼前這樣殊異的孩子在險惡處境中可以險險地長好,而在更必要的時刻,他們不能愛得太多,否則順遂放手的時刻將顯得更為艱難,他們恐怕沒辦法扮演好「中介」的角色,甚至是以自身的垂直身分絆倒了孩子起身尋找水平認同的步伐。
《背離親緣》一書也在問,你願意為心愛的人,將自己的想像力展延至怎樣的程度?一如書名,背離了親緣之後,愛不再簡單,不再那麼理所當然。要如何找出彼此之間都能感受到舒適的距離,在高度重疊的人生中,背對背,看往不同方向,又相互依靠著譜寫自己的生命故事。
在作者拜訪的三百多個家庭中,永遠不乏心碎的時刻。兒子是侏儒的老柯林頓,告訴作者,「有次小柯林頓說:『如果我的個子正常,我就會很棒,對吧?』他那時11歲,住在醫院病房。我不得不離開,因為我哭了,感覺十分無助。」
但也不乏美得讓人屏息的場景,小柯林頓的母親,雪柔,即提供了不一樣的景色。一日,她在路上,發現兒子經過改裝的車停在酒吧外,雪柔感到不安,傳了幾封簡訊給兒子,並回家等兒子的電話。日後雪柔把這件事告訴兒子同窗的母親,對方提醒她,「他人在酒吧,是妳運氣好。」雪柔就想:「是啊,如果他(小柯林頓)出生的時候妳跟我說,他會和大學死黨喝酒,還酒後駕車,我大概會樂壞。」
故事與故事之間,也在問你,信還是不信?有些絕色會在萬物匱乏的荒漠中長得驚人地好。或是人生失落境遇的練習,當你在滿園馨香裡遇見一簇長得歪斜的小花,你或許要感嘆它的無依,若一轉身,在荒漠焦土中遇見同樣一朵小花,你反而是要欣喜的,因著你明白每一草莖的抽長,每瓣芬芳,從無僥倖,遑論天生註定,凡此種種,都是不易中的不易。特別是,當你知道你遇見的從來不是誰,而是──你的孩子。
我也時常在作者形容這些孩子與手足相處的碎語中,得到大量的撫慰。這些兄弟姐妹,自小就和與眾不同的手足生活,似乎在更早的年歲就識得了另一種存在的可能,而擔負起特別的身分,他們游移在垂直與水平之間,是家人,也是夥伴,在如深淵般的惡水中,以輕巧而不世故的童真搭起聯絡兩地的橋樑。
在〈唐氏症〉一節中,作者提到伊蓮,一對兄妹的母親。她記得,有次學校同學跟大兒子喬說,他妹妹是弱智。同學的原意是汙辱,喬卻沒注意到,只說:「她是啊。」然後開始談起妹妹的狀況。伊蓮說:「我原本希望能親自教喬那個字,這樣他聽到的時候才不會受到驚嚇,誰知他竟然早就知道,而且不以為忤,就像聽到有人說他妹妹的頭髮跟眼睛都是棕色的。」
這樣奇幻的對白,似乎隱約勾勒出一個美麗的藍圖,同時也長出一些信心,若我們可以在更早、偏見尚未鞏固、歧視斧鑿未深的時刻,在心還很新很柔軟的日子,就遇見與我們不那麼一致的人。也許我們會做出與長大之後的我們,截然不同的反應。不急著劃分界線,不急著以傷害對方來鞏固對於自身認識的確信,甚至,會希望彼此都對這場相遇感覺都好。而這種美質,應可以伴隨我們之後的人生,在那些近似的特質上得到安全感,但在那些相異的表徵之中得到另一種,「我願意學著欣賞你」的強烈感情。
闔上書頁時,回歸到我自身。每個人身上的元素,既有可以切割成主流的同,也不缺徘徊邊緣的異。像是安德魯.所羅門在書中反覆勾勒,也像是林蔭之間行走,有時是光落在我們身上,有時是影子。
我的母親從來看不明白,我天生的憂鬱、偏執氣質。自小我就對於世界的秩序感到不安以及高度欠缺安全感。我告訴她,在我的心中有另一個世界正在高速運轉,裡頭的人物搬演殊詭的故事以及說話方式,而情節往往與快樂背反。對天性樂觀的母親而言,那是難以想像的詭譎景色,而我,她的孩子,竟置身其中。
她試過千萬種方法,要我走出來,學習快樂,她認為那樣的景致比較動人。在數度溝通與爭執「誰的想法比較重要」的戰役之後,有那麼一天她明白到,「我」,她的孩子,就是這麼一回事了。無關好壞,這是不同的生活方式與想像,她明白的那一刻,也終於放棄,放棄所有把我從那個世界扯出來的念頭。相反地,她轉而站在有點遠的距離之外,看著我,在一個她也許一生都感到神秘的世界中,在憂傷豐富的內裡中堆疊文字磚塊,過得不算差,可以掙錢,養自己,甚至,還好好活著,沒做出讓她無法承受的選擇。
一切竟如風箏,手上的線是我與母親的垂直認同,但她選擇把我拉升到適合我的高度,空氣的涼薄與光貼在身上的溫度,均是站在地面的她所無法感受,但她選擇放手,讓她的孩子去認識自己的水平認同。放手,與放棄,兩詞看似孿生姐妹,實則有遙遠的內在。
安德魯.所羅門在〈孩子〉一章所言,「愛一個人,又覺得對方是個負擔,這兩件事並不衝突。其實,愛往往會加重負擔。不論這些父母能否接受自己的矛盾心理,都應該留點空間給自己的矛盾。付出愛的時候,若感到筋疲力竭,甚至開始想像另一種生活,也不用覺得羞愧。」
愛,需要反覆且大量的練習。童年那舊爛的練習簿,在顫抖的小手裡、歪七扭八的線條中,橡皮擦用力輾過紙頁的挫敗,往復的嘗試以及犯錯,終於逐漸認識了每個字的長相。而我們很少去責怪,一個字,為什麼是長成這副模樣,我們只是一再地練習,好好認識它。如書中〈侏儒〉一節,作者寫到,一位記者詢問《侏儒生活及侏儒症》的作者貝蒂.阿德森,個頭矮小的人希望別人怎麼叫自己,阿德森回道:「大部分的人都希望別人叫他的名字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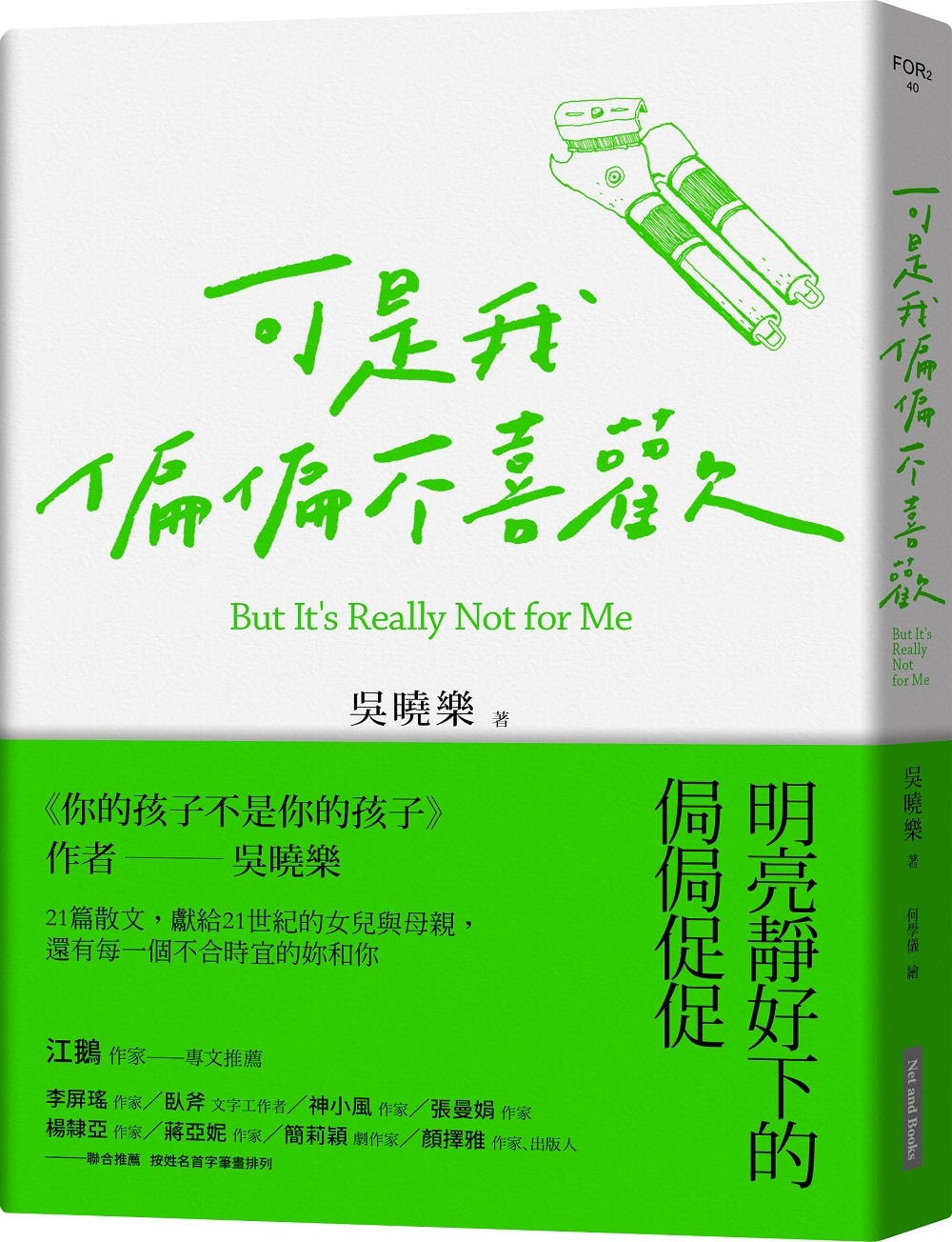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