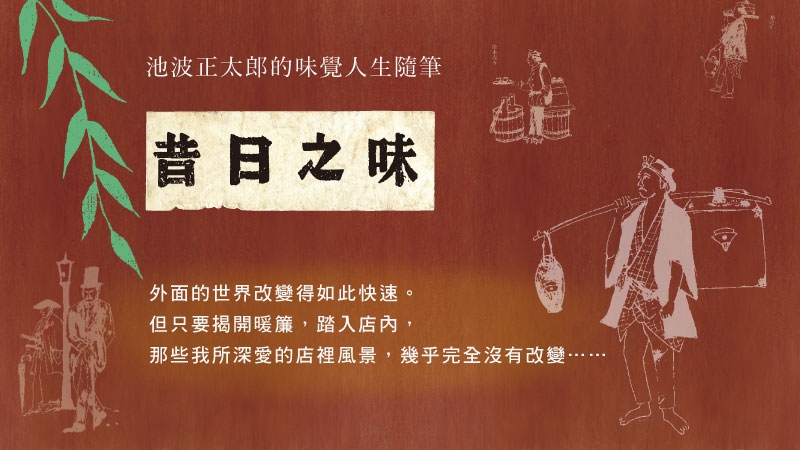
以熱愛美食聞名的老作家池波正太郎,在五十多歲時寫下了《昔日之味》。書中以溫柔幽默、帶著濃厚情感的文字,記下那些讓他低迴不已、陪伴他走過數十年時光的老食物與老餐廳。
每個人的記憶中總有那麼幾道菜、幾間餐廳。或許是數十年如一日的用心營業、讓你每回踏入店門就感到一陣安心;也或許是旅行一期一會、或因為其他原因不知所終,但那味道、那人情,卻始終鮮明的活在心裡。
你心目中的「昔日之味」是什麼?這次,一起來聽幾位深知食物與老滋味之美的作家們,分享他們的「昔日之味」。
文/梅村月
記得小時候,每次出門上街,必須穿越長長的騎樓。即使下雨,只要快跑躲進騎樓,根本不必撐傘。它委婉劃開了天空與車道,紅磚頭砌成的拱式走廊,除了遮日擋雨,更給人一種舒緩陰涼,我喜歡穿梭其間,覺得如此體貼的穿廊,最適合愛飄雨的故鄉,基隆暖暖。
沿街夾道的樓房,大多是做生意的,受到騎樓的庇蔭,不管刮風下雨,人們只要穿進「亭仔腳」,自然就放慢了腳步,趿著拖鞋踏進門檻,就像串門子,談笑間便做成了一樁生意。有賣魚、賣肉、賣雞的……我最怕路過幽暗的雞販,陰森森的店裡不知擺著幾個雞籠,只聽見一群嘰嘰呱呱的雞被關著,客人指定一隻中意的,讓老闆現抓現斬現秤斤。割喉去血拔了毛,剛才活蹦亂跳的雞一下子被扒得光溜溜,只剩下透明的細毛稀疏留在軟癱下垂的脖子上。老闆擒刀一剁,趁鮮成交。
除了賣菜賣肉的,騎樓下還有水電行、西藥房、理髮院、布莊、乾洗店、豆漿店、麵攤,支援著小鎮的食衣住行。麵攤就在騎樓的最尾端,面對媽祖廟,再過去,就是鐵路平交道。遠遠還不見火車的影子,柵欄就咚隆咚隆放下,早早攔住過往的行人車輛,叮叮噹噹高分貝的聲響,讓焦躁的司機更焦躁。
從小就曉得媽媽口中的「阿炎姨那兒」,指的是那個沒掛招牌的麵攤。肚子餓了,媽媽只准我們吃麵果腹,不准去柑仔店逗留。阿炎姨是一位純樸寡言的婦人,永遠默默低頭煮麵弄菜。她膚色黝黑,燙著一頭及肩捲髮,年紀看起來比我媽大些,總是站在鍋灶前,左手拿著幾把交疊的竹篩子,右手擰著麵,看客人點什麼,她就下什麼。店的窗台固定擺著四個大竹籠,裝著油麵、陽春麵、米粉和粄條,不管點哪種,價錢都一樣,看你要吃湯的還是乾的。湯麵可另添餛飩、肉羹或魚丸,乾麵卻賣一種:阿炎姨把熟麵甩乾,倒扣入碗,舀一匙油蔥酥、一點醬油膏,再放兩片白切肉、幾根豆芽菜和韭菜,端到客人面前。
油蔥酥與鹹中帶甘的醬油膏,是阿炎姨乾麵僅有的調味料。就僅僅這樣,卻始終吊人胃口,氣味永遠引人鄉愁。一抽一束的麵條,飄著裊娜白煙,吸進了鼻腔,送進了嘴巴,滋味頑固得一成不變,卻叫人百吃不厭。
 麵條飄著白煙,送進嘴巴,滋味頑固得一成不變,卻叫人百吃不厭(攝影 / 簡隆全)
麵條飄著白煙,送進嘴巴,滋味頑固得一成不變,卻叫人百吃不厭(攝影 / 簡隆全)
 (乾粄條)僅有油蔥酥與醬油膏,卻始終吊人胃口,氣味永遠引人鄉愁(攝影 / 簡隆全)
(乾粄條)僅有油蔥酥與醬油膏,卻始終吊人胃口,氣味永遠引人鄉愁(攝影 / 簡隆全)
水霧氤氳的鍋灶旁,立著一台兩層玻璃櫃,擺著豆干、紅燒肉、臘腸、海帶、肝連、吉古拉(竹輪)等小菜。叫麵點菜,只管用指頭比一下,吩咐燙青菜時,就問問阿炎姨今天進了甚麼菜。我常懷疑店裡的菜是不是阿嬤種的,不然味道怎麼跟阿嬤菜圃的一模一樣。阿嬤生前,總是自己種菜,自己播種、施肥、澆灌,當然不灑農藥,揀菜洗菜得仔細挑蟲,特別麻煩。不管汆燙或清炒,吃起來都細嫩香甜,藏著泥土香。
坐在竹凳子上,天花板懸著幾台電風扇拼命轉呀轉,一陣陣溫熱的風,吹得我頭髮花亂。撫著頭髮,我低頭喝湯。從窗戶望過去,是媽祖廟安德宮,廟口有一座高高的舞台,每逢節慶,舞台總響起鑼鼓嗩吶胡琴,上演一齣齣悲情破音的歌仔戲。有時在週日晚間播放電影,群眾簇擁在台下,抬頭望著帛布放映的畫面,痴痴的。遇上了選舉,各候選人輪番來此登高一呼,披著彩帶,拿起麥克風口沫橫飛。依稀記得自己第一次粉墨登場,也在這露天舞台上,七歲的我梳著兩把小辮子,塗著胭脂,跳了一場「賣湯圓」。
如今紅磚騎樓已拆,但麵攤仍在。只不過站在鍋灶前招呼客人的,不再是阿炎姨,而是她的姪女。那張樸素敦厚的臉,與二十年前的阿炎姨身影重疊。她沉著、耐煩,一口氣手持數把篩子,記住十幾個客人的點單,這桌那桌要湯麵乾麵肝連燙青菜,從來不會搞亂。乾麵依舊裹著深褐香稠的調味料,餛飩肉羹魚丸一貫手工自製,小菜也照著過去手法做。麵的湯頭輕盈滴溜,最後一勺魚露,是不外傳的祕方。切薄的台式臘腸,沾上薑絲醬油膏,是微甜的童年味道。孩子們點了湯麵,逞強舀進了兩匙辣椒醬,模仿外公嗜辣的豪邁,染得整碗紅暈暈的。而我那碗,只撒了一撇胡椒粉。

切薄的台式臘腸,沾上薑絲醬油膏,是微甜的童年味道(攝影 / 簡隆全)
梅村月
生於台灣基隆,大學畢業後在美容時尚雜誌任編輯數年。1997年結婚,婚後隨日籍丈夫移住日本東京六年,後定居神戶已逾十年。2009年11月成立部落格「Moon's月光食堂」,發表料理札記與生活隨筆,其細膩抒情的文字、帶有溫度感的攝影,及獨到的配色構圖,吸引了眾多關注。著有《媽媽愛,便當》、《回家晚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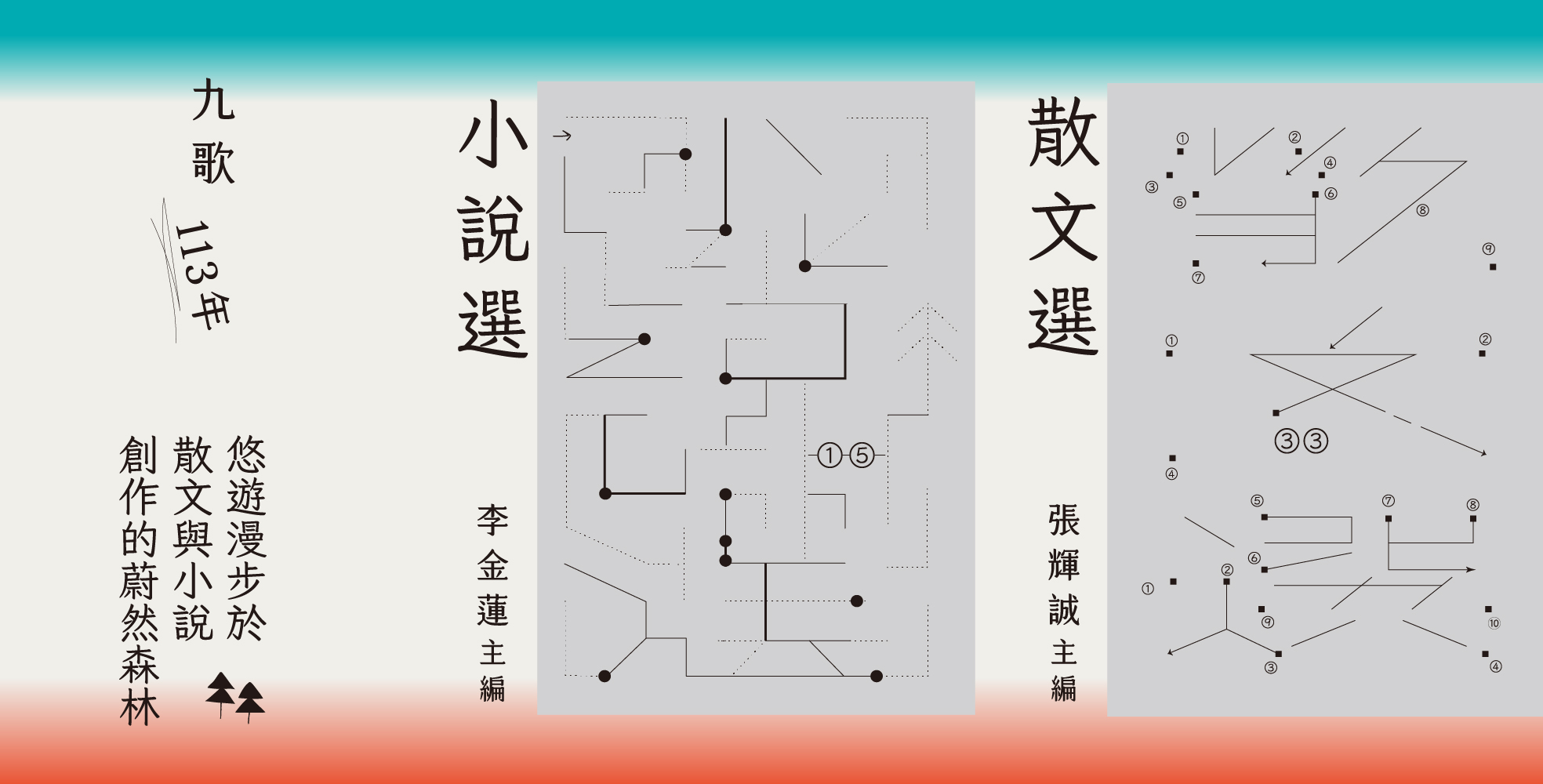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