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年前到戶政事務所更改戶籍的時候,我內心並無猶疑,因為此生有機會做台南人、還是鹽水人,使我感覺無理虛榮。第一年經歷蜂炮齊飛全城跳腳狂喊,諸眾隨神明行腳遊街獻身煙硝石火,身在其中的我因為深深戀慕當夜神鬼人共處一時一地、世俗與神聖同顯的激情,儘管小腿都是瘀青,內心至為感動。
我並非一直可以這樣平和看待此類情事,是遠離了台灣神明管區、再歸來,對鬼物及懸浮在世間的怨念才不再過分敏感。現在除了偶爾還做一些虛實不分的夢,提點仍與我相連不斷的那些逝者執念,日子已逐漸進化到得以自我保護。
或許是當時居住的處所離荒野很近,與空氣中的微妙變化也親暱相聞,搬到鄉下那幾年我才感應漸深。受侵擾最盛時我做過一個夢:一座筆直的山壁立在我的老家客廳,山壁上遙遙站了一名女子,眼看就要跳下來。我拉開喉嚨喊她,要她冷靜。懸崖上的女子沒有聽見,直直落下到我面前,成一大灘模糊血肉,毫無轉圜。夢中的我反應很遲,沒有作噁或驚惶,只是擔心來往的人受驚嚇,於是雙手揮舞著一直阻止門口的人進來。我從未見過那個一心尋死的女人。
除此之外,還有些難以解釋的經歷:
那天早上睜開眼睛,我就發現事態不對。我沒有動彈,盯著天花板,用去一分鐘認真地感覺自己究竟能不能起身。
又來了嗎?和兩個月前一樣,一覺醒來頭暈目眩,連坐起來都沒有辦法。當時醫生搖頭表示無法認定這是什麼病,只能頭暈開止暈藥、胃痛開普拿疼,先把症狀壓下來。我吃了藥,感覺身體被勒令停工,不再於時間空間向度裡無理旋轉,但我知道沒有那樣簡單,方才那種整個內裡的不舒服無法言喻,也無法指明,只強烈知道我的身體忽然不是自己的了。一切毫無預兆,唯一閃過我腦中的,只有前一日剛從阿里山回來,我和雲南朋友沿著廢棄的小火車鐵軌迷路好久,那沿途景色美得不可方物,簡直不是人間有。「這裡不是人間吧。」我的腦中甚至真的浮現這句話。
沒有人能夠確認任何關聯,隔日我也沒事似地重返日常,直至這回,更為慘烈。如慢火燜燒的身體服了藥過後平靜一陣,夜半卻突突胃疼僅能送急診,護士循規為我注入點滴,十分鐘過後眼睛腫成一條線,我奮力呼吸,嚴重過敏。「這很溫和的,我從沒見過有人對這種藥過敏。」護士驚訝地說,我虛弱苦笑。
我暗自揣測是前日為安平老屋點淨香惹的事。朋友領我到天公廟祭改,也到她熟識的地方問事。阿姨說妳夜訪廟宇歸來時常染風寒吧,要我剪去長髮;另一位花蓮的天眼通阿姨說:「妳的名字是個難字,而且帶水。妳不需要這麼多水,會招引魂魄跟上妳。」可是我特別喜歡自己的名字,儘管意志顯弱,對於身為人應該持有或表現的本質感到懷疑、易被鬼物沾染,但還不會放棄名字的。
這過後好長一段時間,我感覺自己的眼睛被換過一次。也像是忽然戴上合眼的隱形鏡片,車馬人聲看起來毫無二致,卻切實地感覺每事每物上都層層覆蓋了疊影,連空氣的質量也彷彿可以描述出來。有時候還適應得不好,夜裡會猛然醒來,睜眼就再也不能睡去,只有坐起來唸一點經,等天終於發白;身體還沒有平衡完全,脖子歪了好幾天,像《河流》裡的李康生,有數夜實在承受不了莫名的苦,只好坐在床邊委屈地哭。
也由於這副無法控制的身體,那段時日格外意識到某些自己害怕的事物。我絕少害怕,或者意識到害怕,但這次經歷給了我一種從未體驗的、深深的恐怖感,仿佛也不是害怕,而是恐怖,像是緣由很深以致於不懂得要害怕了,只能伸手攬住一根浮木,不信不可,不可不信。神明陌生的慈悲把我從世間很邊緣的地點調度回來。我眼睛裡的世界與人物彷彿歷經一次重新對焦。比起左眼毫無用處的飛蚊來說,這種奇異的視覺錯亂令我安心又著迷多了。
我把這些細節說給我的心理醫師聽,星期五的下午,醫師耐心地聽完我以「卡陰」來代稱的事件之後,試圖以不帶任何價值判斷的口吻對我說:「妳知道嗎?在醫學上,這些症狀,就是典型的恐慌症。」他向我解釋,病者不見得要有任何具體害怕的事,但光是等待下一次發作,就足以使他們神經耗弱。我皺著眉頭說只覺得空氣裡充滿看不見的敵人,或許不是敵人但還無法分辨關係,夜裡的貓走狗鳴使我草木皆兵,胸口坐了敵人們的鬼物,他們的手掌不在乎禮節地搓揉我使我發熱,但我一句咒語也記不得。
大體說來,我十分願意以美學角度相信四散飄蕩的魂魄傳說,也同時相信文明製產的永生怪物,好像那便是我們的宿命:身而為人,自遠古塵土而來,同時為科技機械藥物所染,必定有外於你的力量指使你、左右你,不可能獨活。無兆失控之後,接受自己是一個無法抗拒無形力量召喚的人,或者是一個把暴力壓抑過深的人,好似便不再那麼在意自己,也不再那樣恐懼隨波逐流,或特立獨行。
只是有時,它們地動那樣不期復返,最近一次,是即將降落在戴高樂機場前的半小時。這是四年前離開之後第一回,我捨下周歲的孩子,獨自回到歐陸。飛機開始下降的時候我的心臟忽然奔上耳膜咚咚急敲,周圍的空氣瞬時稀薄,我把窗遮拉起來,臉貼近冷冽的窗口試圖穩定呼吸,額頭開始滲出淡淡的汗,胸口絕望幾乎瀕死。短短十多分鐘間有幾次我勉力把頭抬起來看看四周,飽滿的機艙裡有人沉睡有人觀影,兩名中年女子在洗手間前招呼彼此。萬事平凡空調無誤,我被自己攻擊,沒有人跟我一起受苦。在最平常不過的時刻被那些神鬼與願望記起,仍猝不及防,像最初那樣無助悲傷。
羅浥薇薇
八○年代出生。台灣苗栗人、左營長大。
現職為幼兒電視轉播與保育員、不自由創作者,未來不詳。 著有小說《騎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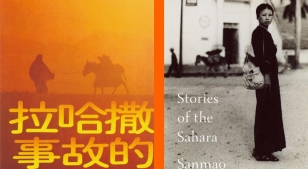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