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患有失眠症的人無法真正入睡,也無法真正清醒。」電影主角說,還好這城市「幸福」的運作,是以無所不在的「廣告催眠」為本質軸心,並不歡迎太清醒的人,也就是這城市跟主角其實都在「幸福」這程式裡夢遊,而泰勒‧德頓就是個駭客,解碼了「當幸福變成迷信時,正是近代人不幸的開始。」
他起床時,意識仍如鉛石沉在大海裡,身體尚未恢復訊號,這個月有沒有真的熟睡過?這問題無法辨識,他像快當機的硬碟還在緩慢地開機中,螢幕保護程式開啟,維持作息。
他的一天先由幾粒彩色的維他命藥丸與營養補充劑開始,他的起居空間走的是北歐簡潔風格,從細節裡看得出主人堅持的品味。他著裝好出發,走入街道與機場明亮的通道,有條不紊的手扶梯與行李通道運作,打開隨時更新的 3C 配備,喝固定品牌的咖啡,一看就知道他是個白領,入目皆是排列整齊的機場座椅、恆溫的空調,偶爾會想起該去健身房跑步機運動一下……他融入生活的環境,簡潔白淨的線條撐起這個大文明(臉色接近慘白),跟上吧!這都會的規律速度,他抖擻的裝扮,禁不住瞬間入座起飛時的疲憊,當手機暫收不到訊號時,五官警戒瞬時崩塌,是的,他是個白領,處境也像浩瀚實驗室的一隻白老鼠。
這是「泰勒‧德頓」,沒人知道他原來的真名,他的角色後來被稱為「敘事者」,在他遇見泰勒前,他有條不紊地活著,內在愈崩塌,他外表的光鮮水泥漆愈塗得厚實,一個宛如新生兒的老者,城市的幸福口號會提醒他甦醒、公司的量化管裡會把他精準數據化,他是腐朽的精裝版,裡面灌滿了讓人精神重振的塑化劑。
泰勒‧德頓的故事,讓我想到基努李維說的:「或許,你們需要快樂地生活,但我不需要。」
那麼,屬於我們整體的快樂生活是什麼?「哪一種家具最能代表我?」敘事者在還沒有變身為「泰勒‧德頓」前,總是拿著平價家具型錄如是想著,手癢似地不斷地下單買家飾、昂貴服飾,讓自己看起來更有與眾不同的「風格」,但與眾不同,就是以「眾」為前提,確定模組吻合了才有的考量。
敘事者穿著讓人能辨識出他是大商社的筆挺西裝,生活的一切都往「成功」的標準前進,訓練有素地「向中看齊、向前看」著,彷彿有神拿著尺丈量,讓他不能出錯也不能劃出線,哪裡來的規格?這麼像我們周遭的你我他,就像他在影印時,抬起來看一切恍然時發出的囈語:「失眠讓我感受不到真實,一切都在被複印中。」的確,若把他置換成他人,恐怕一時也分不出差別,他那身「同中求異」的穿著,只是個入場券,讓他得以進來我們這個「Happy Together」的遊樂園區,裡面無論快樂、幸福、性福、美麗、英俊都有它的分門項目的標準,也有「取得方法」的詳細解說,而我們學校教育是一套「說明書」,我們習慣跟隨大家魚貫而入,一同進入一個「前往幸福」(且永遠在前往中)的 Wonderland 裡。
當然,這過程中鮮少人會警告我們:「當幸福變成迷信時,就是近代人不幸的開端。」
所以,敘事者也跟我們一樣,出現了一些小小的症狀,比方失眠。他開始去各種癌症團體找尋慰藉,如「睪丸癌的安撫團體」(他並沒有得此病)等,敘事者發現:「這麼坦白的陌生人,讓我想哭,促使我回家睡得比豬還沉。」於是他像上癮地找各種團體,「他們哭得兇,我哭得更兇。」那些團聚的場景不同於敘事者生活的環境,他們的空間閃著老式日光燈的灰白、牆壁角落有明顯的掉漆、那裡的人們穿得不若他這般工整,他最喜歡的病友Bob總穿著領口歪斜的Polo衫(Bob因荷爾蒙療法男生女胸),每次抱緊他哭泣,他如同小Baby般感到溫暖。直到出現跟他一樣,需要沾點別人悲傷的醬汁,才能囫圇吞掉自己人生的瑪拉,這才點醒了他的「疏離」。這一次,他無法再入戲哭泣了,他再次回到他「過度清醒」的世界,在他自認品味不凡(其實像實驗室)的裝潢中「無眠」。敘事者渴望清淨、無論視覺還是聽覺的,那無塵室的家卻無法阻絕內心的灰塵大量飄落,隨時為下一秒可能的失去警報著。他說:「患有失眠症的人無法真正入睡,也無法真正清醒。」
還好這城市「幸福」的運作,是有大量配套措施的,以無所不在的「廣告催眠」為本質在運作,並不歡迎太清醒的人。也就是這城市跟敘事者其實都在「幸福」裡夢遊,這程式從小就被植入眾人中,不容許駭客來破解。
而泰勒‧德頓就是一名駭客。
在「敘事者」家爆炸後,「泰勒‧德頓」正式登場,當時主角行李也被送丟了,他最擔心的是那些能「識別」他的DKNY等名牌服飾都去了哪裡?學校給他的「進入社會說明書」開始失靈,他打給飛機上巧遇的「泰勒‧德頓」,這個一看到敘事者就說:「你的笑聲帶著絕望。」的陌生人,與他狠打一頓架後,把他拎回家收容。泰勒家基本上就是個到處會漏雨的廢墟,門快垮、水龍頭生鏽、床柱傾斜、壁癌遍布,跟他的「家」完全不同,但他一趴在發霉的床墊上便熟睡了。所有名牌隨身物全都消失後,他這個無名者就沒什麼好擔心的,「泰勒‧德頓」持續將他的程式更新,藉由一場又一場的幹架。
泰勒‧德頓是「失序」的總和,兼差當放映師,將 A 片片段放入家庭電影中、在大飯店當侍者,會對甜點放屁,往鍋子裡擤鼻涕,他生活主軸是製造混亂,幾乎夜夜找陌生人打架,他不贊成上健身房,宣稱:「男人的成長是靠手淫跟自我毀滅。」

如果敘事者的人生是一連串的「加法」,泰勒就是一連串的「減法」,他的中心思想是:「廣告引誘我們上班,買些不需要的東西,而歷史遺忘了我們,在這時代沒目的、沒地位,我們的大戰只是我們的心靈戰爭,我們的恐慌是我們的生活,從小看電視,讓我們以為能成為 Somebody,所以我們很生氣。」而他手段激烈的「斷捨離」的確奏效,「你的生存讓你遺忘了你的才能。」他警告著。泰勒的打架運動引來烽煙四起,儼然成為一種新興「宗教」,不認識的人夜間集合,打得頭破血流,豁出去打,破除階級地打成一團。城市的白老鼠們走出自己的無菌室,任憑內心困獸出來嘶吼,在破舊的地下室分享著對方的汗水與脆弱,一句旁白:「打架,證明自己不是孤獨的。」慢慢的,敘事者發現生活中都是自己教派的教友,全國都有分會,互相罩著彼此,「鬥陣俱樂部」成員在各個城市走路有風,破壞著原本老大哥設立森嚴的幸福教規,他們組織成一支軍隊,像在動物園裡的作亂一樣,泰勒引燃了動物們想把園區變回原始叢林的欲望。
最後,隨著泰勒消失,敘事者才發現泰勒是自己的分裂人格之一,當泰勒是主性格時,他策畫了一連串破壞計畫,好友大奶 Bob 因作戰計畫「殉職」了,依照他們的信念:「行動中沒有名字,死了之後才有名字。」Bob 求仁得仁,將煙花盛世視為烽煙戰地,他們的作戰目標是什麼?是那個不准他們不幸福的豐饒之地,而他們不像其中的子民,一同享受物質加法的空虛。
當「幸福」被宣傳為只要你努力就可以拿到,彷彿神就是銷售此產品的業務員,整個宇宙就是訂單服務處,不幸福就是你的責任,沒有那樣的房子、衣服、學歷、職銜、外貌、孩子,是你對「幸福」還不夠認真?而你看起來是大家眼中的「幸福者」時,你是否能繼續讓自己看起來更「幸福」?你花了多少力氣在模仿別人行銷的「幸福」?當擁有那麼多「幸福」時,你是否願意受困在自己的幸福裡?那沒有盡頭的競標、打卡、下注、加碼,在無法低調的時代,幸福跟人持續被量化。
敘事者自問:「但破壞計畫之後下一步是什麼?」電影最後那個象徵美好未來的金融大樓,在他眼前爆炸了,很多電影也總是炸掉金融高樓,觀眾總既想看這幕又害怕著這幕。或許大家與他這小白領一樣,知道金融衍生性商品「幸福」正把持整個世界,時時更新教條,人人「不幸福、吾寧死」地從容赴義活著。如果炸的是海市蜃樓,那不等於沒炸?Simon & Garfunkel 60 年代的歌〈沉默之聲〉便預言了人們會像自己製造的霓虹神跪拜祈求,許多國家的金融中心都像神之高塔般地存在著,且日夜不關燈,堅定「信眾」的信仰。
然「幸福」根本不需要想,想了就不會幸福。人活著不踏實時,才有幸福這假議題。於是主角「敘事者」無論加入世界的拜物教,或進入泰勒的存在主義裡,都無路可走。他像做夢的孩子,不是活在自己的噩夢裡,就是無法入睡。在這已睡得太沉的世界裡,他從驚醒到消失,「泰勒‧德頓」是每個孤獨者的夢遊體,連半個敵人都找不到,從頭到尾都是他與自己的鬥陣。
「幸福」就是這麼孤獨的答非所問,人類賴此在史上最久的盛世中,一起進入了這政商共謀的假命題中,分搶海市蜃樓。泰勒‧德頓,是孟克畫中的吶喊,如此大聲也被封存於無聲中,然即便或有眾前例如此,「敘事者」最後仍願強韌如詩,而非可拆解的標籤,人類終究不是幸福的填充物。
﹝電影簡介﹞
《鬥陣俱樂部》為 1999 年電影,由大衛‧芬奇導演,改編自恰克‧帕拉尼克 1996 年的同名小說,主角分別為布萊德‧彼特、愛德華‧諾頓和海倫娜‧寶漢‧卡特。故事描述主角是個患了嚴重失眠症的上班族,每日執行重複的工作,為了找尋生活意義不斷購物,東西愈多愈感空虛,因此找上了各種病症的自助團體,遇見比他更悲慘的人們,藉以舒緩自己的焦慮。
直到遇到賣肥皂的商人泰勒,兩人成為好友,並且沉迷於互毆,之後成立俱樂部。會員擴張迅速,泰勒也被視為如宗教領袖。之後,泰勒開始發動會員進行各種破壞,炸毀了不少建築物,主角企圖阻止時,卻發現了事情真相。這部電影剛上映時,評價兩極,之後發行 DVD 才引起熱烈反應,並成為近代反映都會現象的經典電影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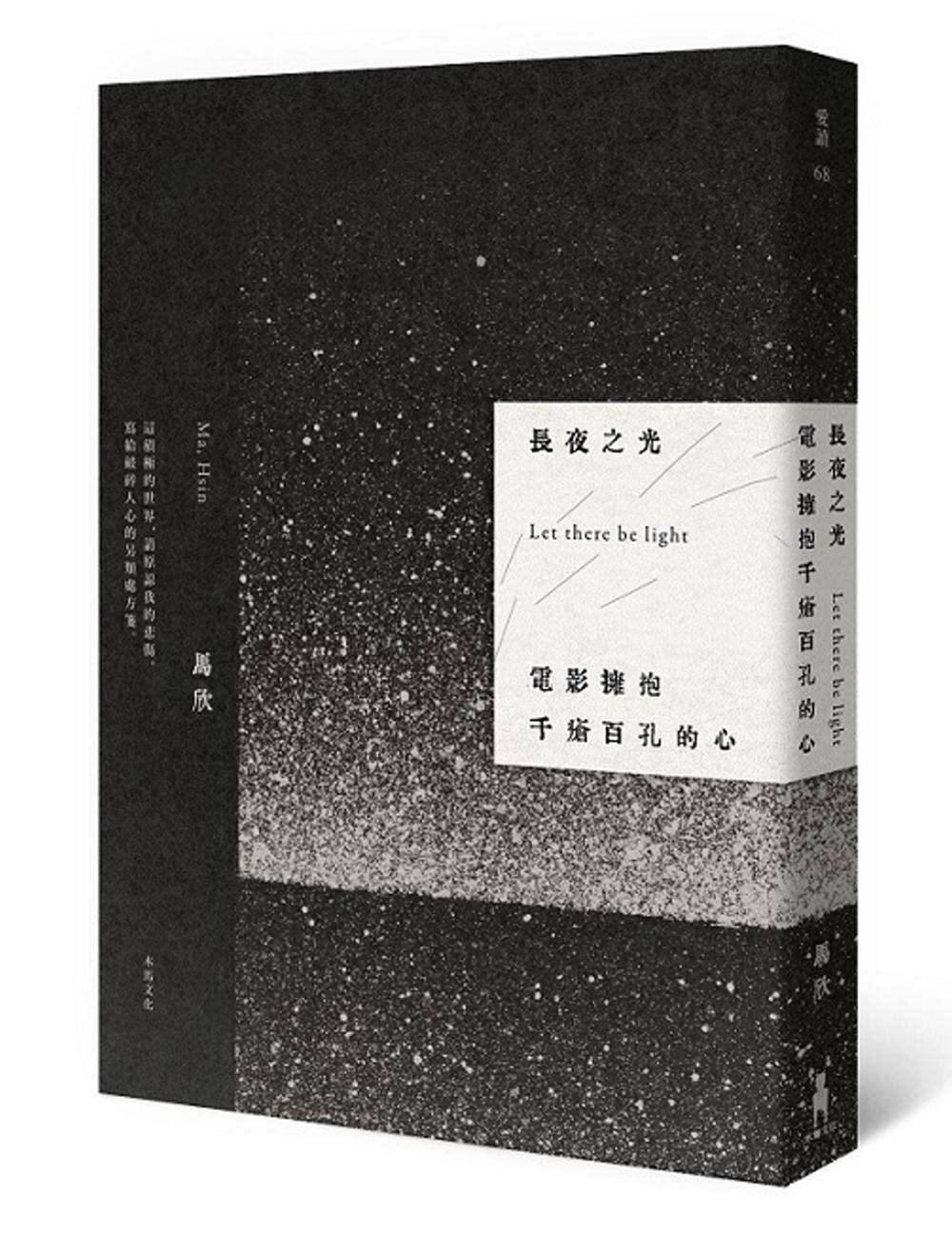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