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陳昭旨)
身邊總有幾個朋友,你會說他們懂得過生活。這樣的人未必富,卻定然足;那知足表現在識得撿好東西吃、挑好街區住,身上穿的不以牌子名氣嚇人,常有棉、麻質料的種植與織工故事好講。其中再有幾個人,把照顧人的心思動到花草植物上頭,散步走過他家那條巷,極容易指認位置。
如作家愛亞在新書《安靜的煙火:我的臺灣花.樹》裡是這麼描述她的陽台:「下面一排花架裡黃色馬櫻丹雜種在可以蓬垂枝條的碧綠武竹裡,上面一排是怎樣種怎樣向天空直苗苗抽長遮擋住窄巷對面鄰人眼的紫花翠蘆莉,間著幾缽開放時紅艷火燃得幾乎有炙燙溫度的九重葛。」
「植物長得好不好,跟這家的氣運有關。」愛亞認真地說,這可不是在搞靈異,她親眼見過太多。前些年,家中丈夫久病連年,過世後愛亞尋思種點白花,卻連朋友說不照顧也能長好的日日春都養死了。她對門的婆婆原來擁有整條巷最漂亮的陽台,不料有幾天沒看見人來澆水,植物很快枯軟了;後來才知道是婆婆獨子意外過世,對生命的希冀滅了,人也再無心照看花花草草。草木本無情,卻自能感應生機。
愛亞極受歡迎的小說《曾經》曾改編為電視劇,小說以她的人生為素材,曾提及寫作時參考初中時期紀錄生活大小事的本子。問愛亞現在還記嗎?她大方拿自己開玩笑,說現在年紀夠大了,回想起的淨是年少事。「在路上碰到兒時熟悉的樹木,拿一片樹葉在手裡搓揉,聞那味道,馬上所有的感覺回憶都來了,順著線頭可以拉出一長串記憶。」隨父母自陸來台後,愛亞童年時住在新竹寶山雙溪村,和村裡的客家小孩玩在一塊兒,樹木的果子、花朵,皆是隨手可得的玩具。
趁父母午睡時溜出門,愛亞頂著夏日午后的炎熱日頭,也要看遍村子周遭的樹木。「我爬到高處,居高臨下的看樹、看草,慢慢發現植物都有不同的樣貌。腦子裡也有了飛到高處看世界的想法,後來寫成了小說《是誰在天空飛》。」
懂植物的孩子可有得玩了。回家路上,女同學摘下榕樹葉,一搓一捲折成樹笛,放口裡吹起學校教的歌謠,另一位同學以口哨和聲,喊愛亞「你唱,你唱!」小時候鬧過的糗事也記到今日,愛亞把苦楝樹的果子當成雜貨店賣的蛋皮花生米,拿起來啃覺得味道不對,剝開外殼也不見花生米,被同學笑了好久。回憶中還有淡淡的甜,高中時,一位男同學與愛亞特別要好,有次拿刷淨葉肉、顯露錯落葉脈枝節的葉子書籤送她,「可惜高一的女生已經很知道了許多事,但高一男生只能做到這樣。」書籤徒留書中,情意在多年後化為篇章。
因此讀愛亞書寫植物特別入心,她不單只寫花樹,她也不寫任一種花樹,而是專寫在她生命裡有過位置的花樹。讀愛亞的文字,會有種作者對著你說話的感覺,就在身旁般貼近,用著易理解的語言去描述頗有共感的經歷,無論那喚起了屬於你或你父母的回憶,讀來趣味盎然。
童心和幽默在愛亞的寫作裡從不缺少,「我現在玩臉書,有8年級的臉友說他們有老靈魂。這些小孩有什麼老靈魂哪?我都沒有了!」拿出隨身手帳,愛亞笑說,外邊的尼龍套是女兒不想要的,送給她用;手帳翻開裡頭有寶,記載2014年星座運勢,警告某月某日萬萬不能簽約。愛亞教寫作也頗另類,不以培育出「作家」為目的,「我告訴學生,寫作是為了讓自己快樂。」在她班上有誤闖的電腦工程師,現在學著描寫身邊的植物,一手好文章。
愛亞絕對算多產作家,她持續書寫,持續吸引著新一代的讀者。初出道以長篇小說、極短篇見長,近年散文寫吃、寫植物各有風采。「寫小說和散文就像改制服,誰都想在同中求變化,把褲子改緊一點,鞋子換穿個尖頭或方頭。」愛亞說,寫作上她不想為了誰而將就,求的是一直看到自己的變化和進步。她話鋒一轉,談到停止進步的可能,「人要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是不能寫了,我會寫到旁人或自己覺得退步的那天。」
採訪告一段落,請愛亞到外頭庭院拍照,暫時不談寫作,聊起她養的寶貝貓。問她,貓會不會找植物麻煩?「抓啊!怎麼不抓?就讓牠抓吧。」
〔愛亞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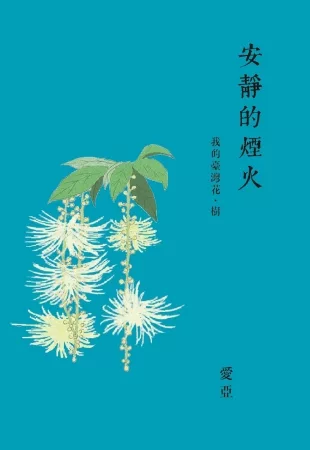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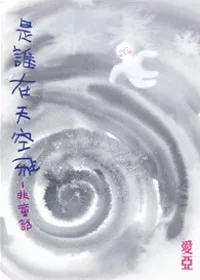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