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但以理)
年輕的導演Raye,是紀錄片《十二夜》的創作者,更是發起者,是她的發想與熱情啟動這個拍攝計畫。大概沒有人會懷疑她對流浪動物的熱情。但與其嘗試形容那樣的熱血,不如說一個她的親身故事。
大概是國一國二的年紀,Raye家住台北市吳興街底,當時她聽班上一個女同學說到附近的流浪狗收容所看到火化,她想起平常在每週固定的日子,總聞到一股燒焦味,當這個說法與生活經驗的線索連在一起,她便決定和這位女同學一起去一探究竟。
那是Raye第一次進入流浪狗收容所現場。
那時難過又年輕的她們,把一窩新生小狗帶出來,先請街角雜貨店老闆娘幫忙,「用現在的話講,就是『狗中途』。」再自己做傳單、貼傳單找人領養。Raye還記得,傳單上的聯絡電話,就傻傻寫上自己家裡的電話,「若真的被家裡接到一定挨罵。」
她也曾利用假日到中正紀念堂發送傳單,上頭寫的是關於流浪狗收容所的現況。她一面說一面微微仰頭回憶,她還記得那一天搭的是22路公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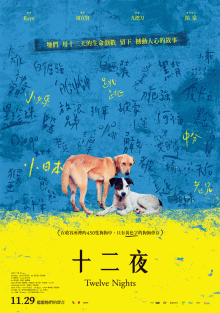
《十二夜》在呈現上一個很大的特點在於,攝影盡量以狗狗的視角——離地約30公分的高度,讓觀眾看到收容所裡的種種。而看過電影的觀眾若注意到許多鏡頭的拍攝,看著工作人員的鞋跟如何靠近,若更有些攝影知識的觀眾,與週邊有效角度稍微計算,會發現這鏡頭與之中的工作者是多麼貼近。
紀錄片拍的是這些狗的運途,但劇組與這些在收容所裡工作的人,是如何相處的呢?「其實我們刻意隱藏了收容所裡種種『人』的狀況。在這裡工作的人,多是社會上比較弱勢的老人家,這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也許有人會覺得他們並不是怎麼溫柔和善地對待小狗,但我們覺得,這些老人家並不知道這些。尤其,真正的問題是出在目前動保法的設定與機制,還有棄養的人們。」Raye對這點的想法很清楚,「我們並不想譴責在收容所裡工作的人,這個惡劣的環境設計不在他們,整個機制的設計也不是他們。」
片中唯一有從人的角度,談到之中工作者的一件事,大概只在獸醫標注執行安樂死程序的那一段落,當我們一談起點,Raye也記得很清楚,在執行上,這部紀錄片希望很有意識地「盡量隱藏人的狀況」。

(攝影/但以理)
不僅以小狗的角度來看,故事也以小狗的角度來說,讓觀眾對片中好幾隻小狗產生感情與認同,也才不需要更多控訴或說明,讓想傳達的感受透過影像傳遞出去。而在說故事的技術上,很明確的做法是為之中好多隻小狗取名字。「我們就是每天一早就去,也不知道今天會拍到什麼。但有些小狗就是會很快抓住你的注意,讓你看見牠的故事。每天晚上一回到飯店,大家就一起看今天拍攝的片花,看看有哪些故事能連貫起來。」
那些頗有巧思的名字是怎麼取的呢?「就是大家看邊片花,邊想怎麼串連故事時一起取的。一開始的一兩天,我們也不能認出全部的小狗。」想起當時每天的拍攝流程,Raye自然又想起,「每天早上攝影師阿賢會先進去拍,一早收容所會先把之中已經在夜裡死掉的小狗揀出來,我們也必須整理,今天又有哪些小狗過世了。」
關於拍攝這部電影,之中當然有一種動了真情的悲願成分,Raye對於動保法修法的推動很有熱情,「作品即將完成的時候,我有些不安,因為好像沒有把能做的行動告訴觀眾,是不是不對?」後來九把刀明確指出,這些影像已經「呈現了生命莊嚴的事實」,這已足夠。最後電影的樣貌也就確定下來。
另一個讓Raye不安的點,則是許多熱愛小狗的人,縱使對這電影想談的主題有興趣,卻可能不忍心去看。Raye告訴我們,「我想讓愛狗的人也敢進來看。電影呈現的,沒有多加煽情,就是狗狗真實的生命故事。我們如果愛牠們,就應該要有勇氣面對這些生命故事。」
採訪即將結束前,我們攝影說,這電影的收入會捐出去幫助流浪動物,他要支持,但又不太敢去看;不然把電影院裡特別壞的、不太有人買的位置買下來當支持好了。Raye毫無遲疑,給出「不行!」兩字。她希望這些故事被更多人瞭解與看見,不只是一次的支持或募捐而已;我想,她確實還記得自發地搭乘22路公車,到中正紀念堂發送傳單的那天,當時她自製的傳單上,用筆寫著她覺得該讓更多人知道與關心,關於收容所裡的情況、關於流浪動物會如何被處置的現況。
「領養,不棄養」,現在Raye手上已經有了《十二夜》這部電影在電影院播放,不再是一個人發著傳單了。

(攝影/但以理)
關於電影十二夜的更多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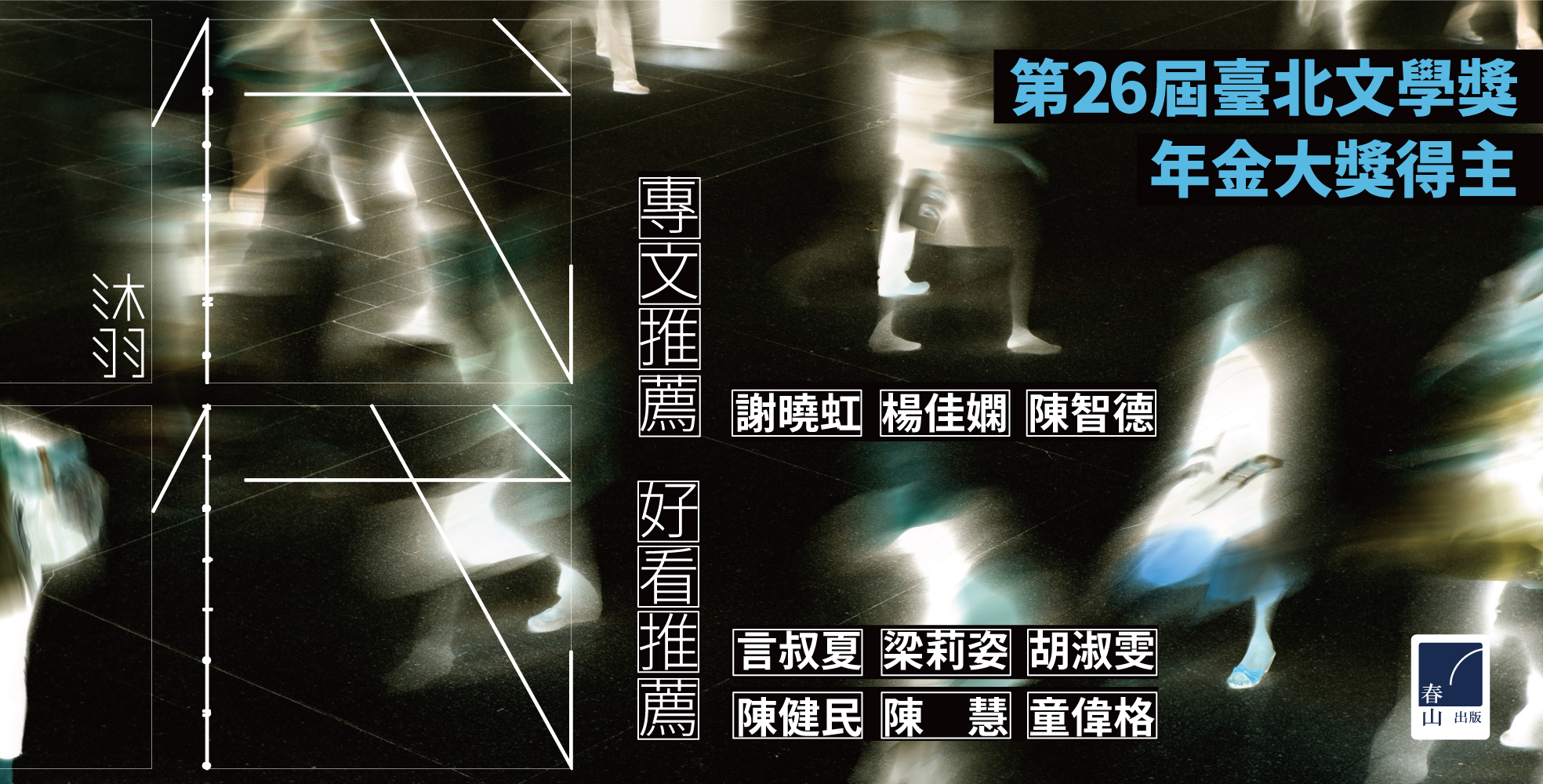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