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常,我們如何接觸、理解、介紹一位留名千古的歷史人物?
可能是透過文章、透過史料與故事,透過該人物遺下的種種作品,或後代為其留下的摹畫記錄、延伸重現。藉這些方式,我們對思想家荀子、墨子、莊子,文學家李白、白居易、蒲松齡,或是傳說中的齊天大聖,遂因此累積了不少既有認識。然在詩人羅智成的新舊集結作品《諸子之書》中,他以詩的語言,為這些在印象中已然僵化的人物,翻上了新的一篇詮釋。
「多麼不適當的時辰/我卻絕望地戀愛了/那是何等難堪與悲哀/我的兄長、我的父王/監國使者與知心同儕/讓處境更加艱難/卻是無助無告的妳/為我容身庇護所在」──〈洛神〉
《諸子之書》裡的詩作,分別來自1989年初次問世、現已絕版的《擲地無聲書》的「諸子篇」八首,以及1982年《傾斜之書》中〈問聃〉〈離騷〉兩首,與新作〈洛神〉〈李白〉〈蒲松齡〉數篇。雖然頗有歷史,但讀來新意依舊。「我很早就有撰寫諸子的想法,也一直希望把這些純粹詠史與表達、刻畫人物的作品收成一本。」算算30年餘,羅智成如今終於兜攏了四下散落的諸子們,也算是一個創作階段的完成。
回想以諸子為題寫詩的初始,是羅智成在美國求學的時期。「其實寫現代詩,想要把自己的想法西化、異質化的衝動是比較強的。」說來矛盾,人在既有環境底下,忙的是將自己用他種文化方式展現;到了西方,原來習慣的環境不見了,對新環境又尚未產生投入感,便四下尋覓身邊有哪些與自己最接近的事物。「那時我在美國的圖書館閱讀大量中國古書典籍,碰觸在生活上、情感上與自己靠近的東西,也得到在中國思想文化與歷史人物上相當豐富的素材。」於是他便想,或許可以用詩,來描寫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人們。
「寄託的成分當然是有。但我想,古今中外不論中國或台灣,都有很多精彩人物,只是沒有人以比較有感觸的方式展現他們。」羅智成認為,數百年來,強盛西方文化的確覆蓋了東方文化的光芒,很多時候我們自我認同的對象,也都以西方為主,忘掉我們也有過許多耀眼的成就。「我想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來讓大家想起這件事。」
「我這兒/從頭到腳已被虛虛實實的恩怨、義理/蛀蝕一空/像具襤褸的走動的中國/每根筋脈/暴結著一串串人物與事件的果實/每束血管/緊扯住縛之愈裂呼之欲出的情節/每絡神經/雜亂彈奏著講者與聽者的心弦/像春蠶吐絲/我為他們結繭」──〈說書人柳敬亭〉
即使已然中年,羅智成依舊記得自己寫詩的起點。「寫詩這件事,不是你清楚了『詩是什麼』才發生的。」大部分的人都是一邊寫一邊摸索,慢慢知道什麼叫詩。小學二年級就開始寫日記的羅智成,將日記當作各類文體的練習場,也學著掌握文字的節奏與韻律。早期他對詩的喜好偏向有韻的古詩,寫著寫著,發覺現代詩的熱情奔放又充滿創意的文學特性更吸引他,後來幾乎都用現代詩的形式在寫日記。「說起來幾乎是史前的事情了。」他笑。

羅智成認為,詩可以是花園、是小鎮、是城市,看的角度多深,詩就有多大,在裡頭就會逛上多久。「我看到的詩是一個世界,它可以讓我在裡頭住一輩子。」是以,詩,也就成為他日常自然看待生活的觀點之一,而非刻意將自己打造成一名詩人。
「什麼時候/神祇和精靈們靜靜地撤走了呢?/什麼時候/雲不再低低地棲息/龍不再因翻身憇睡而發出摩擦的聲響?/什麼時候/巫祝的歌失去了溫情?」──〈離騷〉
不論以誰為題,羅智成總要先經過漫長的閱讀與爬梳整理,而非一時的情感觸動。「這就像是我用詩寫的論文,我希望它有論文的扎實,又希望它有詩最迷人的部分,兩者沒有偏廢。」不能因為是詩而過度感性浪漫,也不能因為帶有研究背景而變得冷硬呆板。「等於是用詩的方式來寫一份人物報告。」要準確地傳達出自己對這個人物的客觀認知,更把自己巨大的主觀與感情投射其中。
從諸子與詩的流傳重演,我們看見了文化與人物的相互辯證關係,「有精彩的文化就會有精彩的人物,自古即然。所以我們也都要更主動地讓自己變得精彩,推動出更精彩的文化。」這是詩人捧在心中,隱在文字之間的遠大期望。
〔羅智成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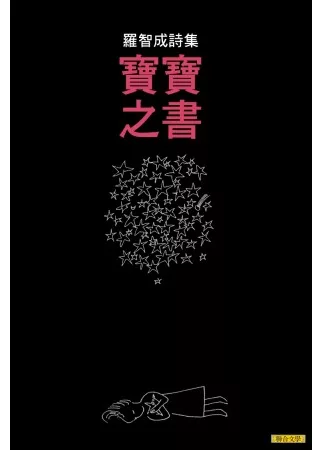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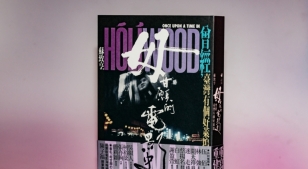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