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林阿讓)
「往後退,沒有路,倒不如只有往前走。」
––《拔一條河》
2009年八八風災重創南台灣,以芋頭聞名的甲仙小鎮,一夕之間風雲變色,一百多戶住家遭到土石流覆滅,491人失蹤。紀錄片導演楊力州蹲點一年多,《拔一條河》以甲仙重建為背景,敘述甲仙國小拔河隊如何為家鄉爭取榮譽,用一條繩子拉起被惡水沖垮的家園,也拉起散落的希望。孩子的力量其實比大人更強韌,孩子們失去學校,只能在組合屋上課;拔河隊沒有練習機,那就對著樹根、對著牆壁練習;沒有拔河鞋、沒有護具,每次用力拉扯總帶來皮破血流,但是沒關係,擦乾眼淚、再來一次。那些孩子教會大人的事,非常簡單,卻也非常深刻。
最開始是一個微電影的邀約。統一超商委託楊力州的「後場音像記錄工作室」拍攝便利超商店長的故事,帶來厚厚一大袋資料。「我在翻資料的時候翻到甲仙,」楊力州說,「同事聽到甲仙有點緊張,說工作室附近就有三家超商,可以就在附近挑一家拍。」等到楊力州去甲仙作田野調查的當天,這個計畫不只底定,還立即變型。原本應該交出的3-5分鐘的微電影,成為29分鐘的短片,「當時就動了念頭,看有沒有希望成為一部長片。」他不想做跟新聞報導一樣的東西,不去特寫悲情、不去凸顯呼天搶地,紀錄片要跟在後面,慢慢記下那些微妙的變化。
拍攝紀錄長片是個大工程,楊力州帶著團隊在甲仙住了一年多,「比較困擾的是,會拍到農曆年,所以我們的家人都到甲仙陪我們過年。」他說,大部分的時間其實都沒在拍片,只是在小鎮街上晃來晃去,「午餐吃飯時間經過誰家門口,他們就招手把我們叫進去。」大部分的時候,他們都在聽,安靜地聽小鎮居民說故事。其實拍下來的東西大部分沒有用,片中用了非常高比例、幾乎是武俠片規格的鏡頭量,因此影片節奏很快,剪進去片中的,大約只是拍攝量的十分之一而已,「聽起來很多,並沒有那麼厲害。只是待的時間夠久,跟他們夠熟。」楊力州補充。
拔河隊之外,片中也拍攝當地的新住民媽媽們。楊力州不諱言,這個選擇讓電影公司壓力非常大,擔心會影響票房。「拔河隊裡三分之一成員的媽媽是新住民媽媽,所以很早就決定要把媽媽們拍進去。」他說,「她們一直在,只是政府都假裝沒有看到,管理單位是行政院下面的內政部,內政部下面的移民署,移民署下面的外籍配偶科,在政府裡的等級低到荒謬的地步。政府怎麼會漠視一大群人,漠視到這種地步。」這些新住民媽媽們扛起家庭,為甲仙重建投入莫大的心力,他認為,「小朋友的故事應該被看見,媽媽的故事更應該被看見。」
「在這小鎮裡,每個人都不是英雄,但每個人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我想講一個小鎮的故事。有點像是日本電影《幸福的三丁目》,因為窮,因為什麼都沒有,人的質感都跑出來了。」正因為如此,《拔一條河》不是一部關於淚水的影片,即使哭泣也不是因為悲傷,而是不甘願,從淚水中會盛放更堅實的毅力。

(攝影/林阿讓)
楊力州明白紀錄片就是涉入別人的生活,他甚至翻轉鏡頭,刻意讓觀眾看到這點。拍攝的同時團隊也參與其中,他們是小鎮生活的一部分,他們不可避免地涉入了別人的生活,他們試圖去改變。有人提起媽媽們都沒有拍過全家福,工作人員於是出動幫忙,後來又說到,媽媽們都沒有拍過婚紗照,婚紗的工程比較繁雜,整個社區都動員起來,東拼西湊借來婚紗、找人幫忙梳化,他們的團隊就負責拍照。
甲仙是個移民色彩濃厚的小鎮,原住民、平埔族、閩南人、客家人、新住民,還有很多榮民伯伯在山上種樹。楊力州覺得甲仙就是台灣這個移民社會的縮影,「這幾年不公不義的事情太多了,打開電視、翻開報紙,幾乎沒有一件好事,就像當時的甲仙小鎮,沒有一個好消息。如果這小鎮站得起來,台灣也會有機會。」楊力州說,「如果一條繩子可以把這個小鎮拉起來,那麼一部紀錄片應該也有希望把台灣翻轉過來。」
【紀錄片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楊力州:這問題我確實被問過了很多次,但我好像一直沒有好好地回答過。
我一開始學紀錄片,我就覺得紀錄片可以改變世界,我幾乎這麼相信。儘管所有的外在環境、我的過往作品好像也沒有改變世界太多。但我一直這樣相信,才有辦法繼續去拍每部紀錄片,我依舊相信紀錄片可以讓這世界改變、往美好的方向去。
我很喜歡一部義大利電影《美麗人生》,在講二次大戰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時候,有個爸爸帶著兒子在集中營。他一直不想讓兒子知道這是戰爭,他告訴孩子是在玩一個遊戲、做一趟旅行,甚至寧願自己扮一個丑角把兒子逗笑,不希望讓兒子在災難、恐怖或憤怒的氛圍中長大。就連最後他快被殺掉了,他要兒子躲在木箱裡,告訴兒子要玩捉迷藏。兒子透過小小的縫看到父親離開,踢著滑稽的正步、臨走前還對兒子眨個眼睛,可是一個轉彎爸爸就被打死了。
我覺得紀錄片就是這個父親,我願意去擔任這樣的角色,一直把很多美好的東西拍攝記錄下來,告訴我們的孩子、告訴這個社會,這世界是很多很壞的事,但其實沒那麼糟。所以我很喜歡做這件事。

(攝影/林阿讓)
【《拔一條河》電影預告】
【關於電影《拔一條河》的更多資訊】
【更多楊力州導演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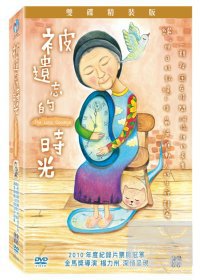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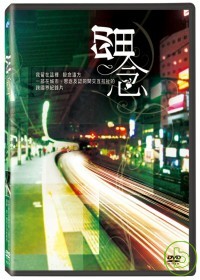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