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成為西蒙波娃》,思考關於「成為」。成為,是一個過程,就像捏塑陶土成某個樣子。波娃說:「人唯有透過自由的抉擇與事態的交互影響,才能發現真實的自我。」但是這個「自我」,是先有那麼一個所謂的「自我」,然後慢慢成為自我?或是在整個過程中漸漸成形,成形的過程都是自我?
這是很形而上的思考。但我回看自己,我確實隨著一次一次的選擇,看見事態的變化與自己,就又更了解自我多一些;而「我」的樣子,也因著這些選擇,有了自己才知道的變化。我感覺到做出選擇與行動的自己,是基於自由。
可是,我一直都是自由的嗎?
自由,存在不自由中。得先感覺到不自由,才會生出對自由的渴望。
第一次感覺到不自由,是小學三年級。某天午睡我趴在桌上,看著窗外的天空,想著自己什麼時候才會十八歲。為什麼是十八歲?大概是認為十八歲就有決定任何事情的權利;當時的我還不知道,自由除了擁有選擇的權利外,還要有能夠選擇的能力。
自由,並沒有因為我長到十八歲,就順其自然的來了。十八歲的我陷入一個更為明確的困境。如果說,九歲的我感覺到不自由是因為體制,十八歲的不自由仍舊是因為體制,但以前從未思考過脫離的可能。九歲的我認為上學是理所當然,十八歲的我不再認為理所當然,卻沒有為自己選擇另一條路的能力。
我感到不自由,卻沒有選擇自由的能力。離開學校要做什麼?我不知道我要做什麼,我沒有想做的事,沒有方向,沒有工作能力,沒有經濟能力,唯一能做的只有對現況說「不」。那是第一次發現,想擁有自由,要有「能力」。這不是說要有能力才能夠享有自由的權利,而是,就算享有自由的權利,但無能力者無法為自己選擇自由;就像門開了,卻不會飛。
慶幸的是,當時的我雖然沒有能力,但我有後盾,有名為家庭的支持系統,有所謂好的現實條件,讓我有機會對「不自由」說不,而不是不得不。我想說不,也有條件說不。可是有些人,他們不得不。
看電影《富都青年》,看到阿邦跟阿迪,看到馬來西亞無身分移工的困境,他們的生活是被推著走,幾乎沒有選擇。我想起沙特說的「現實性」與「超越性」。
「現實性」指的是人生中所有無法自行選擇的偶然條件,包括誕生的時代、地點、膚色、性別、家庭、教育條件及人所得到的身體。「超越性」指的是人能自由超越這些條件而決定自己的價值觀,而後「選擇如何理解」現實,以及如何以行為塑造自我。沙特認為:無論處境如何,人可以自由選擇回應自身處境的方式,從而超越現實性。
波娃對此看法提出質疑:「一個被關在深閨中的伊斯蘭小妾要用什麼方式超越現實?」波娃認為理論上能夠自由為自己選擇價值觀是一回事,但在現實中擁有選擇的能力是另一回事。
我認同波娃的說法──人若處於一種沒有機會接觸到現實以外世界的處境,要如何看見現實以外的可能?但換個角度來看,世界再封閉,總是有隙縫,總是有現實條件以外的「什麼」透進來;透進來的不一定能改變現實,卻可能帶來「選擇如何理解」的自由。
雖然我這麼想,但還是覺得所謂的「選擇」,不論是現實性或超越性,對活在底層的人來說都格外的少與難。而朋友說,底層的無能為力,中產階級也會有。「可中產階級的選項,或得以超越現實的可能性,總是比底層世界要來得多吧?」我說。
但當我說完,我想起電影《大象席地而坐》,那當中的老人、青年、少年與少女,他們不自由的痛苦,或許不比無身分者來得小──
「我覺得呢,我的生活就是一堆破爛,每天堆在我面前。我清一棍,就有新的堆過來。」胡波筆名胡遷,著有小說《大裂》,同名小說〈大象席地而坐〉是其中一篇,與電影改編差異極大,但同樣透出虛無。電影中從未出現過的大象,在小說裡出現了。「我」去看那頭大象──
「這人活著啊,是不會好的。會一直痛苦,一直痛苦。從出生的時候開始,就一直痛苦。以為換了個地方會好,好個屁啊。會在新的地方痛苦。沒有人明白,它是怎麼存在的。」
「你不舒服。我覺得這就對了,我沒覺得人什麼時候舒服過。」
「你能去很多地方,可以去,可到了就發現,沒什麼不一樣。」
「因為我得看看牠為什麼要一直坐在那,這件事可能是我這輩子最大的一個問題了。」為什麼一直坐在那?為什麼我一直在這裡?為什麼一直痛苦?這可能是胡波創作的源頭。他在《大裂》後記寫道,「將寫作看做直面生活最有力的方式。於是從其中得到某種力量,以對抗世界的灰暗。」我想,創作是胡波超越現實的方式,可最終,他還是讓自己的肉身先離開了現實。
我忍不住想,當一個人還未感到不自由之前,是自由的嗎?在還未思考自己是誰之前,是自由的嗎?而思考之後,就真的是自由的開始嗎?
作者簡介
大學讀了七年,分別是工業產品設計系與新聞系。認為生命所有經歷都影響創作。著有詩集《沒用的東西》;非虛構長篇《滌這個不正常的人》,曾獲第二十屆台北文學獎年金,2020年臺灣文學金典獎。
瞇是細細地看,慢慢地想。現以文字為生。
【OKAPI專訪】「真實的去認識一個人吧,然後,再多知道一些。」──專訪廖瞇《滌這個不正常的人》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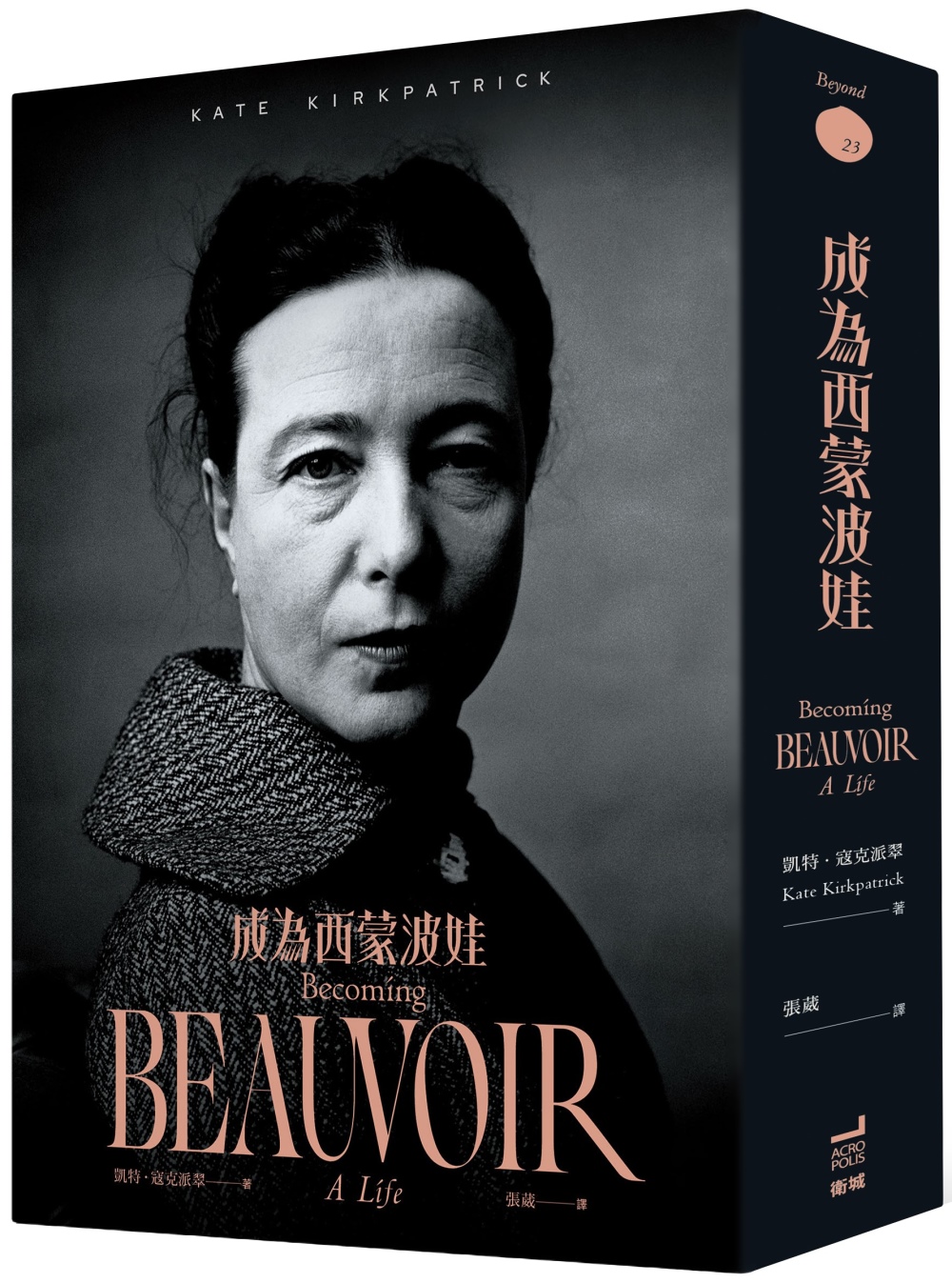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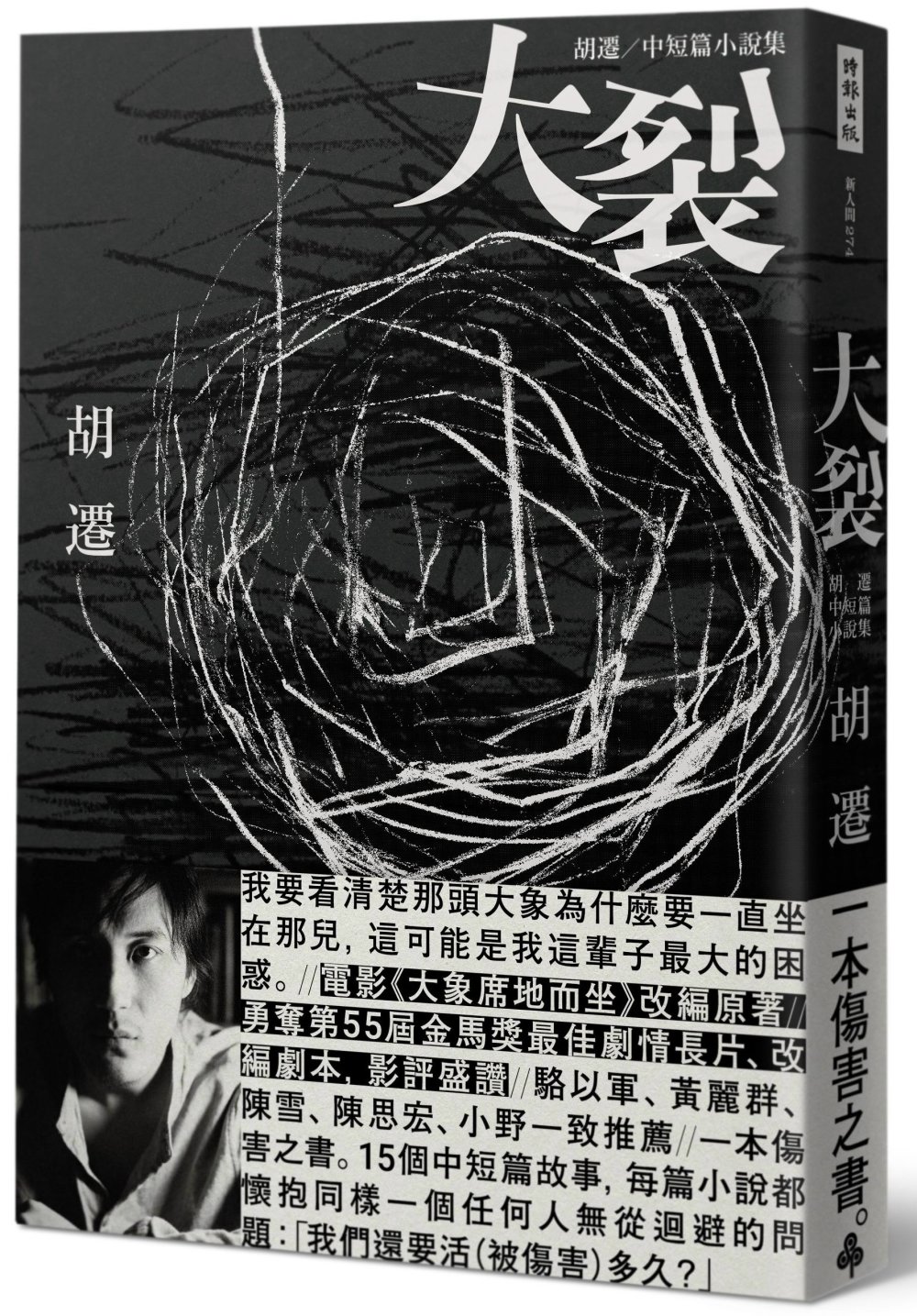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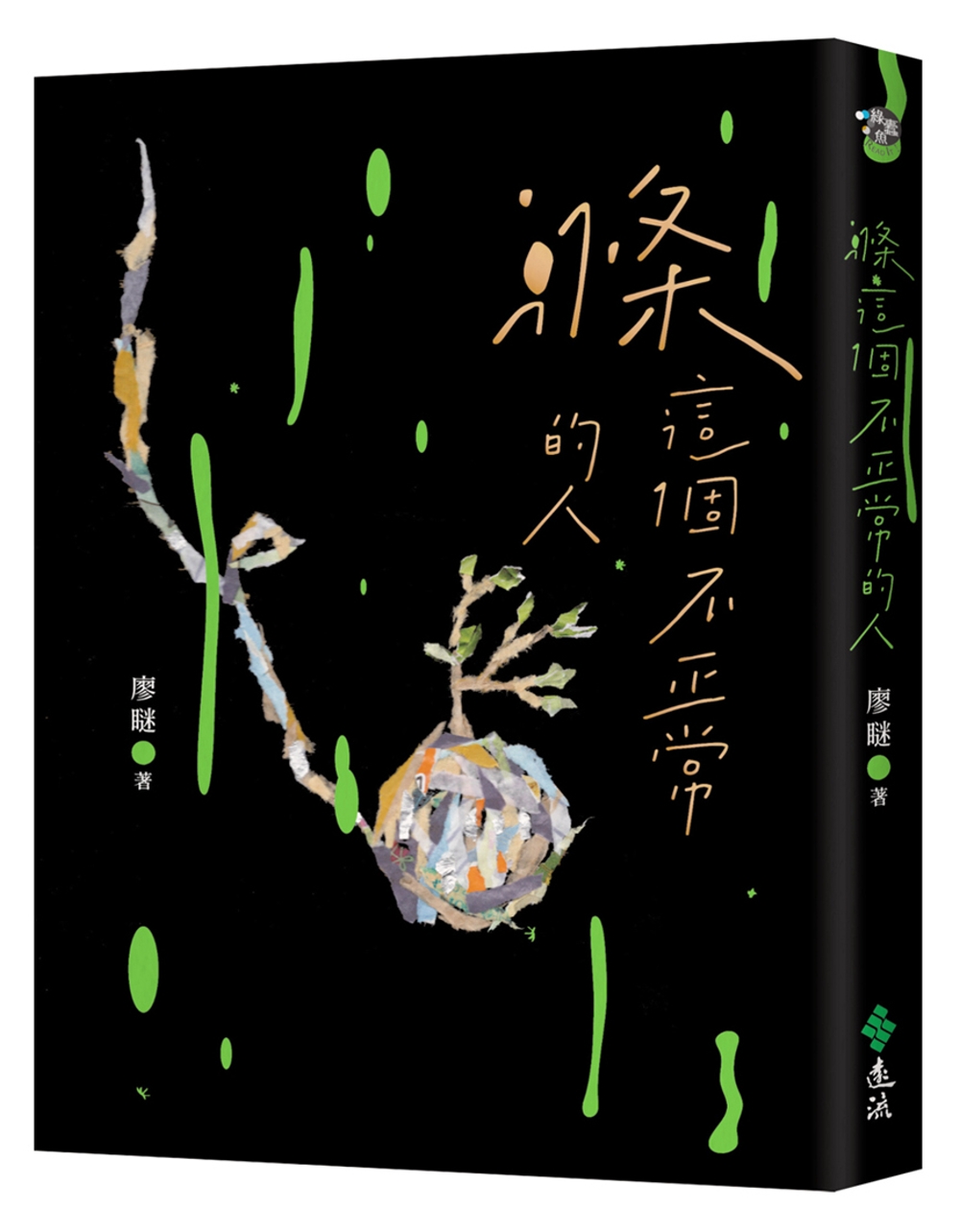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