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西哥詩人蘿希歐.賽隆 (Rocío Cerón, 1972- )。
在幽暗的地方燒出火花────
當代的美洲文學,怎麼發聲?
怎麼更新人類的表達?
吐出一個詞。再吐出相似的一個,覆蓋上去。她衝快速度,疊起一串詞一串句子,不在乎意義拖在後面磨破了皮。不久,一座詞語的叢林就在她的嘴巴裡冒了出來:人的沙質內部,太陽漩渦,放在適婚膝蓋上的手,不明的天體,牡蠣,時間,幾乎攪動波羅的海的呼吸……
她變換聲調,鼓動一陣風,吹響叢林,令每一個詞語的身體相互撞擊,發出從沒聽過的交響。她的手摀住她的嘴,呻吟嚎叫,語言化之前的聲音有時擠壓樹根,有時吹送氣流撫摸樹冠。層層疊疊,她一手創造的叢林就要將她滅頂。
她瓦解聲音嗎?沒有,她指揮多種聲音同步鳴響。她陷入混亂嗎?沒有,她在結構混亂,用看起來混亂的方式。她激烈變形嗎?沒有,她在恢復感官與意識的連通本能。
重點在於,摧毀。
就像蘇格蘭物理學家在光的偏振和折射實驗中偶然發明的萬花筒:圖案和顏色散開,搖一搖,碎片重新排列,露出新的幾何圖像;再搖一搖,摧毀那裡的東西,掀起新的波動,看那世界多重反射、不斷自我重塑。沒有摧毀,就沒有新的形態。
沒有新的形態,詩就死了。
墨西哥詩人 Rocío Cerón 結合文字、圖像、音樂、舞蹈、錄像的跨界詩歌實驗,一再改變舊的系統,生成新的秩序,重點在於,創造詩的行動能力,就像萬花筒「kaleidoscope」一字源於古希臘語,意思是:觀察美麗的形式。

Rocío Cerón詩集《漩渦nudo vortex》和內頁的拼貼作品。
對詩人來說,美麗是什麼呢?從她2015年的詩集《漩渦nudo vortex》中的幾幅拼貼照片來看,她先摧毀影像的脈絡,挖出那正在交媾的人形,把它們置放到一張素淨的背景上,再把花種在它們的肉身。構圖並不複雜,形體之間的邊界也不刻意抹消,透過凸顯它們的粗糙對接來摧毀它們的封閉情境。Rocío Cerón製造的漩渦不是肢解物象,不是用屍塊來組裝一座新的無名身體,而是保留各物象的完整形貌,僅僅重新佈置它們的關係。
美麗的是,新的關係形態。
於是,她詩中的單詞與空白也以同等的獨立完整,被保留下來。她的句子極短,碎裂。線條和符號圍繞詞句,而括弧像是動態的喘息,肺葉還在擴展。異質的詞語、空白與符號拼貼出一種新的語言結構,不是為了通順地構築出連貫的意義,而是勒令我們停下來,因語焉不詳而受阻,停在詞語的斷裂處而不是它們連結相生的意義網絡。意味不明之際,聲音本身的韻律和節奏成為文本的骨幹。以 Rocío Cerón 在2012年出版的詩集《立體模型Diorama》中的詩作〈幽暗鳥奏鳴曲曼陀羅〉的開頭段落為例:
泥土和種族的氣味。掀開蓋子,看看還有什麼。
不需要更多了。聲音就是詩的全部。Rocío Cerón 帶我們回到這是什麼而不是它意味了什麼的狀態。暈了,再多一點意志去抗拒清醒的誘惑,反覆聆聽Rocío Cerón 朗讀這一首詩,她的呢喃、吟唱、呼吸都在進行直接的身體性表現。詩作成為樂譜,詞語成為開放的指令,她擴展了詩的第二生命,生產存在而不是生產意義,讓我們從語意解讀的習慣中解放出來,通向意識的祕密空間,一座原始洞穴。
一邊聆聽聲音詩,一邊閱讀文字版本的〈幽暗鳥奏鳴曲曼陀羅〉,聲音的堆疊推進,讓那斷裂飛躍的意象不斷激烈碰撞,撞出鮮明而奇異的感官體驗。我們無窮原始地得到一種迷人的敏感,遠遠超越任何可以理解的流俗。就像電影導演羅伯.布列松說的:「舊的事物,若你把它抽離習慣圍繞它的一切,舊的也會變新。」詩中的詞語、括弧、空白、標點符號、變換的字體、意象的質地、斷句的位置,它們也在誘發一場智力的舞蹈:
這首詩的第一個字 Cortical 指大腦皮質,它是層層疊疊包覆在大腦表層的神經細胞,掌管我們的語言、思考和記憶。詩的起點是大腦皮質,然後向下,鑽入腦內的運作,Rocío Cerón 以「形式和陳述」概括大腦接收、整合與反應訊息的能力,她在意的顯然不是皮質功能而是它們作用的形態:力的脈動。然而,「脈動」和「振動」這樣的詞語還不足以表達「力」的樣貌,她緊接著用了符號 (((( )))) 來視覺化震盪和擴充的波形。她不要我們用大腦皮質專擅的抽象概念來理解大腦,她要我們跟隨大腦的生命脈動形態,去感覺存在。
從大腦的外層進入,進到語言的內層,再深入語言的盡頭。然後,「味道」出現了,可見可觸的一張古老「地毯」現身,那是非法奪取的「紀念品」,佈滿了「果子狸麝香,野生,霧氣」。Rocío Cerón 要我們運用身體感官去追蹤和辨識地毯的來源,進入那守護內部、隔絕外部的「真皮」層,去懂得一張被掠奪的有形地毯的無形「死亡」。即使地毯的身上還有「茶香和星點」,它已失去了它的實在與完整,「就像是一個碎片」。在這樣的狀況下,再打開大腦的「蓋子,看看還有什麼」,瞭解了一張地毯的身世、瞭解了人世的殘酷,大腦仍在脈動,「一點一點呼吸」,但是,知情了就無法全身而退:「在這個時刻,在這種氣味中,任何人都會迷失方向。」

詩集《立體模型Diorama》和她運用詞語、符號和空白組成的詩作結構。
一次又一次墜落,就是 Rocío Cerón 為我們和這個世界建立的關係形態。破碎的形式,撐起了磅礡的歷史批判。〈幽暗鳥奏鳴曲曼陀羅〉開頭的這幾個段落,乍看詞語和意象跳躍,但細讀詞語之間的關聯,就能追隨一場具有方向性的動態行進,從解剖大腦開始,解剖語言、解剖文明大陸的暴行、解剖暴行無法摧毀的氣味、重新進入大腦,叩問那還在顫動的良知。
以形式的摧毀,來挽留那些不可摧毀的物事。Rocío Cerón 常以一段真實的經歷來描述她和詩之間的關係:「13歲時,我幾乎失去了生命。我的左腿植入一根神經,從腳後跟到小腿──這是一個神奇的阿基里斯之踵,它給了我脆弱性作為我強壯的力量。我還住進醫院,做眼睛的顯微手術──在那裡我明白了傷口就是眼睛,傷口就是我通往詩歌的道路。」
Rocío Cerón 在2016年接受英國文學雜誌《Wasafiri》專訪時曾說:「我喜歡墨西哥城,因為我聽到了混亂,我聽到了它的人民,這是我詩歌的主要材料。傾聽,積極傾聽,就是了解世界的混亂。詩以最親密的方式看到世界的懸浮顆粒;最深刻的,也是見證人類日常生活的一種方式。每首詩都是一個微小的回應或一個偉大的答案,同時它也提出問題。」
收錄在詩集《漩渦》中的〈冷杉花園紀念館集體石碑〉,Rocío Cerón 提出的問題是:「到這一刻為止,你為自己的生活畫了多少幅畫?」這個句子後面,她寫了數字312678000──
圖像在響亮的聲音中停下來,被感嘆聲打斷,在這一點上揭示了一些東西:爆炸的真實情節所在的陳述:手指已經在煙灰中敲擊著。
這裡誰是革命者?冷漠是想像力的匱乏。
猩猩身上的直線。波浪線。舉起你的手,你的手指,你的文章,讓自由不再是一個被操縱的詞,而是在經過的房間的牆壁之間轉移。
世界不僅僅是政治,同時也像這首詩一樣。
她透過這一首詩,鼓吹一種革命的形態:在所有事物的皮膚上「畫出你想到的空間,最自由的空間。更具爆發力。更性感。更加真誠。」用洞察的目光去畫,用心思去畫,那展開的線、下降的線,也是一種呼吸的韻律。因為,我們和事物已在我們的探索中創造出我們的全新關係。
關係不會消亡,而是發生變化。Rocío Cerón 的祖父是一個科學家,祖母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對她來說,打破學科界限的詩歌實驗,是自然而然的家族傳統。她總是先寫了文字的詩,再將它轉換成音樂,然後結合影像和身體展演。她稱這樣的橫向詩歌為她的「銀河計劃」。她說:「墨西哥詩人都是傳統和習俗的孩子。我們這一代人不再生活在奧克塔維奧.帕斯(Octavio Paz)的重壓之下。我們的聲音和看待世界的方式非常多樣。」

Rocío Cerón結合音樂和影像的現場詩歌表演。
Rocío Cerón 打破「文字」的傳統去回應「詩」質疑語言的傳統,我想以一首被她名為〈碎片〉的散文詩來描繪她擴展中的詩歌雕塑:「從一張嘴到另一張嘴,一個房間,一個城市,一個大陸,一個恆星空間:渴望未來的呼吸,堅持未來。寫其他東西。疊加。在空氣中寫作,聽覺上顛覆——沉默──共同的脈搏變成了一個世界。」
Rocío Cerón 的詩創造了共時的多維性,她對感知與記憶的來回爬梳,從過去到現在,從未來到過去,從中心到外圍,從外圍到中心,引發形式與內容相契的脈動,搭建一座立體的螺旋迴圈。就像《Wasafiri》的記者問她:妳對未來有什麼計劃?她回答:「一個新的開始,一個疑問,一個開始,一個疑問……,約翰.凱吉說得很好:『從任何地方開始。』」
作者簡介
曾獲選東華大學「楊牧文學研究中心」青年駐校作家、原住民文創聚落駐村藝術家、紐約 Jane St. Art Center 駐村藝術家、挪威 Leveld Kunstnartun 駐村藝術家、美國聖塔菲藝術學院駐村作家。2022年夏天從花蓮的阿美族部落移居美國,就讀美國印地安藝術學院創意寫作研究所,持續追探情感的深淵、日常與神話的糾纏。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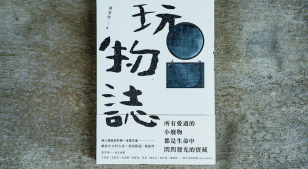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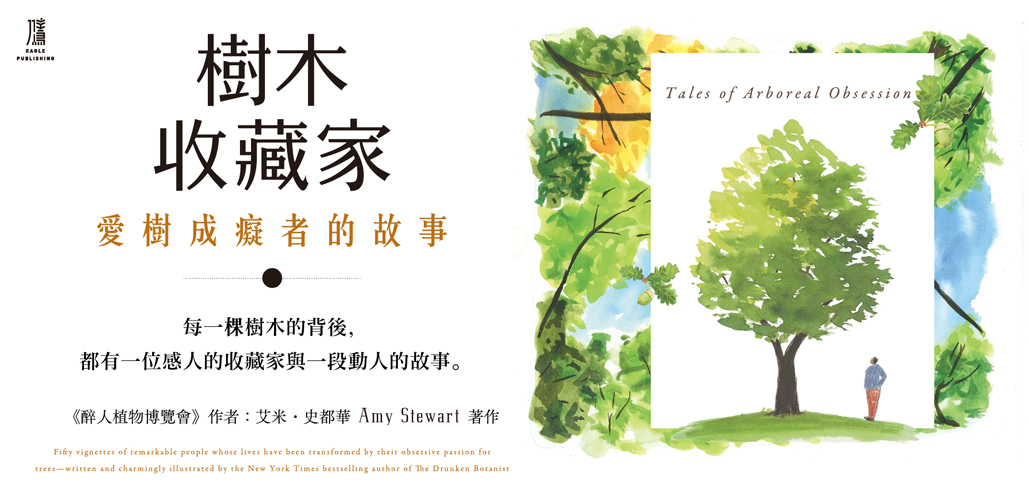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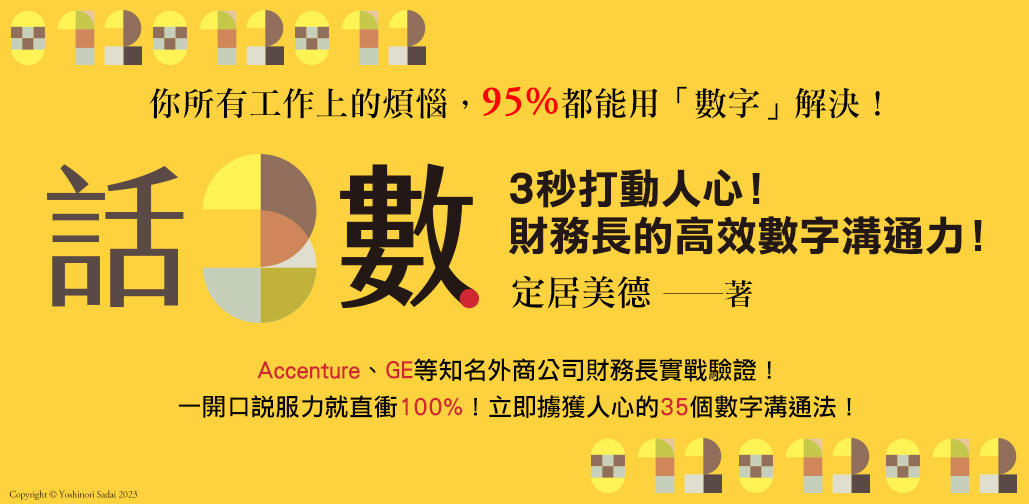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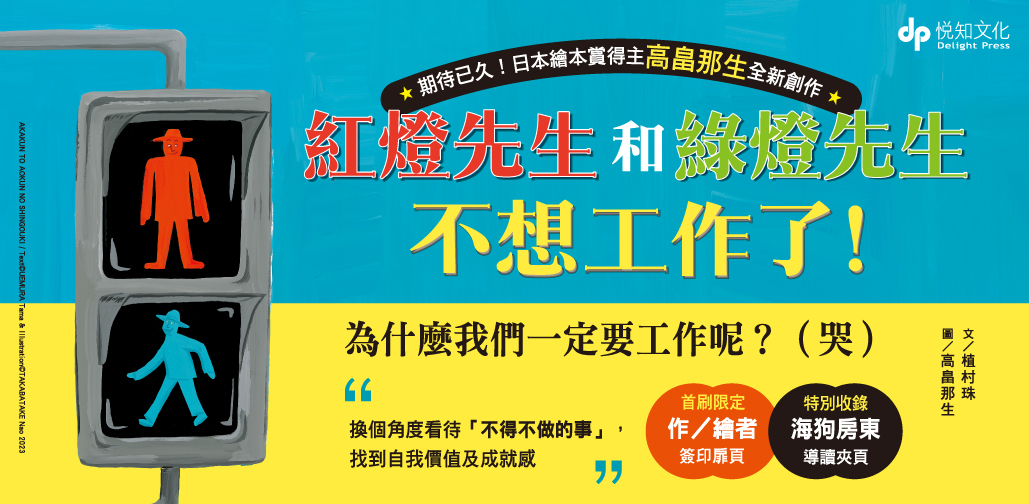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