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公認,一八八〇年代末期至一八九〇年代初期,是契訶夫(А.П. Чехов, 1860-1904)醫生做為一名短篇小說與戲劇的作家大展天才,且在文壇上鴻圖大展的時刻;他不僅出版了新的小說集,還獲得了科學院頒發的普希金獎,而他的兩齣戲劇《熊》(Медведь, 一八八八)與《求婚》(Предложение, 一八八八—一八九○)也在當時的專業與業餘舞台輪流上演著。正值外界看來大放異彩的時期,本該三十而立的契訶夫在精神上卻對自我的寫作與存在意義產生了強烈懷疑,而有了信心危機。
不少學者試圖解釋並找尋,契訶夫為何在文學事業發展如日中天時前往俄羅斯罪犯流放的遠東地區,並寫下《薩哈林島[1]行旅》(Остров Сахалин,一八九一—一八九三)的創作動機。就目前已挖掘的資料顯示,契訶夫本人並未解釋這次遠行的目的與原因,故當他在一八九〇年一月發佈是年四月將啟程前往薩哈林島的消息時,引發了莫斯科文藝界一片譁然。眾所皆知,薩哈林島乃係重犯、流犯、政治犯與苦刑犯聚集之地,且當時西伯利亞大鐵路尚未完全通行,沿途多靠馬車、人力與舟行,交通不便自不在話下,氣候苦寒對於體弱多病的契訶夫而言更是一種身心折磨。
其實,在發佈旅行消息前不久,約莫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在莫斯科的契訶夫寫信給當時擔任報紙《新時代》(Новое время)的主編蘇沃林(А.С. Суворин,一八三四—一九一二),傾吐自己的心境與心情:
隨筆、雜文、蠢話、輕鬆喜劇、枯燥乏味的故事我寫過不少,有過許多錯誤和荒誕不經的東西,用完了好幾個普特[2]的紙張,得過科學院獎金,過著波將金[3]式的生活,─然而卻沒有一行在我心目中是有嚴肅的文學意義的東西。我從事過大量的緊張工作,但沒有認真地勞動過一分鐘。……我的多疑,以及對別人勞動成果的羨慕心,把合乎真情的憐憫心誇飾成像巨象那般大。我非常想藏到一個什麼地方,藏個四、五年,從事仔細而又認真的勞動。我應當學習,一切都從頭學起,因為我,作為一個文學家來說,是個完全的外行,我應該認真負責地寫作,有感情、有理智地寫,不是每個月寫個五印張,而是五個月寫一印張。[4]
由此書信可知,獲得科學院普希金獎後的作家契訶夫,非但沒有因此驕衿自喜,反而更加感受到「作家」一職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的俄羅斯社會被賦予了社會責任與道德使命的沉重壓力。他反省自己過往寫作的態度太隨性、隨意,不夠嚴肅看待作家身分,也認為自己長期處在中產階級「醫生」一職的象牙塔裡,生活無虞,根本無法看清身為作家的自我存在意義與道德責任,也難以瞭解在俄羅斯這塊大地上民眾為何無法活得好,遑論去深沉思考:人民生活疾苦究竟是誰之罪,社會問題的根源在何方,又該何解等等一系列由十九世紀俄羅斯作家創作中所提之大哉問。職是,他必須走出自己的舒適圈,走向遠方,走入人群,深刻體驗民間文化,並瞭解社會所需。這也是為什麼契訶夫在另外一封寫給蘇沃林的信,如此寫道:
唉,朋友們,多麼苦悶呀!如果我是個醫生,我就需要有病人和醫院;如果我是個文學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間,……需要一點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即使是一點點都好,而現在關在這種四堵牆內的,脫離大自然、人群和祖國的,沒有健康和食慾的生活,這不是生活。[5]
也有不少研究者將契訶夫東遊至薩哈林島的選擇視為一種朝聖,又或者是精神救贖的苦行之旅,認為經由「西伯利亞人間煉獄」苦難磨練的洗禮,最終將在精神上得到淨化。弔詭的是,西伯利亞在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書寫中因容納種種罪惡與罪人,而被形塑為「救贖聖地」。這些研究多半將《薩哈林島行旅》與杜斯妥也夫斯基(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一八二一—一八八一)的《死屋手記》(Записки из Мёртвого дома,一八六○—一八六二)或《罪與罰》(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一八六六)相互連結,說明契訶夫的創作動機是如何繼承這些文藝遺產,並從其書寫中勾勒出俄羅斯知識分子對西伯利亞所懷之流放情結、遠東想像與世界情懷。
亦有些研究認為,「旅行」在俄國文學發展的主軸中,向來就是不可忽略的主題。因此,《薩哈林島行旅》上承了阿凡那西(Н. Афанасий,不詳)的《三海紀行》(Хожение за три моря,一四七五),至拉吉舍夫(А.Н. Радищев,一七四九—一八○二)的《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Путешествие из Петербурга в Москву,一七九○),到十九世紀果戈理(Н.В. Гоголь,,一八○九—一八五二)的《死靈魂》(Мёртвые души,一八四二)與涅克拉索夫(А.Н. Некрасов,一八二一—一八七七)的《誰在俄羅斯大地上活得好》(Кому на Руси жить хорошо,一八六六—一八七四)等等文藝傳統,其創作皆意在藉由「行萬里路」來認識俄羅斯,並揭露社會現實,從而思考體制的問題。[6]此研究一一羅列並點名,以為正是這些傳統創作,為《薩哈林島行旅》一書鋪墊了相當厚實的文藝基礎。
然而,上述這些研究大抵忽略了契訶夫與拉吉舍夫、果戈理、杜斯妥也夫斯基或涅克拉索夫等傳統作家之間,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在成為作家之前,已經成為一位訓練有素的醫生,而強調科學知識與臨床經驗的醫科和博覽人文萬卷書的文科知識分子,在邏輯、思考、方法論等認知上,截然不同。因此,如果用當代流行話語來解釋,契訶夫不僅是個「理工男」、「醫科男」,在沒出遠門前,絕大多數的時刻還很可能是位只在住家周邊行醫的「宅男」。這和因為政治理念而被流放的「文藝男」、「革命男」拉吉舍夫或杜斯妥也夫斯基,抑或從小就是貴族的涅克拉索夫或地主出身的果戈理,在智識的養成與專業的訓練上全然不同。此一顯著差異,也凸顯在《薩哈林島行旅》的體裁書寫中。
在此,讀者必須注意的是,十九世紀前半葉之前從事文學的文藝男多半來自貴族階層,比起來多數自中產階級家庭的醫科男更受社會矚目,而人文學科專業,特別是法律與文學,相較於醫學與科學,更屬於社會顯學。只是,隨著科學與工業革命的腳步快速推進,貴族階層逐漸沒落,帝國體制受到時代挑戰,理科與醫科的地位也因此躍身。醫學的專業對於《薩哈林島行旅》的重要性,亦可從契訶夫後來給蘇沃林的幾封信裡得知。就在此趟旅行出發前與回程後不久,契訶夫提筆向後者闡述自己選擇薩哈林島的主要原因,其一是因自己透過書寫此一旅程可以「償還他對醫學的債務」[7],再者,他深信,「這本書對百年後的人們會是一本瞭解監獄制度的文獻與指南」[8],頗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普渡眾生的壯闊胸懷。同時,藉由醫生與作家兩種身份,詳實記錄薩哈林島上的刑罰系統、監獄生活、公共衛生狀況與醫療設施,契訶夫希望以此書替代論文的撰寫來鞏固他在莫斯科醫校的教職。[9]儘管有些醫學專業與職業發展的考量,契訶夫仍舊無法放棄作家的身分,因為作家一職在十九世紀後半葉仍然舉足輕重,並普遍受到俄羅斯社會各階層敬重。這也是為什麼身為醫生的契訶夫在文壇崛起後,面對俄羅斯作家的天職身分與社會責任感時,深感自身經驗不足,且對俄羅斯大地的瞭解不夠,不得不生的一種心理轉折,而萌生不得不走的一股創作動機。
行文至此,若讀者以為,「文藝男」契訶夫對待此趟旅程的態度與創作動機十足地嚴肅,那麼恐怕只對了一部分。有學者指出,契訶夫此趟薩哈林島之旅的決定可說是怪異至極,因為作家也常常以一種漫不經心或開玩笑的態度來向他人解釋此趟旅行的目的。他最初的理由說是為了抹去他過去一部份的生命經歷,接著又說要創造一段值得的半年回憶,也有為了改變生活節奏的說法,然後又說是為了逃避一段糾纏的感情,有時他也改口說這是一項科學計畫,有時又說是因為自己罹患了「薩哈林狂熱」症候群。[10]由此可知,這趟旅程與此書創作的背後具備了諸多內在動機,並融合了許多外在原因,猶如文科與醫科、幽默與諷刺、感性與理性、悲傷與歡笑等等多重矛盾的特質並存一樣,二律背反地齊聚契訶夫一身與其作,無法以單一角度或面向視之。綜上所述,多種內、外因素相互結合之下,此書由是誕生。可以說,契訶夫的自我擁有複雜的多面性,而此作的體裁則具備了豐富的多樣性。
有趣的是,如果對照俄、中與英美各國探究《薩哈林島行旅》一書所開展的研究問題意識、取徑與主題時,則不難發現文化差異佔據相當顯著的位置;不僅是作者契訶夫主體本身,甚至連研究者自己都難免在學術研究中展露出自身文化培養下的「自我投射」(self-projection)現象。例如,俄蘇學者往往關注此書語言文字的藝術性,文本背後的歷史背景與文化意涵,以及犯罪與刑罰引發的社會問題討論。中國的俄羅斯文藝研究則多數注重在傳統文藝遺產的承繼,以及契訶夫的「遠東想像」(imagination of Far East),對於書中描寫中國人部分時所帶有的「偏見」(或更精確而言,是一種刻板印象)與殖民眼光,頗不以為然。當中亦有研究,不免重提「庫頁島」當年是如何被滿清「割讓」給沙俄的歷史,字裡行間義憤填膺,希望「以正視聽」,故探究《薩哈林島行旅》時投射了相當「自我」的民族情懷。相較於中、俄兩國,英美同領域的學者則大多傾向聚焦於契訶夫在該書中所創造出獨特的文藝體裁,強烈的人道主義關懷,以及其作家眼中的「俄羅斯形象」(image of Russia)。不同於當中、俄的學者更傾向於將此書視為文藝創作之際,英美研究者則反而認為,創作《薩哈林島行旅》的契訶夫其實更應該被視為是「民族誌學家」,因為此書的體裁風格相當接近民族誌研究的形式。
綜觀上述這些因各國文化差異所造成研究上視野的不同,筆者試圖爬梳並整理關於《薩哈林島行旅》在俄、中與英美各國研究的最大公約數,將之融會。因囿於行文空間,遂簡短分析如下:
首先,從文藝的角度出發,契訶夫做為一個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的作家,就無法不注意到他如何在作品中描繪大自然的風景與人文景觀。契訶夫從不諱言自己從孩提時代就鍾情於大自然,甚至到了迷戀的地步,自然遂成為他生命與存在意義的一部分。例如,他愛頓河草原,並視之為家,每一條小溪他都瞭若指掌,並把如此體驗與心境寫入中篇小說〈草原〉(Степ,一八八八)裡。[11] 此一風格亦延續至本書中,不少篇幅展露了他對自然細心的觀察與自我的心境。舉例而言,當他描繪「葉尼西河最雄偉美麗的景觀」時,認為它「是被當地土著奉為神祇的自然風景,逃亡的流放者最愛的樂園,同時也是西伯利亞未來詩人取之不盡的黃金題材。」是他「這輩子見過最莊嚴美麗的河流」,「像是強壯有力,虎虎生風的海克力斯,不知如何面對自己的年輕和力量。」於是,當他「站在河岸注視著寬廣的河面一路奔向北極海時」,心中想著,「生命以呻吟始而以超乎想像的激昂終結」。無怪乎他在給友人信中形容他在西伯利亞的旅程中,有一整個月看著日出而能感受生命的狂喜。[12]
再者,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契訶夫遠比二十世紀人文學家如傅柯(Michel Foucault,一九二六—一九八四),更早注意到文明對狂人、犯罪者、邊緣人所設置的馴化教育與監獄制度,而帝國體系的腐敗更增生許多隱匿的罪惡。契訶夫的關懷不僅出於醫者之心,更來自於他身而為人的惻隱之心。在此書中,有不少部分描述薩哈林島上罪犯生活、典獄官僚腐敗,冤屈和正義難以伸張,公共衛生問題嚴重,以及兩性關係引發的生理、家庭與社會問題。種種慘不忍睹的現實情景一一導引著讀者深思,流放、死形或鞭笞等各類刑罰,是否真能導引人類向善,為人民帶來更美好的未來?俄羅斯文化和文學,以及基督教社會或基督教文學,是否真心關懷或真能幫助這些罪犯?俄羅斯知識分子是否對這些社會問題過於冷漠,缺乏關心和討論,使得這些罪惡產生更多的罪惡,最終致使薩哈林島所發生的一切恍如人間煉獄?
最後,竊以為,《薩哈林島行旅》絕對有資格成為一部民族誌研究參考指南。如若對照俄羅斯在十九世紀後半葉與二十世紀初其他的民族誌專著,例如,早於《薩哈林島行旅》十五年,俄國海軍保羅•伊比斯(П.И. Ибис,一八五二—一八七七)所寫的臺灣調查筆記《福爾摩沙之旅》(Экскурсия на Формозу: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И. Ибиса,一八七五),又或者是晚於契訶夫十六年到西伯利亞遠東地區探勘的阿爾謝尼耶夫(В.К. Арсеньев,一八七二—一九三○),於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七年間寫下《在烏蘇里的莽林中》(По Уссурийскому краю: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горную область Сихотэ-Алинь,一九二一),在這些專著中,讀者將十分容易發現,經由旅行、調查與探勘後,以科學角度所記錄的文字、視角、形式和方法,共享了諸多相似性。每到一個新的地區,契訶夫和民族誌作者一樣,必定詳實地記錄人口、性別、職業、人種、天候、地理景觀、風俗、物產和人物等等,如百科全書般的描寫,生花妙筆,鉅細靡遺。因此,此書超越了契訶夫原本的企圖,不僅是本可以瞭解百年前俄羅斯監獄制度的參考指南,更可說是一本俄羅斯遠東部分的民族誌。
於是,懷抱著這些創作動機與體裁等文本背後所透露出的訊息與知識,勇敢又愛冒險的讀者想必已經迫不及待自請「入甕」,想跟隨「文藝男」與「醫科男」契訶夫一步一腳印,進入他的思緒,啟程走這一遭人間煉獄的歷險,時刻深思此書所帶來的種種問題意識與人文關懷。
[1]編按:薩哈林島在唐代稱「窟說(ㄩㄝˋ)」和「屈設」。「窟」可能音譯自愛奴語的「人」,也是愛奴人的自稱。「說」可能源自古愛奴語的「地」。「窟說」即「吾等人的陸地」。元代稱「骨嵬」,明代稱「苦夷」和「苦兀」。元代「骨嵬」和明代「苦兀」是指當時島上的原住民愛奴人。清代稱「庫葉」、「庫野」和「庫頁」。島的俄語名稱「薩哈林」來自於滿語,意為黑江嘴頂;「薩哈林」音譯自該島滿語名的第一個詞,該詞是「黑」的意思。在台灣另有一個譯法稱為「庫頁島」,日本人則習慣稱該島為「樺太島」。
本書統一採用「薩哈林島」譯法。
[2]Пуд,沙皇時期俄國的重量單位。一普特約等於一六‧三八千克。
[3]Г.А. Потёмкин(一七三九年—一七九一年)俄國凱薩琳大帝的寵臣之一,位高權重,以生活奢侈浪費著稱。
[4]中文翻譯參考契訶夫著、朱逸森譯:《契訶夫文學書簡》(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一四二—一四三。
[5]同前註,頁一九四—一九五。
[6]姜磊:〈《薩哈林旅行記》與契訶夫的遠東印象〉,《外國文學研究》二○二二年第二期,頁一六八—一六九。
[7] 一八九○年三月九日給蘇沃林的信。轉引自L. A. Polakiewicz, “Western Critical Response to Chekhov’s The Island of Sakhalin,” Russian History/Histoire Russe, Vol. 33, No. 1 (Spring 2006), p. 73.
[8] 一八九一年八月三十日給蘇沃林的信。見А.П. Чехо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и писем в тридцати томах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4-83), Письма 4, С 266.
[9] L. A. Polakiewicz, p. 73.
[10] Cathy Popkin, “Chekhov as Ethnographer: Epistemological Crisis on Sakhalin Island,” Slavic Review, Vol. 51, No. 1 (Spring, 1992), p. 36.
[11]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hekhov, ed. Vera Gottlieb and Paul All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4.
[12] Ibid.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陳相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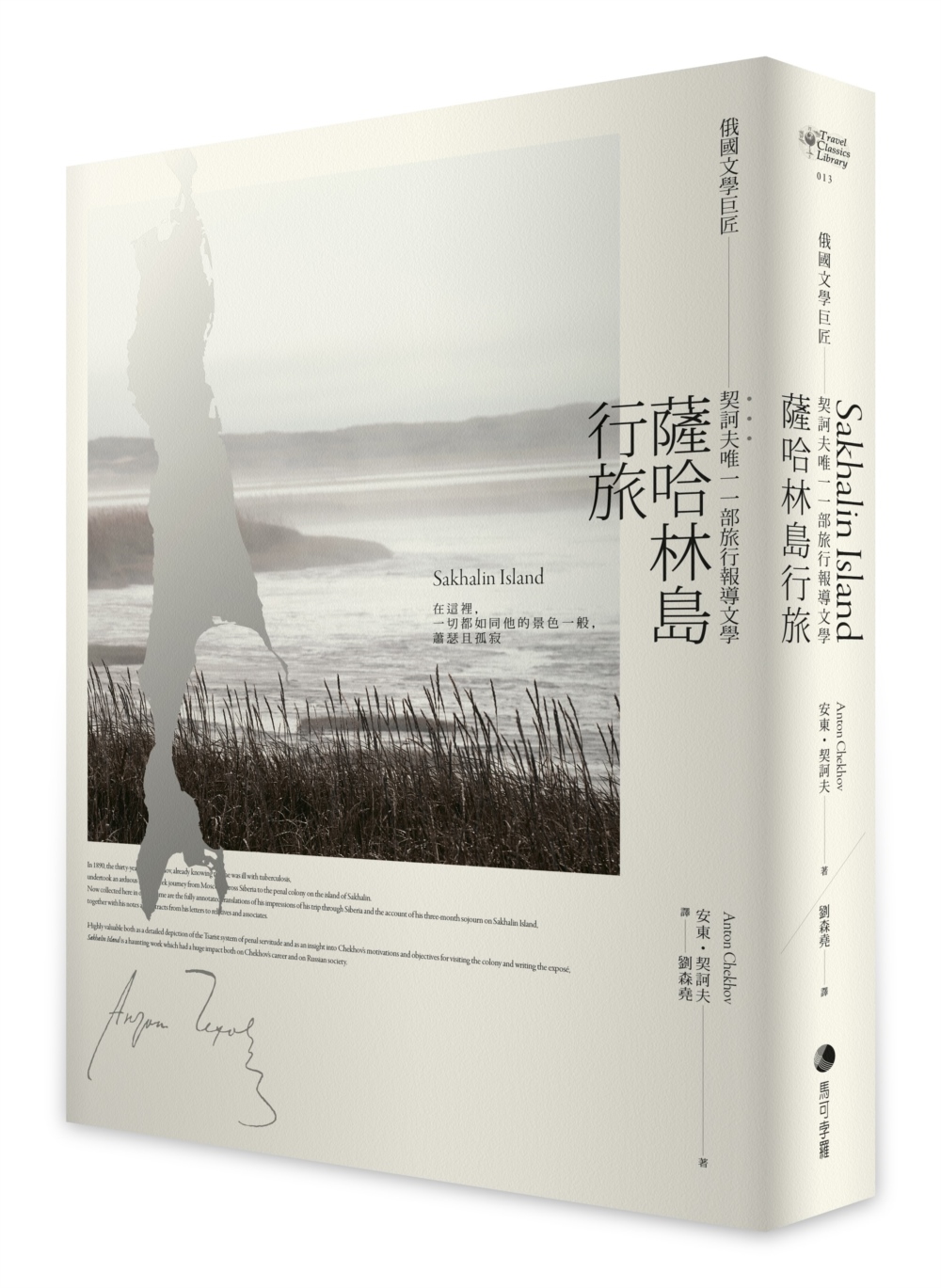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