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加入工會前,曾聽過這樣的事:我的二個同事原本在總公司的臺北印刷廠做事,因為是工會成員,一次大裁員的抗爭失敗後,公司高層以縮編為由,刻意將他們調到高雄的印刷廠。二人原本是維修師傅,到高雄只能當作業員,形同流放與貶職。這二位同事,都有一種生活與工作皆必須忍的氣質,一位脾氣較衝,總是在主管說公司不會虧待我們時,用滿滿的火氣吐槽:什麼公司不會虧待你?公司一直都在虧待你。至於另一位同事,不太講公司如何,他住在公司倉庫後的簡陋宿舍,我聽他講最多話的時候,是上班前,打電話給臺北的老婆與兒子。
以前的我,沒意識到這二人的苦,沒意識到作為工會成員,作為抵抗公司的人,都必將面臨打壓。直到我在《飛蛾撲火:兩個女人組織工會的故事》讀到這段,才比較明白:
「如今你回到悶熱的工廠分揀醫院的髒布巾,只要有空便跟我一起工作,賺的錢比運動開始前還少,實在很辛苦。這當然就是公司試圖表達的:看看阿爾瑪,處境比之前更慘。」
讀這本書,像是在閱讀一封很長很長的信。作者從住院時的一條毛毯開始回憶,談她作為工會組織者,與一位洗衣廠女工阿爾瑪成立工會的過程。一開始失敗了,阿爾瑪接著面對的是:停工行動後的繁瑣訴訟、主管的刁難、反工會同事的霸凌排拒。
一層又一層的困境描述,搭配的是更細膩深刻的紀實描寫:組織工會的策略與行動、美國洗衣業的大環境背景、工運歷史與重大事件,以及,歷史中一次次投身工運抗爭,卻被忽略而面目模糊的女性們。作者黛西.皮特金(Daisy Pitkin)從一場造成上百人傷亡的大火寫起,以大量資料佐證,還這些女性該有的面貌。
在 Instagram 查看這則貼文
這本書不斷在記憶中穿行,在歷史事件中穿行,在蛾的科普知識中穿行,像是一個人走了好遠的路,回過頭來,看那些曾經的燈火,有些記憶在深夜裡亮著,如書中一個提問:「你問了一個至今仍縈繞我心頭的問題……是什麼驅使某些人戰鬥?」
然後是思索:「自從你在2004年提出這個問題後,我想了又想,如今我懷疑戰鬥意志說不定與願景或想像力無關,而可能是一種變態,一種極度渴望改變、以致自己被改變了的狀態。日益緊繃的表皮緊箍著毛蟲的頸項和身軀,而毛蟲走動時,體內已藏著另一個未來身體的某些部分。戰鬥前的你使自己變性,出於必要而爆發成新的存在。」
「蛾」與「火」的篇章交錯,呈現出詩意的書寫。蛾,隱隱象徵著工廠裡的人、願意挺身而出的人、願意團結眾人的人,也是最微小的人。而火,從重大的工安事件與一位位投身工會的女性面貌中,成為抵抗意志的象徵。
這是一本容易勾動回憶的書。如果你曾經參加過工會,或者某些社會運動,你會被其中細膩的描寫,勾起過去的記憶。又或者,你曾經像我一樣,有著這樣的疑問:工會是什麼?工會的作用是什麼?加入工會有什麼好處?罷工是怎麼發動的?罷工時要幹嘛?罷工之後呢?你或多或少能從這本書中獲得解答。
2008年,我在中國時報高雄印刷廠當作業員,遇到大裁員(在我進廠工作前,他們已經先裁了50人)。我25歲,年輕,薪水不到三萬,年終只有半個月,雖然惶恐,但程度比不上年資15年以上的老同事,他們對於未來有更深的擔憂。
中國時報工會與資方談判破裂,決定發起罷工投票,但工會成員不足,一個衰老的工會,成員從一千多人衰退至二百多人。因此優惠新加入的成員免繳會費,但為防罷工時「背骨」(閩南語背叛之意),需要簽一張五萬元本票。
我簽了,加入工會,但什麼都不懂,滿心疑問。我上網查文章,碎片式的閱讀沒能建立什麼正確知識,印象深刻的反而是一串討論,有網友提到國外只要抗爭,一定會燒一臺車,不然沒人重視。
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工會、抗爭、抵抗這些詞彙。我有個浪漫幻想:罷工開始時,工會成員會帶著我們鎖上控制工廠總電源的機房,藏起關鍵零件與操作工具,讓不罷工的人也無法做事,然後工會成員會帶著我們拿一堆舊報紙在工廠外的廣場燃起火堆,他會揹著吉他彈奏,我們一群人就舉著旗子與布條,繞著火堆唱工人那卡西。
這畢竟是幻想。那年七月,我跟同事們早上下班後搭遊覽車到臺北參加罷工投票(報紙印刷廠上班時間是晚九朝五)。《苦勞網》有篇報導描述罷工投票前的開會現場:「強調自己是百忙之中抽空前來的中國時報發行人周盛淵表示,此波裁員,必須『說聲抱歉』,且原本預計裁員575位,如今已減為430位。」報導沒提的部分是,周盛淵在現場說他只回答三個問題。在臺下聽到這句話的我,回想起讀過的勞工文章,文章描述那些老闆與主管,都是這樣的形象:百忙之中,西裝筆挺,命令語句。周盛淵回答完就走了,之後,工會顧問鄭村棋有一番訓話,大意是:「你們怎麼那麼乖?對方說只回答三個問題,就真的只問三個?」又說:「你們也可以把門關起來,不放他離開呀!」他認為我們沒有戰鬥意志。
戰鬥意志是什麼?我聽了忍不住想。工廠裡的人,說穿了,是被訓練成事事都配合的人,不瞭解什麼是戰鬥,不瞭解什麼是抵抗,我們擁有的美德,是服從,遵從,與屈從。
罷工投票失敗了,差五票。回程時我滿懷失敗心情,混雜著「這到底在幹嘛」的疑問。當晚上班,到製版室取 PS 鋁板時,聽到廠長說工會真棒,說他覺得自己應該也要加入工會。我人單純,問了同事才知道是在奚落。有趣的是,當晚印刷機故障,廠長頭髮凌亂一臉惶恐地跑來,頻頻追問怎麼了?他以為我們硬是要搞罷工。下班時,一位老同事邊洗手邊笑:「原來還是會怕的喔。」
隔二個月,工會又進行一次投票會議,我沒去。這次投票通過了,不是罷工,是解散。
工會沒了。其後,中國時報被旺旺集團蔡衍明買下,易主後財務穩定,我升職等,薪水加了一千二百元,年終還能領到一個月。這種狀況,讓我有一段時間處於錯亂狀態,覺得加入工會沒帶給我任何幫助,也無法明白工會存在的意義。如果當時的我,能讀到《飛蛾撲火》這本書,或許不會在那股錯亂中徘徊良久。
錯亂感消失,浮現抵抗感,或許來自於新老闆的管理手段。每年尾牙抽獎,抽中的人,必須上臺背誦公司訓,唱旺旺歌,才能夠領獎。不分任何職等,新聞臺記者是如此,印刷廠工人也是如此。知道這個規定後,我曾忍不住想:如果工會還在,我們是不是可以不用這麼奴?
去年,高雄印刷廠裁撤。沒有工會,所有的裁撤都異常簡單。趁著一次出差機會,我半夜跑到廠區,看著黑暗中安靜的印刷廠,想起2016年我跟第二任廠長說我打算離職,嘗試別的工作。第二任廠長總是要我們這些作業員知足,說公司體制多好,這份工作有多穩定。(工會發動抗爭時,有同事在印刷機貼標語,當時是副廠長的他,看到,立刻撕下來。)
第二任廠長對我訓話了一番,大意是許多人被裁後都想回來。他說:「嘗試,有什麼好嘗試的。」當時我結結巴巴,說不出有力的句子。雖然現在還是說不出來,但我想,所謂的嘗試,或許是讓自己有能力透過讀一本書,有些心得,把一些記憶寫出來吧。
我參加工會的經驗雖然是失敗的,但終究在我心中,埋下一顆小小的,屬於抵抗的火種,如果不曾加入過工會,我可能要很久很久,才能瞭解抵抗是怎麼一回事吧。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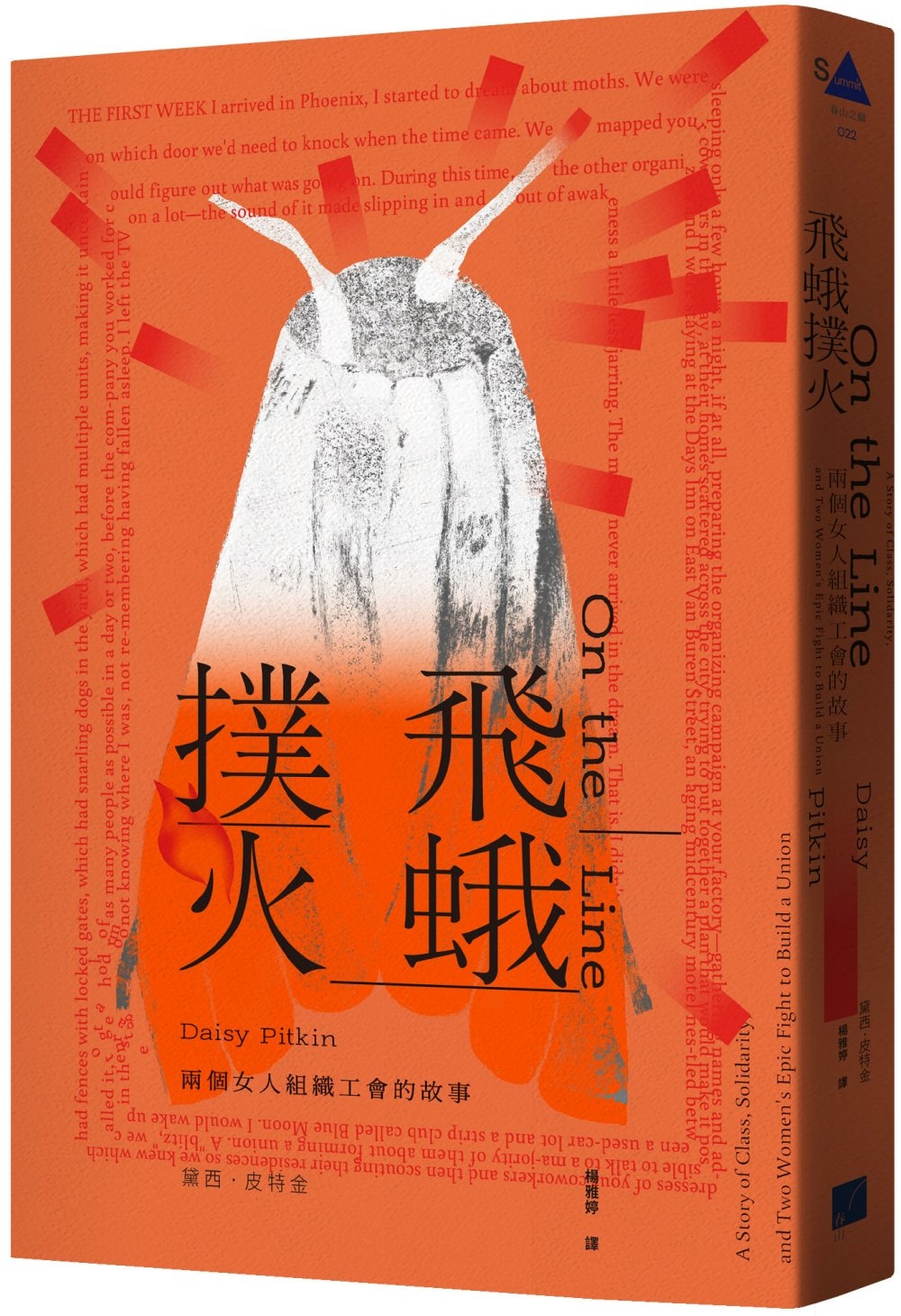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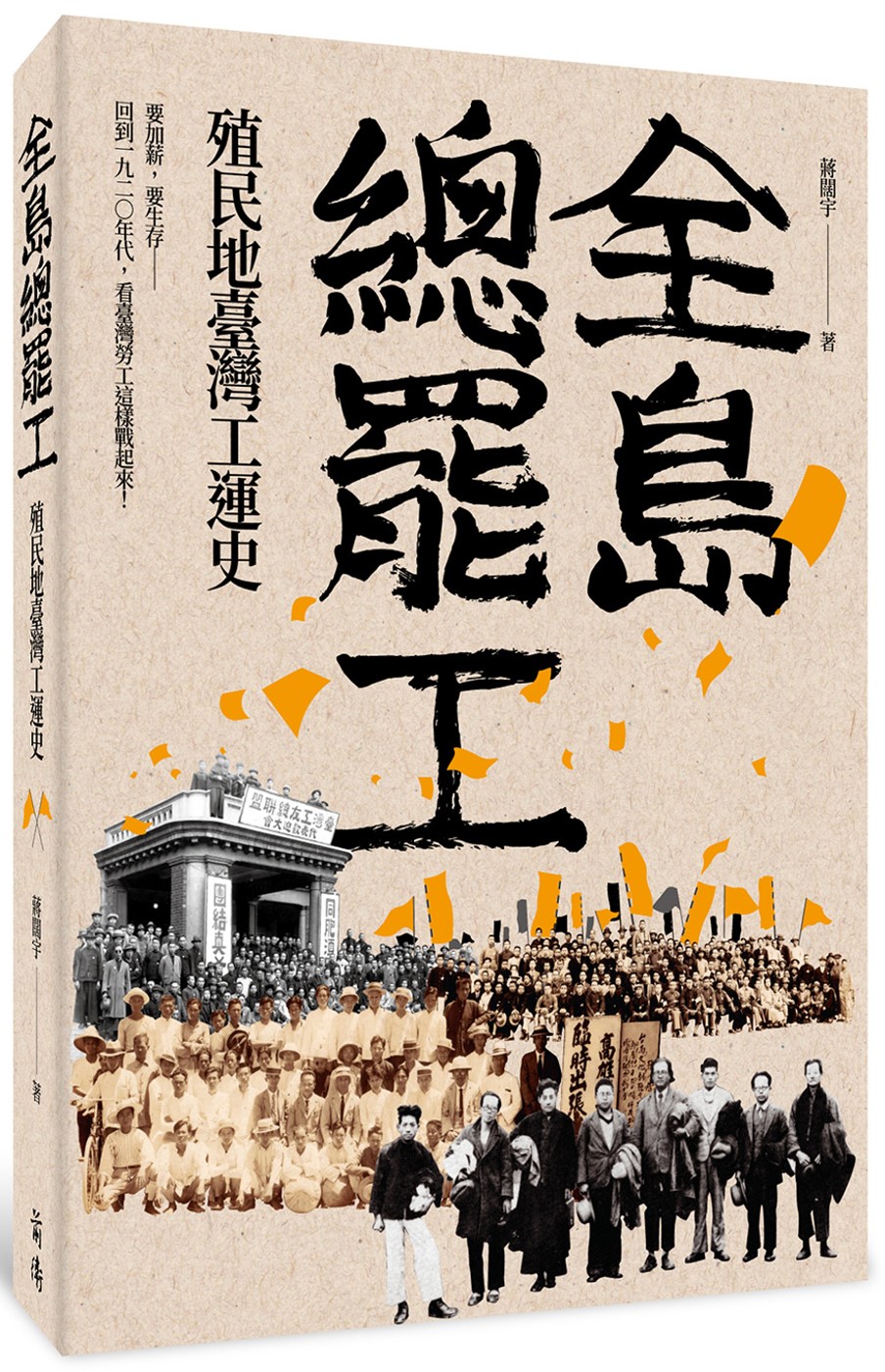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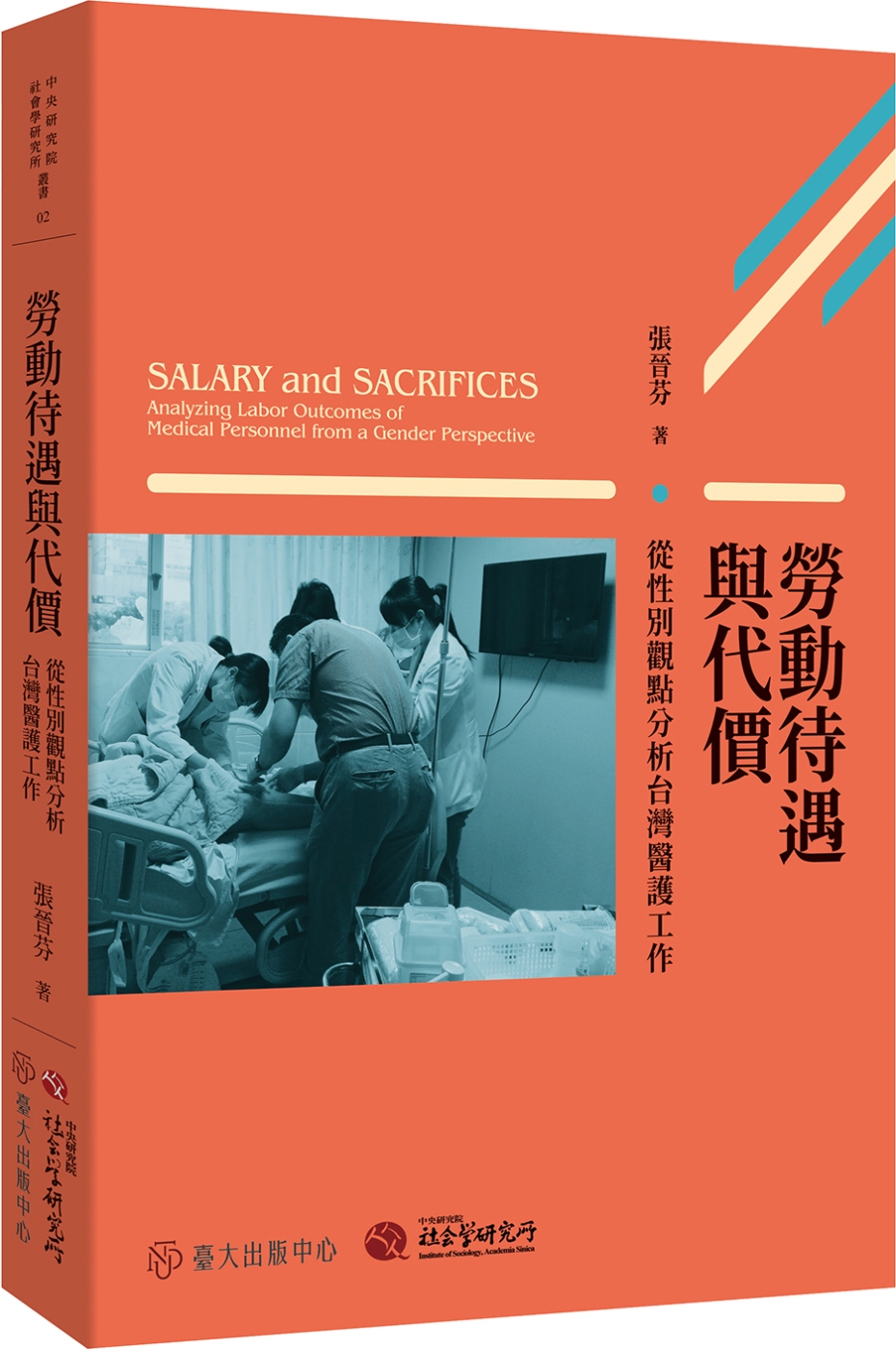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